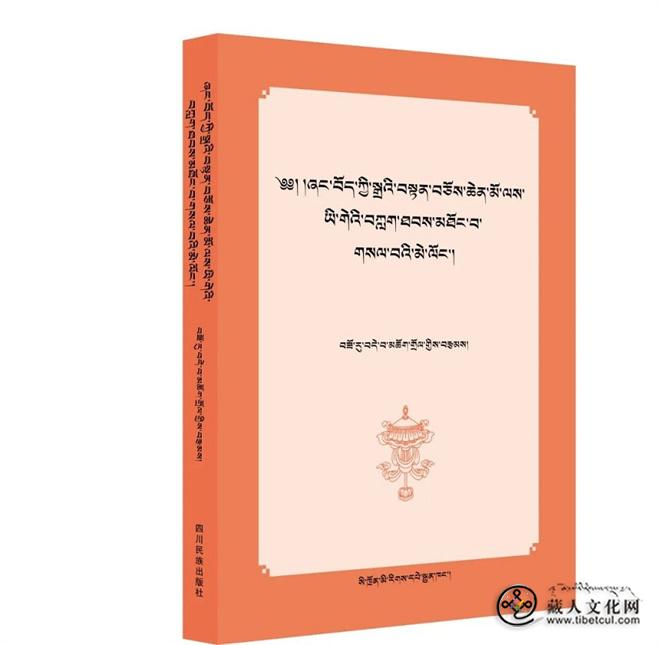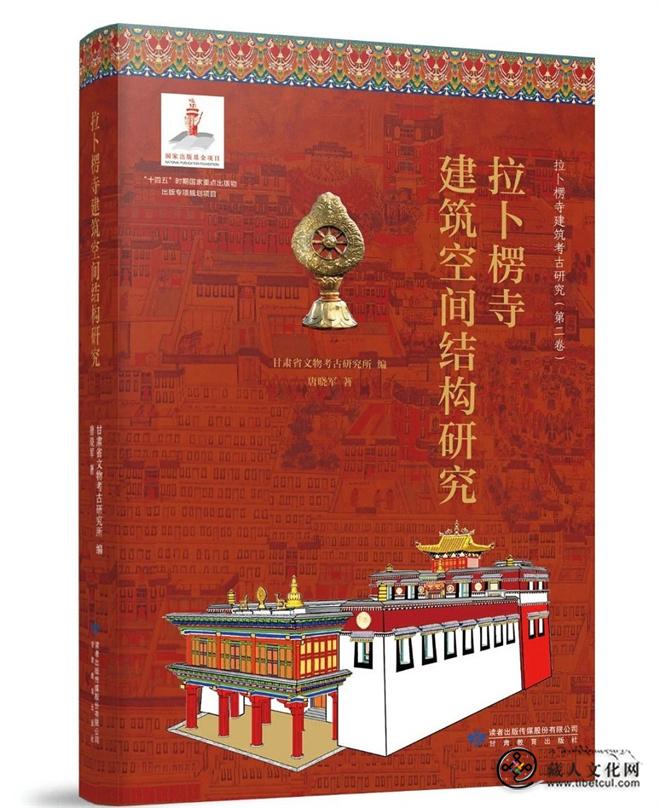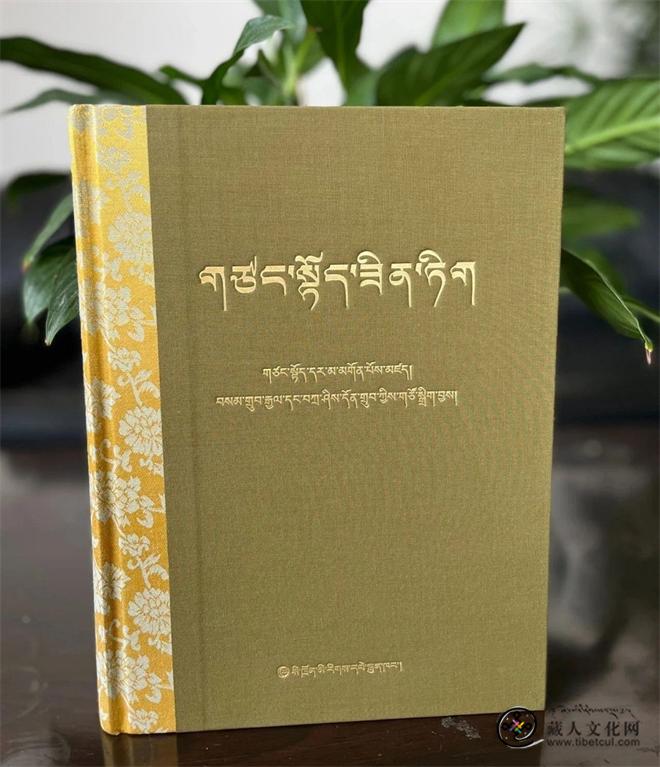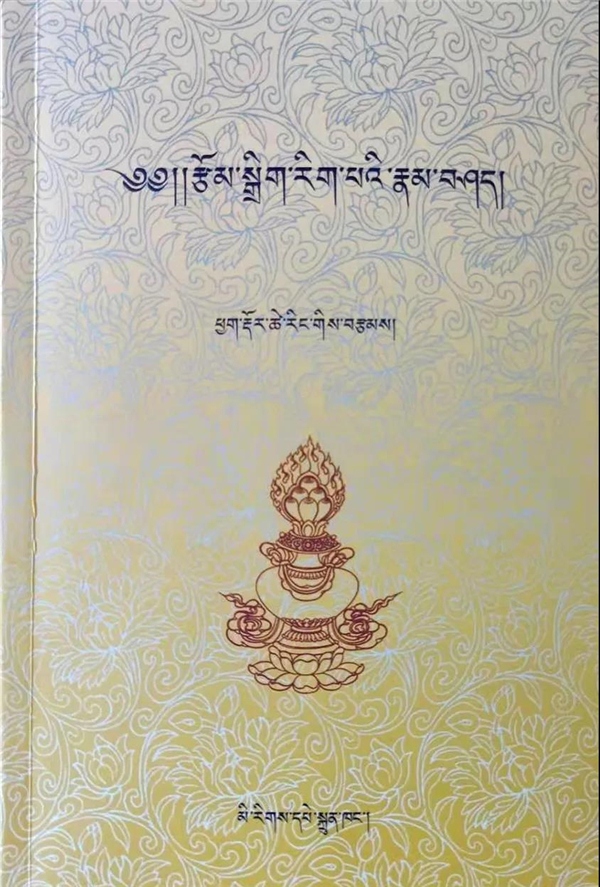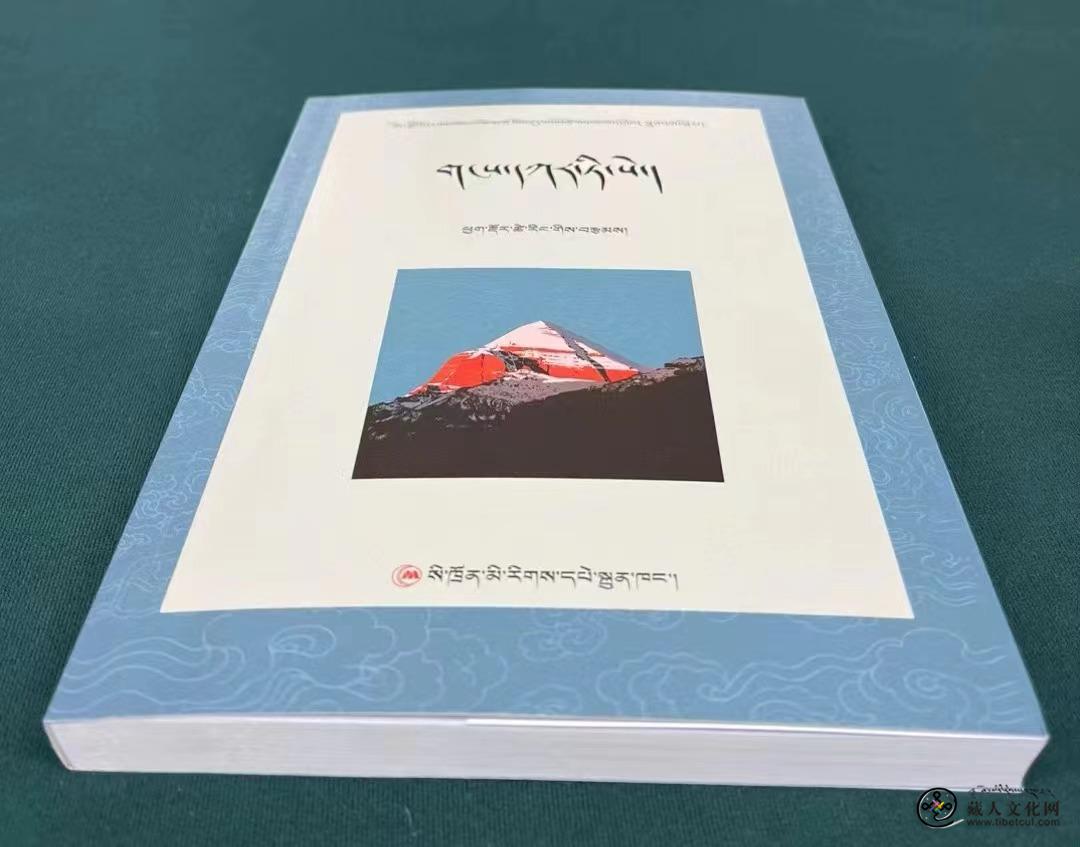2008е№ҙ5жңҲ12ж—ҘпјҢжҲҗйғҪпјҢйҳҝжқҘеқҗеңЁе®¶дёӯеҶҷдҪңй•ҝзҜҮе°ҸиҜҙгҖҠж јиҗЁе°”зҺӢгҖӢпјҢеҫңеҫүеңЁеҸӨд»ЈзҘһиҜқдё–з•ҢдёӯгҖӮдёӢеҚҲдёӨзӮ№пјҢдё–з•ҢејҖе§Ӣж‘ҮжҷғпјҢйҳҝжқҘжҠ¬еӨҙзңӢи§ҒзӘ—еӨ–зҡ„жҘјжҲҝж‘Үж‘Үж‘Ҷж‘ҶпјҢйҡҸеҗҺпјҢд»–дёӯж–ӯдәҶгҖҠж јиҗЁе°”зҺӢгҖӢзҡ„еҶҷдҪңгҖӮйҳҝжқҘжІүжөёеңЁеӨ§ең°зҡ„иӢҰйҡҫд№ӢдёӯпјҢжҜҸжҷҡйңҖиҰҒеҗ¬зқҖгҖҠе®үйӯӮжӣІгҖӢжүҚиғҪе…Ҙзң пјҢеҪ“д»–еҶҷдёӢ第дёҖеҸҘиҜқвҖңйҳҝе·ҙдёҖдёӘдәәеңЁеұұйҒ“дёҠж”ҖзҲ¬вҖқж—¶пјҢе·ІжіӘжөҒж»ЎйқўпјҢд»–жңүдҝЎеҝғеҶҷеҘҪиҝҷйғЁдҪңе“ҒпјҢдёәиҮӘе·ұпјҢдёәеӨ§ең°гҖӮ
 иҝҷдҫҝжҳҜдҪңе“Ғ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зҡ„иҜһз”ҹгҖӮ
иҝҷдҫҝжҳҜдҪңе“Ғ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зҡ„иҜһз”ҹгҖӮ
11жңҲ25ж—ҘпјҢз”ұдёӯеӣҪдҪңеҚҸеҲӣз ”йғЁгҖҒеӣӣе·қзңҒдҪң家еҚҸдјҡгҖҒеҢ—дә¬еҚҒжңҲж–ҮиүәеҮәзүҲзӨҫиҒ”еҗҲдё»еҠһзҡ„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з ”и®ЁдјҡпјҢеңЁеҢ—дә¬дёӯеӣҪдҪң家еҚҸдјҡеҚҒеұӮдјҡи®®е®ӨдёҫиЎҢгҖӮз ”и®ЁдјҡдёҠпјҢ专家еӯҰиҖ…д»Һеҗ„дёӘи§’еәҰеҜ№ гҖҠдә‘дёӯи®°гҖӢ иҝӣиЎҢдәҶйҳҗйҮҠдёҺи®Ёи®әгҖӮ
ең°йңҮеҗҺзҡ„еҸҚжҖқд№ӢдҪң
вҖң5В·12вҖқжұ¶е·қең°йңҮжҳҜдёҖж®өжІүз—ӣзҡ„и®°еҝҶпјҢзҒҫйҡҫд№ӢеҗҺд№ҹеҮәзҺ°дәҶдёҖзі»еҲ—зӣёе…ідҪңе“ҒгҖӮеңЁжұ¶е·қең°йңҮеҗҺпјҢйҳҝжқҘдәІзңји§ҒиҜҒдәҶдёҖдёӘжқ‘еӯҗд»…дёҖеӨңд№Ӣй—ҙеҪ»еә•ж¶ҲеӨұпјҢжң¬зқҖвҖңз”ҹе‘Ҫе…ұеҗҢдҪ“вҖқзҡ„жҖқиҖғпјҢд»–еҝғжғ…жІүйҮҚпјҢеӣ жӯӨеҲӣдҪңеҮә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гҖӮдёӯеӣҪдҪңеҚҸе…ҡз»„жҲҗе‘ҳгҖҒ еүҜдё»еёӯеҗүзӢ„马еҠ иЎЁзӨәпјҢ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еғҸдёҚж–ӯеӣһж—Ӣзҡ„еӨҚи°ғпјҢжҠҠзҺ°е®һгҖҒжўҰеўғгҖҒзҘһиҜқдёҺең°йңҮиҝҮзЁӢдёӯжҜҸдёӘдәәж„ҹеҸ—еҲ°зҡ„е…·дҪ“з»ҶиҠӮжңүжңәең°иһҚеҗҲеңЁдёҖиө·пјҢж·ұеҲ»ең°еҸҚжҳ зҒҫйҡҫеҸ‘з”ҹд№ӢеҗҺпјҢж°‘ж—Ҹж–ҮеҢ–зҡ„еҺҶеҸІи®°еҝҶдёҺж°‘ж—ҸзІҫзҘһи„җеёҰж–ӯиЈӮеҗҺзҡ„жәҜжңӣгҖӮ
еӣӣе·қзңҒдҪңеҚҸе…ҡз»„д№Ұи®°гҖҒеёёеҠЎеүҜдё»еёӯдҫҜеҝ—жҳҺи®ӨдёәпјҢвҖңйҳҝжқҘз»ҸиҝҮ10е№ҙзҡ„й…қй…ҝе’Ңз§Ҝж·ҖжңҖз»Ҳе®ҢжҲҗй•ҝзҜҮе°ҸиҜҙ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пјҢе°ҸиҜҙеҮәзүҲд»ҘеҗҺеҘҪиҜ„еҰӮжҪ®пјҢ并иҺ·еҫ—е…ЁеӣҪвҖҳдә”дёӘдёҖе·ҘзЁӢеҘ–вҖҷгҖӮжҲ‘们еҸ¬ејҖз ”и®Ёдјҡж—ўжҳҜеҜ№йҳҝжқҘиҝҷйғЁдҪңе“ҒиҝӣдёҖжӯҘж·ұе…Ҙз ”и®ЁпјҢжӣҙжҳҜиҙҜеҪ»иҗҪе®һеҚҒд№қеұҠеӣӣдёӯе…Ёдјҡе…ідәҺжҠҠзӨҫдјҡж•ҲзӣҠе’Ңз»ҸжөҺж•ҲзӣҠзӣёз»ҹдёҖзҡ„ж–ҮеҢ–еҲӣдҪңз”ҹдә§жңәеҲ¶зҡ„е…·дҪ“иЎҢеҠЁгҖӮвҖқ
еҢ—дә¬еҮәзүҲйӣҶеӣўжҖ»з»ҸзҗҶжӣІд»Ід№ҹеҜ№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з»ҷдәҲиӮҜе®ҡпјҡвҖңиҝҷйғЁдҪңе“Ғд»Ҙй«ҳиҙЁйҮҸзҡ„ж–ҮеӯҰејәжңүеҠӣең°еӣһеә”дәҶжҲ‘们民ж—ҸеҺҶеҸІдёҠе…ізі»йҮҚеӨ§гҖҒеҪұе“Қж·ұиҝңзҡ„дәӢ件пјҢжҳҜеҪ“д»Јж–ҮеӯҰеңЁзҺ°е®һйўҳжқҗеҲӣдҪңдёҠпјҢеңЁе‘јеә”ж—¶д»ЈйҮҚеӨ§дё»йўҳиҜҙзҡ„дёҖйғЁзҺ°иұЎзә§дҪңе“ҒгҖӮйҳҝжқҘдёҚжҳҜеңЁең°йңҮеҸ‘з”ҹзҡ„еҪ“дёӢеҮӯдёҖи…”зғӯиЎҖжҠ•е…ҘеҶҷдҪңпјҢд»–еҜ№зҒҫйҡҫжҖ§зҡ„дәӢ件пјҢеҜ№е®ғз»ҷжҲ‘们йҖ жҲҗзҡ„еҝғзҒөеҲӣдјӨд»ҘеҸҠеҲӣдјӨеҰӮдҪ•дҝ®еӨҚпјҢдёҚжӯўжҳҜзү©иҙЁдёҠзҡ„дҝ®еӨҚпјҢжӣҙйҮҚиҰҒзҡ„жҳҜйҖҡиҝҮеҜ№йҖқиҖ…зҒөйӯӮзҡ„ж…°е®үпјҢе®һзҺ°еҜ№з”ҹиҖ…зІҫзҘһзҡ„жҠҡж…°пјҢжңүзқҖй•ҝиҫҫеҚҒе№ҙзҡ„жІүж·ҖжҖқиҖғгҖӮжңҖз»ҲпјҢйҳҝжқҘжүҫеҲ°дәҶд»–зҡ„зӢ¬зү№зҡ„иЎЁиҫҫж–№ејҸгҖӮвҖқ
еҢ—дә¬еёҲиҢғеӨ§еӯҰж–ҮеӯҰйҷўеүҜйҷўй•ҝеј жё…еҚҺеҲҷд»ҺдәәдёҺиҮӘ然зҡ„е…ізі»иҝӣиЎҢеҲҮе…ҘпјҢвҖң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жғіиЎЁиҫҫд»Җд№Ҳе‘ўпјҹе®ғжҳҜиЎЁиҫҫиҮӘ然法еҲҷе’Ңдәәзҡ„иҜүжұӮд№Ӣй—ҙзҡ„еҶІзӘҒгҖӮвҖқе…ідәҺйҳҝжқҘеҶҷзҒҫйҡҫзҡ„ж–№ејҸпјҢеј жё…еҚҺиҜ„и®әйҒ“пјҡвҖңеҜ№дәҺдәЎйӯӮзҡ„зәӘеҝөпјҢ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йҖүжӢ©дәҶзҒҫйҡҫд№ӢеҗҺдәәзұ»зҡ„ж•‘иөҺгҖӮж•‘иөҺзҡ„ж–№ејҸжңүдёӨз§ҚпјҢдёҖз§ҚжҳҜ科еӯҰе’ҢзҗҶжҖ§зҡ„пјҢж”ҝеәңзҡ„ж•‘еҠ©е’ҢзҒҫеҗҺйҮҚе»әжҳҜеҝ…иҰҒзҡ„пјҢйҮҚе»әжқ‘еә„жҒўеӨҚиҮӘ然秩еәҸгҖӮиҖҢж–ҮеӯҰзҡ„иҒҢиғҪпјҢеҲҷжҳҜзҒөйӯӮзҡ„е®үзҪ®гҖӮйҳҝжқҘйҖүжӢ©дёҖдёӘзҘӯеёҲйҳҝе·ҙзҡ„и§’иүІпјҢе…¶йҹіиҠӮеғҸе“‘е·ҙзҡ„еҸ‘йҹіпјҢеӣ дёәе“‘е·ҙеҸӘиғҪеҸ‘вҖҳйҳҝе·ҙгҖҒйҳҝе·ҙвҖҷзҡ„еЈ°йҹігҖӮйҳҝе·ҙжңүдёӨдёӘиә«д»ҪпјҢдёҖдёӘжҳҜзҺ°д»Јж–ҮжҳҺз»ҷе®ҡзҡ„иә«д»ҪпјҢжүҖи°“зҡ„йқһзү©иҙЁж–ҮеҢ–йҒ—дә§дј жүҝдәәпјҢиҝҳжңүдёҖдёӘжҳҜдј з»ҹж–ҮеҢ–еҪ“дёӯд»Ӣд№ҺдәҺе·«зҡ„и§’иүІпјҢе°ұжҳҜжүҖи°“зҡ„зҘӯеёҲгҖӮд»–еӣһеҲ°ж•…еңҹпјҢе’Ңжӯ»еҺ»зҡ„дәЎйӯӮеҜ№иҜқпјҢе®үйЎҝ他们пјҢжқҘе®ҢжҲҗеҸҰдёҖдёӘд»ӘејҸпјҢе°ұеғҸеҺҹе§Ӣзҡ„ж°‘й—ҙж–№ејҸеӨ„зҗҶзҒҫйҡҫе’Ңи®°еҝҶгҖӮвҖқ
гҖҠеҪ“д»Јж–ҮеқӣгҖӢеүҜдё»зј–иөөйӣ·д»ҺдәәжҖ§ж·ұеәҰе’ҢжӮІеү§зІҫзҘһпјҢеҜ№йҳҝжқҘзҡ„зҒҫйҡҫжҖ§д№ҰеҶҷз»ҷдәҲиӮҜе®ҡпјҡвҖңжҲ‘们并дёҚзјәд№ҸзҒҫйҡҫж–ҮеӯҰпјҢжҲ‘们зјәд№Ҹзҡ„жҳҜжңүдәәжҖ§ж·ұеәҰе’ҢжӮІеү§зІҫзҘһзҡ„зҒҫйҡҫж–ҮеӯҰпјҢзјәд№ҸеғҸгҖҠйңҚд№ұж—¶жңҹзҡ„зҲұжғ…гҖӢиҝҷж ·зҡ„дҪңе“ҒпјҢжҲ‘дёӘдәәи®Өдёә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жҒ°еҘҪејҘиЎҘдәҶиҝҷдёӘйҒ—жҶҫгҖӮ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жҳҜд»Һж–ҮеӯҰгҖҒзҫҺеӯҰе’Ңе“ІеӯҰзҡ„з»ҙеәҰпјҢз»Ҹз”ұдёӘдҪ“зҡ„ж¶ҲеӨұгҖҒжқ‘еә„зҡ„ж¶ҲдәЎжқҘи§Ӯз…§дәәзұ»зҡ„жҷ®йҒҚеўғйҒҮе’Ңе…ұеҗҢе‘ҪиҝҗпјҢд»ҺиҖҢиҫҫеҲ°и¶…и¶ҠжҖ§гҖҒжӮІеү§жҖ§зҡ„еўғз•ҢгҖӮзӣёдҝЎиҝҷж ·дёҖйғЁдҪңе“ҒиғҪеӨҹз»ҸеҸ—дҪҸиҜ»иҖ…зҡ„йҳ…иҜ»е’ҢеҺҶеҸІзҡ„жЈҖйӘҢпјҢеңЁдёӯеӣҪеҪ“д»Је°ҸиҜҙеҸІе’Ңдё–з•ҢзҒҫйҡҫж–ҮеӯҰеҸІдёҠеҚ жҚ®е®ғеә”жңүзҡ„ең°дҪҚгҖӮвҖқ
дёӯеӣҪдҪңеҚҸзҪ‘з»ңж–ҮеӯҰдёӯеҝғдё»д»»дҪ•ејҳи®ӨдёәпјҢ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жҳҜиҝ‘е№ҙжқҘе°ҸиҜҙеҶҷдҪңйўҶеҹҹйқһеёёйҡҫеҫ—зҡ„дҪңе“ҒпјҢиҝҷдёӘдҪңе“Ғи§ҰеҸҠеҲ°еҪ“дёӢпјҢдёҚе…үжҳҜдёӯеӣҪдәәпјҢиҖҢжҳҜж•ҙдёӘдәәзұ»йқўдёҙзҡ„йҮҚиҰҒй—®йўҳпјҢж—ўжҳҜдёҖдёӘзҺ°е®һзҡ„й—®йўҳпјҢд№ҹжҳҜдёҖдёӘз»ҲжһҒзҡ„й—®йўҳгҖӮдәәзұ»йқўеҜ№зҡ„зҺ°д»ЈжҖ§пјҢзҺ°д»Јз§‘жҠҖзҡ„еҸ‘еұ•пјҢжҲ‘们еҰӮдҪ•и®Өе®ҡж— зҘһзҡ„дҝЎд»°пјҢеҰӮдҪ•йқўдёҙеҸҚйӯ…зҡ„й—®йўҳпјҹжұ¶е·қең°йңҮеҸ‘з”ҹд»ҘеҗҺеҫҲеӨҡдҪңе“ҒжҸҸеҶҷпјҢеӨ§еӨҡзҡ„еҶҷдҪңжҳҜдёҖз§Қеұ•зӨәејҸзҡ„з”ҡиҮіж¶Ҳиҙ№ејҸзҡ„еҜ№зҒҫйҡҫзҡ„д№ҰеҶҷпјҢйҳҝжқҘеҶҷвҖң5В·12вҖқжұ¶е·қең°йңҮеҲҷйҮҚж–°еӣһеҲ°дәәжң¬иә«пјҢд»–йҖҡиҝҮиҝҷдёӘдәӢ件еҫҲеҘҪең°еҶҷеҮәдәҶдәәдёҺиҮӘиә«зҡ„е…ізі»гҖҒдәәдёҺз”ҹе‘Ҫзҡ„е…ізі»гҖҒдәәдёҺиҮӘ然зҡ„е…ізі»гҖӮ
 гҖҠдёӯеӣҪйқ’е№ҙдҪң家жҠҘгҖӢ2019е№ҙ12жңҲ3ж—Ҙ1зүҲе’Ң3зүҲжҲӘеӣҫ
гҖҠдёӯеӣҪйқ’е№ҙдҪң家жҠҘгҖӢ2019е№ҙ12жңҲ3ж—Ҙ1зүҲе’Ң3зүҲжҲӘеӣҫ
е…ёеһӢдәәзү©зҡ„еЎ‘йҖ
дёҖйғЁдјҳз§Җзҡ„ж–ҮеӯҰдҪңе“ҒпјҢзҰ»дёҚејҖдәәзү©еҪўиұЎзҡ„жҲҗеҠҹеЎ‘йҖ гҖӮдёҖдәӣжҲҗеҠҹзҡ„дәәзү©еҪўиұЎд№ҹдјҡж·ұе…ҘдәәеҝғпјҢ家喻жҲ·жҷ“гҖӮ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дёӯдё»иҰҒеЎ‘йҖ дәҶдёӨдёӘдё»иҰҒдәәзү©пјҢзҘӯеёҲйҳҝе·ҙе’Ңдҫ„еӯҗд»Ғй’ҰгҖӮеңЁз ”и®ЁдјҡдёӯпјҢ专家еӯҰиҖ…еҜ№ж–ҮеӯҰдҪңе“Ғе…ёеһӢдәәзү©зҡ„еЎ‘йҖ д№ҹиҝӣиЎҢдәҶи®Ёи®әгҖӮ
дёӯеӣҪе°‘ж•°ж°‘ж—ҸдҪң家еӯҰдјҡеүҜдјҡй•ҝеҢ…жҳҺеҫ·пјҢе°Ҷ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дёҺгҖҠе°ҳеҹғиҗҪе®ҡгҖӢдёӨжң¬д№Ұзҡ„дё»дәәе…¬еҒҡдәҶеҜ№жҜ”гҖӮвҖңйҳҝе·ҙе’ҢгҖҠе°ҳеҹғиҗҪе®ҡгҖӢдёӯзҡ„еӮ»еӯҗе°‘зҲ·жҜ”иө·жқҘиҝҳжңүдёҚеҗҢгҖӮеӮ»еӯҗе°‘зҲ·з”ҹжҙ»еңЁдёҖдёӘдёҮжҒ¶зҡ„ж—§зӨҫдјҡпјҢз”ҹй•ҝеңЁй»‘жҡ—зҡ„еңҹеҸёеҲ¶еәҰз»ҹжІ»ж—¶жңҹпјҢз”ұдәҺд»–еҫҲжҷәж…§пјҢеңЁз”ҹжҙ»дёӯжңүзҡ„дәәдёҚеә”зў°пјҢд»–е°ұйҡҸжіўйҖҗжөҒпјҢдҪҶдҝқжҢҒзқҖиҮӘе·ұзҡ„жё…йҶ’пјҢйҡҸжіўйҖҗжөҒдҪҶз»қдёҚеҗҢжөҒеҗҲжұЎгҖӮдҪҶжҳҜйҳҝе·ҙжӣҙ超然дәҺдё–дҝ—пјҢд»–жӣҙеңЁж„ҸдәҺзҒөйӯӮе’ҢдҝЎеҝөпјҢд»–иҷ”иҜҡең°еҙҮд»°еұұзҘһпјҢд»–еҲ»йӘЁй“ӯеҝғзҡ„д№Ўж„ҒпјҢеҜ№зҷҫдҪҷдәЎзҒөжҒӢжҒӢдёҚиҲҚзҡ„д№Ўжғ…пјҢйӮЈдёӘжҸҸеҶҷйқһеёёж„ҹдәәгҖӮвҖқеҢ…жҳҺеҫ·иҜҙгҖӮ
дёӯеӣҪдҪңеҚҸеҲӣз ”йғЁеүҜдё»д»»жқҺжңқе…Ёи°ҲеҸҠдё»дәәе…¬йҳҝе·ҙе’ҢеӨ–з”Ҙд»Ғй’Ұж—¶пјҢиҜҙпјҡвҖңиҝҷйғЁе°ҸиҜҙйқһеёёжқ°еҮәзҡ„ең°ж–№пјҢеңЁдәҺдәәзү©зҡ„еЎ‘йҖ жҳҜйқһеёёзӢ¬зү№зҡ„гҖӮйҳҝе·ҙжҳҜе…·жңүж®үж•ҷжҲ–иҖ…е°ҪиҒҢзҡ„зҘӯеёҲпјҢд»–иҮӘж„ҝйҖүжӢ©жӯ»дәЎпјҢеңЁд»–иә«дёҠдҪ“зҺ°еҮәзҡ„жҳҜжӮІеЈ®зҡ„иӢұйӣ„зҡ„еҙҮй«ҳзҫҺгҖӮд»–дёҖдёӘдәәиҰҒжүӣиө·жүҖжңүй»‘жҡ—зҡ„й—ёй—ЁпјҢз»ҷжҙ»зқҖзҡ„дәәз•ҷдёӢе…үжҳҺеёҰеҺ»жё©жҡ–гҖӮд»–зҡ„еӨ–з”Ҙд»Ғй’Ұиә«дёҠд№ҹжҳҜеёҰжңүеҫҲжө“йҮҚзҡ„дәәжғ…е‘іпјҢең°йңҮ第дёҖж—¶й—ҙдҪңдёәеҺҝйҮҢжҙҫдёӢеҺ»зҡ„е№ІйғЁпјҢд»–еҪ“然иҰҒе…ЁеҠӣжҠўйҷ©ж•‘зҒҫгҖӮд»–жё…йҶ’иҝҮжқҘзҡ„зһ¬й—ҙдёҖи·ҜеҜ»жүҫд»–зҡ„еҰҲеҰҲпјҢиҝҷдёҖзӮ№еҶҷеҫ—йқһеёёеҲ°дҪҚпјҢдҪҶжҳҜеҫҲйҒ—жҶҫеҰҲеҰҲжІЎжңүжүҫеҲ°пјҢжҲ‘еңЁиҜ»зҡ„ж—¶еҖҷд№ҹжҳҜжөҒдёӢдәҶзңјжіӘгҖӮиҝҷж ·дёҖдёӘе№ҙиҪ»дәәжңүдәәжғ…е‘іпјҢд»–дёҚжҳҜе°ұжғіеҪ“е®ҳгҖҒе°ұжғідёҖдёӘеҠІеҫҖдёҠзҲ¬пјҢе®һйҷ…дёҠд»–зҗҶи§Јд»–иҲ…иҲ…зҡ„йҖүжӢ©пјҢд»ҺиҝҷдёӘе№ҙиҪ»дәәжҲҗй•ҝзҡ„з»ҸеҺҶпјҢжҲ‘们зңӢеҲ°зҡ„жҳҜи¶…и¶Ҡзҡ„еҠӣйҮҸпјҢиҝҷе®һйҷ…дёҠд№ҹжҳҜи—Ҹж—Ҹж–ҮеҢ–дј жүҝдёӢжқҘзҡ„еёҢжңӣпјҢйҳҝе·ҙдј жүҝеҲ°д»Ғй’Ұиә«дёҠгҖӮе…¶е®һпјҢиҝҷжҳҜдёҖйғЁзҒөйӯӮж•‘иөҺд№ӢдҪңпјҢжҠҡж…°з”ҹиҖ…е‘Ҡж…°йҖқиҖ…гҖӮд№ҹжҳҜдёҖйғЁж–ҮеҢ–еҜ»ж №д№ӢдҪңпјҢд»Һж°‘ж—Ҹдјҳз§Җдј з»ҹж–ҮеҢ–иө„жәҗдёӯжүҫеҲ°з–—ж•‘иә«еҝғзҡ„зҒөиҚҜгҖӮвҖқ
е°ҸиҜҙзҫҺеӯҰйЈҺж ј
йҳҝжқҘжң¬жҳҜдҪҚиҜ—дәәпјҢе…¶е°ҸиҜҙд№ҹе…·жңүзӢ¬зү№зҡ„зҫҺеӯҰйЈҺж јгҖӮвҖңеңЁеҶҷдҪң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жҲ‘иҖҒжғіиө·иҺ«жүҺзү№зҡ„йҹід№җпјҢе°Өе…¶еңЁеҪ“е№ҙең°йңҮзҒҫе®ізҺ°еңәпјҢеҘҪеғҸе”ҜдёҖз»ҷжҲ‘е®үж…°зҡ„е°ұжҳҜд»–зҡ„йҹід№җпјҢжҜҸеӨ©жҷҡдёҠжҲ‘еңЁиҪҰйҮҢеҒ·еҒ·еҗ¬ж—¶пјҢеҘҪеғҸеҫ—еҲ°дёҖзӮ№е®үж…°гҖӮеә„йҮҚгҖҒж·ұйӮғгҖҒе…ёйӣ…зҡ„йҹід№җе’ҢеҘҪзҡ„ж–ҮеӯҰдҪңе“ҒеёҰз»ҷдәәзҡ„еҶІеҮ»е’Ңж„ҹеҸ—йғҪжҳҜжӣҙж·ұеұӮйқўзҡ„гҖӮвҖқеңЁз ”и®ЁдјҡдёҠпјҢйҳҝжқҘиҝҷж ·иҜҙгҖӮ
гҖҠдәәж°‘ж—ҘжҠҘгҖӢж–ҮиүәйғЁеүҜдё»д»»еҲҳзҗјд»Һйҹід№җзҡ„и§’еәҰиҜ„д»·иҜҙпјҡвҖң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жңүеӨҚи°ғж•Ҳжһңе’ҢдәӨе“ҚжӣІзҡ„ж•ҲжһңпјҢд№ҹжӣҙеғҸдёҖдёӘе°ҸжҸҗзҗҙзҡ„еҚҸеҘҸжӣІгҖӮе°ҸжҸҗзҗҙеҚҸеҘҸжӣІйҮҢйқўдё»йҹізҡ„йғЁеҲҶпјҢе°ұжҳҜзҘӯеёҲйҳҝе·ҙзҡ„иҠӮеҘҸе’Ңж—ӢеҫӢпјҢе…¶д»–зҡ„дәәзү©жҳҜй…ҚеҷЁзҡ„еҶҷдҪңгҖӮвҖқ
йқ’е№ҙиҜ—дәәжқҺеЈ®и®ӨдёәпјҡвҖңжҲ‘们еҸҜд»ҘжҠҠ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зңӢдҪңдёҖдёӘи·Ёж–ҮдҪ“зҡ„ж–Үжң¬пјҢйҰ–е…Ҳе®ғжҳҜй•ҝзҜҮе°ҸиҜҙпјҢеңЁеҪўејҸе’ҢеҶҷжі•дёҠ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дҪңе“ҒиғҢеҗҺиҜ—зҡ„иҜӯиЁҖгҖҒиҜ—зҡ„жғ…ж„ҹзҡ„е‘ҲзҺ°ж–№ејҸпјҢд»ҘеҸҠйҹід№җзҡ„е…ғзҙ пјҢе®ғзҡ„е№ізј“зҡ„жөҒж·ҢпјҢе®ғзҡ„иҠӮеҘҸж„ҹпјҢеҢ…жӢ¬жқ‘еә„еңЁйҷ·иҗҪд№ӢеүҚдёҚж–ӯдёҠеұұзҡ„дәәпјҢд»Һең°иҙЁйҳҹеҲ°жқ‘е№ІйғЁпјҢеҲ°д№ӢеүҚзҡ„ж—§зӣёиҜҶпјҢдёҚж–ӯдёҠжқҘжү“д№ұеҺҹжқҘзҡ„иҠӮеҘҸпјҢжһ„жҲҗдёҖдёӘеҸҳи°ғгҖӮйҳ…иҜ»иҝҷйғЁе°ҸиҜҙпјҢдёҚд»…д»…жҳҜеңЁиҜ»пјҢжӣҙеғҸжҳҜеңЁеҗ¬д№Ұеҗ¬йҹід№җгҖӮвҖқ
еј жё…еҚҺеҲҷд»ҺзҫҺеӯҰйҖ»иҫ‘еҜ№йҳҝе·ҙзҡ„жӯ»иҝӣиЎҢдәҶиӮҜе®ҡпјҡвҖңдёҺең°йңҮеҗҺдёӢжІүзҡ„дә‘дёӯжқ‘дёҖиө·жІүе…ҘжӮ¬еҙ–иҗҪе…Ҙж·ұжёҠпјҢ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жӮІеү§зҡ„еҜ“иЁҖпјҢе®ғж—ўжҳҜжңәйҒҮе’Ңж•‘иөҺзҡ„д»Јд»·з»“жһңпјҢд№ҹжҳҜжӮІеү§зҡ„зҫҺеӯҰйҖ»иҫ‘гҖӮжҲ‘и§үеҫ—и®©дәәзү©жҙ»дёӢжқҘдёҚз¬ҰеҗҲе°ҸиҜҙзҡ„зҫҺеӯҰйҖ»иҫ‘пјҢд»–дёҚжӯ»дјјд№Һд№ҹж— жі•еҶҚж¬ЎеҪ’жқҘпјҢд»–зҡ„ж¶ҲеӨұжҳҜж—¶д»Је’Ңж–ҮжҳҺзҡ„ж¶ҲеӨұпјҢжҳҜеҝ…然зҡ„гҖӮвҖқ
е…ідәҺз”ҹжӯ»зҡ„и®Ёи®ә
йҳҝжқҘеҶҷ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жҳҫ然жҳҜиҰҒиЎЁиҫҫж–°зҡ„жғіжі•пјҢжҢүз…§д»–иҮӘе·ұзҡ„иҜҙжі•пјҢжҳҜеңЁжҖқиҖғз”ҹе‘ҪдёҺжӯ»дәЎгҖӮз”ҹдёҺжӯ»жҳҜж–ҮеӯҰзҡ„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дё»йўҳпјҢдҪҶе°ҸиҜҙ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дёӯпјҢйҳҝжқҘеҜ№з”ҹдёҺжӯ»иөӢдәҲдәҶжӣҙеӨҡзҡ„еҶ…ж¶өпјҢе…¶дёӯеҜ№дәҺе°ҸиҜҙдё»дәәе…¬йҳҝе·ҙзҡ„жӯ»дәЎз»“еұҖпјҢд№ҹеј•иө·дәҶеҗ„дҪҚеӯҰиҖ…зҡ„и®Ёи®әгҖӮ
жІҲйҳіеёҲиҢғеӨ§еӯҰзү№иҒҳж•ҷжҺҲиҙәз»ҚдҝҠиҜҙпјҢд»Һ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дёӯеҸҜд»ҘзңӢеҮәпјҢйҳҝжқҘеҜ№з”ҹдёҺжӯ»зҡ„жҖқиҖғжңүеҫҲеӨҡж–°зҡ„еҶ…ж¶өпјҢжңҖзӘҒеҮәзҡ„дёҖзӮ№жҳҜз”ҹжҖҒж„ҸиҜҶпјҢе®ғжһ„жҲҗдәҶйҳҝжқҘйҮҚж–°и®ӨиҜҶжұ¶е·қең°йңҮзҡ„дёҖдёӘжҖқиҖғзҡ„еҮәеҸ‘зӮ№гҖӮе°Ҫз®ЎйҳҝжқҘдёҚжҳҜеҲ»ж„ҸиҰҒеҶҷжҲҗеҸҚжҳ з”ҹжҖҒй—®йўҳзҡ„е°ҸиҜҙпјҢдҪҶжҳҜз”ҹжҖҒж„ҸиҜҶдҪҝд»–жҠҠжҖқиҖғзҡ„з”ҹдёҺжӯ»зҡ„й—®йўҳпјҢзҪ®дәҺдәәдёҺиҮӘ然зҡ„е…ізі»дёӯеҺ»и®ӨиҜҶпјҢзҪ®дәҺзҺ°д»Јж–ҮеӯҰзҡ„ж–°й«ҳеәҰжқҘи®ӨиҜҶгҖӮдҪңе“ҒдёӯжҖқиҖғзҡ„з”ҹдёҺжӯ»зҡ„й—®йўҳдёҚд»…еұһдәҺдәәзұ»пјҢд№ҹеұһдәҺж•ҙдёӘеӨ§иҮӘ然гҖӮ
йҳҝе·ҙзҡ„жӯ»жҳҜеҸҜжғңзҡ„пјҢвҖңиғҪдёҚиғҪжңҖеҗҺдёҚи®©йҳҝе·ҙжӯ»еҺ»пјҹвҖқиҙәз»ҚдҝҠи®ӨдёәпјҢйҳҝе·ҙзҡ„жӯ»зҡ„зЎ®жҳҜе°Ҷз”ҹдёҺжӯ»зҡ„иҝҪй—®жҺЁеҗ‘й«ҳжҪ®пјҢе…·жңүеҫҲејәеӨ§зҡ„еҶІеҮ»еҠӣгҖӮйҳҝе·ҙзҡ„жӯ»йҡҗеҗ«зқҖд»Җд№Ҳй—®йўҳпјҹеҜ№з”ҹдёҺжӯ»зҡ„иҝҪй—®жңҖз»ҲжҳҜдёәдәҶд»Җд№ҲпјҹжҳҜдёәдәҶиҰҒзғӯзҲұз”ҹе‘ҪгҖҒдҝқжҠӨз”ҹе‘ҪгҖӮд»Һж•…дәӢеұӮйқўжқҘиҜҙпјҢеҸҜд»ҘйҖүжӢ©дёҖдёӘдәәжӯ»пјҢдҪҶжҲ‘и§үеҫ—иҝҷдјҡдјӨе®іеҜ№дәҺз”ҹдёҺжӯ»иҝҪй—®зҡ„иҝҷдёӘдё»йўҳгҖӮеҰӮжһңи®©з”ҹдёҺжӯ»зҡ„иҝҪй—®дёҺдәәйҒ“дё»д№үй—®йўҳеҚҸи°ғиө·жқҘпјҢе°ұжӣҙжңүеҠӣйҮҸдәҶгҖӮ
 йҳҝжқҘй•ҝзҜҮе°ҸиҜҙ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з ”и®ЁдјҡзҺ°еңәгҖӮиөөе°Ҹиҗұ /ж‘„
йҳҝжқҘй•ҝзҜҮе°ҸиҜҙ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з ”и®ЁдјҡзҺ°еңәгҖӮиөөе°Ҹиҗұ /ж‘„
дёӯеӣҪдҪңеҚҸеҠһе…¬еҺ…еүҜдё»д»»зҺӢеҶӣи®ӨдёәпјҢйҳҝе·ҙйҖүжӢ©еҗ‘жӯ»иҖҢз”ҹпјҢиҝҷе°ұдҪ“зҺ°еҮәж–ҮеӯҰж„Ҹд№үдёҠзңҹжӯЈзҡ„дәәзҡ„д»·еҖјпјҢвҖңйҳҝе·ҙе’Ңдә‘дёӯжқ‘дёҖиө·еқ е…ҘжұҹдёӯпјҢд»–зҡ„иӮүдҪ“ж¶ҲеӨұдәҶпјҢдҪҶжҳҜзҒөйӯӮеңЁдёҠеҚҮгҖӮжӯҢеҫ·иҜҙеҝғдёӯжңүдёӨз§ҚзҒөйӯӮпјҢдёҖдёӘжӢје‘Ҫең°йҷ„зқҖзҺ°дё–пјҢеҸҰдёҖдёӘиҰҒзҰ»ејҖдё–дҝ—пјҢиҰҒеҲ°е…ҲиҫҲйӮЈйҮҢгҖӮиҝҷжҳҜдё–дҝ—е’ҢзҒөйӯӮгҖҒзү©иҙЁе’Ңз”ҹжҙ»зҡ„йҡҗе–»пјҢдёҖж–№йқўе°ҳеҹғиҗҪе®ҡпјҢдёҖж–№йқўзҒөйӯӮдёҠеҚҮгҖӮйҳҝе·ҙдҝЎеҘүзҡ„иӢҜж•ҷи®ӨдёәпјҢиҚүжңЁйҖҡзҘһпјҢдёҮзү©жңүзҒөпјҢжүҖд»Ҙйҳҝе·ҙжІЎжңүж¶ҲеӨұгҖӮеңЁд№ҰеҪ“дёӯжңүдёҖдёӘеҺҹзӮ№пјҢзү©зҗҶеӯҰдёҠеҸ«еҘҮзӮ№пјҢе°ұжҳҜе®Үе®ҷеӨ§зҲҶзӮёиҝҷдёӘзӮ№пјҢе®Үе®ҷеӨ§ең°йңҮеҸ‘еҮәзҡ„еҫ®жіўиҫҗе°„еҲ°зҺ°еңЁжүҚиғҪзңӢеҲ°пјҢеҲ°зҺ°еңЁиҝҳжІЎжңүж¶ҲеӨұпјҢд»Һж•ҙдҪ“и§ӮжқҘзңӢпјҢж—¶й—ҙз©әй—ҙеҜ№дәҺжҲ‘们дёӘдҪ“зҡ„дәәжқҘиҜҙжҳҜеӯҳеңЁзҡ„пјҢдҪҶжҳҜеҜ№ж•ҙдҪ“жқҘиҜҙпјҢз©әй—ҙдёҚеӯҳеңЁпјҢж—¶й—ҙд№ҹдёҚеӯҳеңЁпјҢеғҸйҳҝе·ҙиөһеҸ№еҺҹжқҘж¶ҲеӨұзҡ„еұұеҸӘжҳҜеҸҳжҲҗеҸҰеӨ–дёҖдёӘж ·еӯҗпјҢд»Һж•ҙдҪ“и§ӮжқҘзңӢдә‘дёӯжқ‘зҷҫеҚҒжқҘдәәд№ҹйғҪеңЁе®Үе®ҷдёӯпјҢйҳҝе·ҙиҝҳе’Ңд»–зҡ„д№ЎдәІд»¬еңЁдёҖиө·пјҢеҸӘжҳҜи§Ҷи§’дёҚдёҖж ·гҖӮвҖқ
дёӯеӣҪдҪңеҚҸеҲӣиҒ”йғЁж°‘ж—ҸеӨ„еӨ„й•ҝйҷҲж¶ӣи°ҲеҲ°йҳҝе·ҙзҡ„жӯ»дәЎж—¶пјҢиҜҙпјҡвҖң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иҮӘе§ӢиҮіз»ҲиҙҜз©ҝзқҖиӢұйӣ„дё»д№үзҡ„жғ…иҠӮпјҢиҝҷз§ҚиӢұйӣ„дё»д№үеңЁзҘӯеёҲйҳҝе·ҙиә«дёҠеҫ—еҲ°дҪ“зҺ°пјҢжҲ‘д№ҹиөһеҗҢйҳҝе·ҙиҝҳжҳҜиҰҒжӯ»жҺүзҡ„пјҢж”Ҝж’‘д»–жҙ»дёӢеҺ»зҡ„ж„Ҹд№үжҳҜд»Җд№ҲпјҹеҪ“д»–иёҸдёҠдә‘дёӯжқ‘зҡ„ж—¶еҖҷпјҢд»–зҡ„е‘Ҫиҝҗе·Із»ҸжҳҜжіЁе®ҡзҡ„пјҢеӣ дёәдә‘дёӯжқ‘е°ұжҳҜдә‘дёӯзҡ„жқ‘иҗҪпјҢжіЁе®ҡиҰҒеӣһеҲ°еӨ©дёҠгҖӮжҲ‘еңЁиҜ»зҡ„ж—¶еҖҷд№ҹеңЁжғійҳҝе·ҙжҳҜи°ҒпјҢд»ҠеӨ©зҡ„дё–з•ҢжҳҜдёҚжҳҜзңҹзҡ„жңүйҳҝе·ҙиҝҷдёӘдәәпјҹеҗҺжқҘжҲ‘жғіиҝҷдёҖеҲҮйғҪдёҚйҮҚиҰҒпјҢйҮҚиҰҒзҡ„жҳҜйҳҝжқҘи®©жҲ‘们зӣёдҝЎйҳҝе·ҙжҙ»з”ҹз”ҹзҡ„еӯҳеңЁиҝҮпјҢ并且еңЁжҹҗдәӣең°ж–№дҫқ然еӯҳеңЁпјҢд»–её®жҲ‘们жҠҡж…°дәҶжӯ»еҺ»зҡ„дәЎзҒөпјҢд№ҹе®үжҠҡдәҶжҲ‘们зҡ„еҶ…еҝғпјҢд»–ж•ҷдјҡжҲ‘们еҰӮдҪ•д»ҘиҮӘ然зҡ„ж–№ејҸйқўеҜ№иҮӘ然е’ҢеӨ§ең°пјҢдёҚжҠұжҖЁең°йқўеҜ№дё–з•ҢпјҢйҳҝе·ҙд»Ҙиҷ”иҜҡзҡ„еҝғиө°еҗ‘жӯ»дәЎпјҢд»–йҮҠж”ҫеҮәйңҮйўӨдәәеҝғзҡ„жӮІеЈ®еҠӣйҮҸгҖӮвҖқ
дёӯеӣҪзӨҫдјҡ科еӯҰйҷўж–ҮеӯҰжүҖеүҜз ”з©¶е‘ҳеҫҗеҲҡи®ӨдёәпјҢе°ҸиҜҙеҰӮдҪ•и¶…еәҰгҖҒеҰӮдҪ•е‘Ҡж…°иҝҷдәӣж¶ҲеӨұзҡ„ж–ҮжҳҺдҪ“пјҢе…ід№ҺжҲ‘们д»ҠеӨ©жҖҺж ·зҗҶи§Јж–ҮеӯҰзҡ„еҠҹиғҪпјҢвҖңдҪңе“Ғдёӯзҡ„ж¶ҲеӨұгҖҒжӯ»дәЎпјҢйғҪжҳҜйқһеёёжғЁзғҲзҡ„пјҢйқһеёёе®һеңЁзҡ„пјҢдҪҶжҳҜж–ҮеӯҰдјҡи®©иҝҷдёҖеҲҮеҸҳеҫ—еқҰ然пјҢеҸҳеҫ—и®©жҲ‘们жҺҘеҸ—иҝҷдёҖеҲҮгҖӮиҝҷйҮҢйқўж— и®әжҳҜдёӘдҪ“зҡ„зүәзүІд№ҹеҘҪпјҢиҝҳжҳҜж–ҮжҳҺзҡ„зүәзүІд№ҹеҘҪпјҢйҳҝжқҘиҖҒеёҲзҡ„е·ҘдҪңжҳҜи®©жҲ‘们еҸҳеҫ—иғҪеӨҹжҺҘеҸ—е®ғгҖҒзҗҶи§Је®ғгҖӮйҳҝе·ҙзҡ„жӯ»пјҢжҹҗз§ҚзЁӢеәҰдёҠжқҘиҜҙпјҢжҳҜиӮүдҪ“дёҠзҡ„жӯ»дәЎпјҢе…¶е®һд»–жҳҜжҚўдёҖз§Қж–№ејҸеӯҳеңЁгҖӮиҝҷд№ҹжҳҜиҝҷдёӘе°ҸиҜҙеҸҚеӨҚе‘ҠиҜүжҲ‘们зҡ„пјҢж— и®әжҳҜдәәд№ҹеҘҪпјҢж–ҮжҳҺд№ҹеҘҪпјҢе®ғзҡ„жӯ»дәЎдёҚжҳҜзңҹзҡ„жӯ»дәЎпјҢиҖҢжҳҜжҚўдёҖз§Қж–№ејҸеӯҳеңЁгҖӮвҖқ
дё»жҢҒз ”и®Ёдјҡзҡ„дёӯеӣҪдҪңеҚҸеҲӣз ”йғЁдё»д»»дҪ•еҗ‘йҳіжҖ»з»“иҜҙпјҡвҖңдёҖдёӘдҪң家жңҖеӣһйҒҝдёҚејҖзҡ„жҳҜеӨ„зҗҶзҺ°е®һйўҳжқҗй—®йўҳпјҢеҰӮдҪ•еӨ„зҗҶзҺ°е®һйўҳжқҗдёӯзҡ„зҒҫйҡҫжҖ§зҡ„з”ҹе‘ҪдјӨз—•й—®йўҳпјҢиҝҷдёӘйҡҫеәҰйқһеёёеӨ§пјҢдҪҶжҳҜи§ЈеҶіиҝҷдёӘеӣ°йҡҫзҡ„й’ҘеҢҷеҸӘиғҪжҳҜдёҖдёӘдҪң家еҜ№з”ҹе‘Ҫзҡ„ж·ұзҲұпјҢйҳҝжқҘиЎЁиҫҫдәҶиҝҷз§Қж·ұзҲұпјҢиҝҷжҳҜз”ҹе‘Ҫе…ұеҗҢдҪ“зҡ„зҲұгҖӮеӣ дёәиҝҷз§ҚзҲұпјҢжүҖд»ҘжңүдәҶ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пјҢеӣ дёәжңүдәҶгҖҠдә‘дёӯи®°гҖӢпјҢйӮЈдәӣжӯ»дәҶзҡ„дәәйғҪеӣ дёәиҝҷжң¬д№ҰиҖҢиҺ·еҫ—дәҶеҸҰеӨ–дёҖз§Қж„Ҹд№үзҡ„еӨҚжҙ»гҖӮж„ҹи°ўйҳҝжқҘпјҢиҝҷд№ҹжҳҜд»ҠеӨ©жҲ‘们еңЁжӯӨз ”и®Ёиҝҷжң¬д№Ұзҡ„ж„Ҹд№үжүҖеңЁгҖӮвҖ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