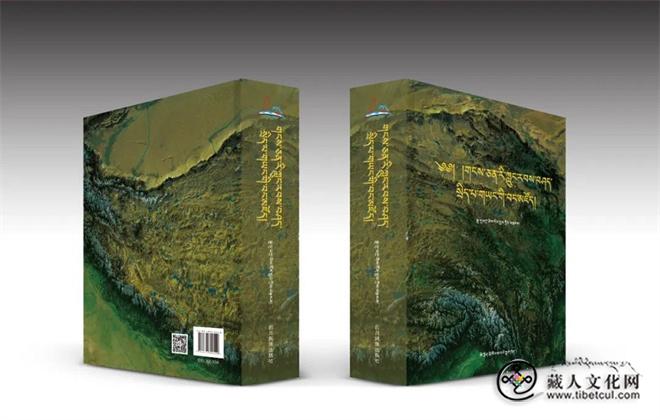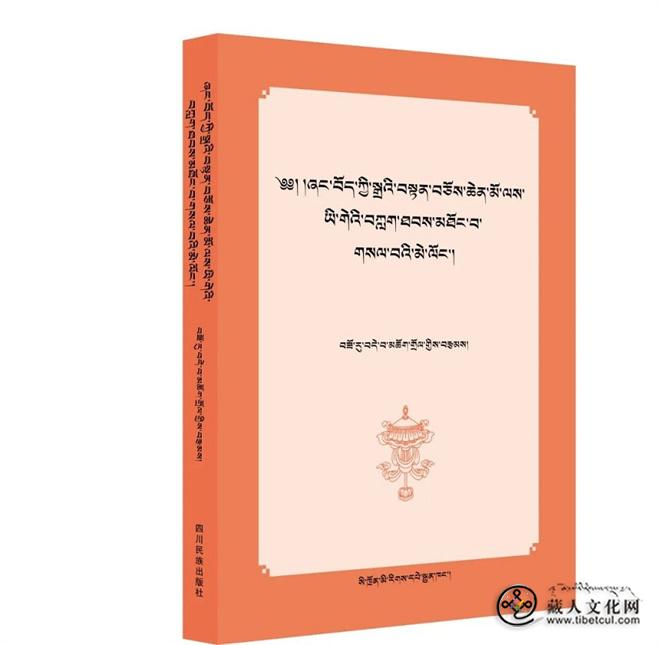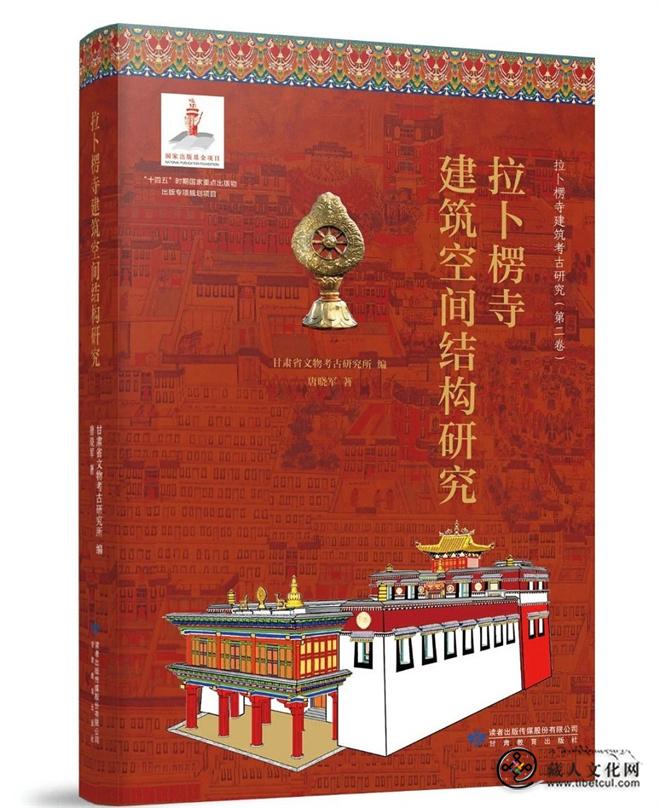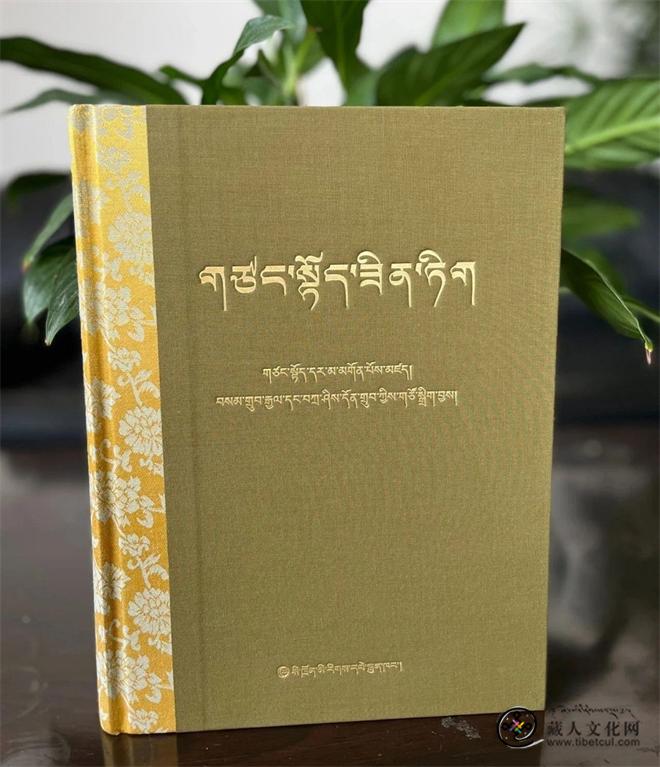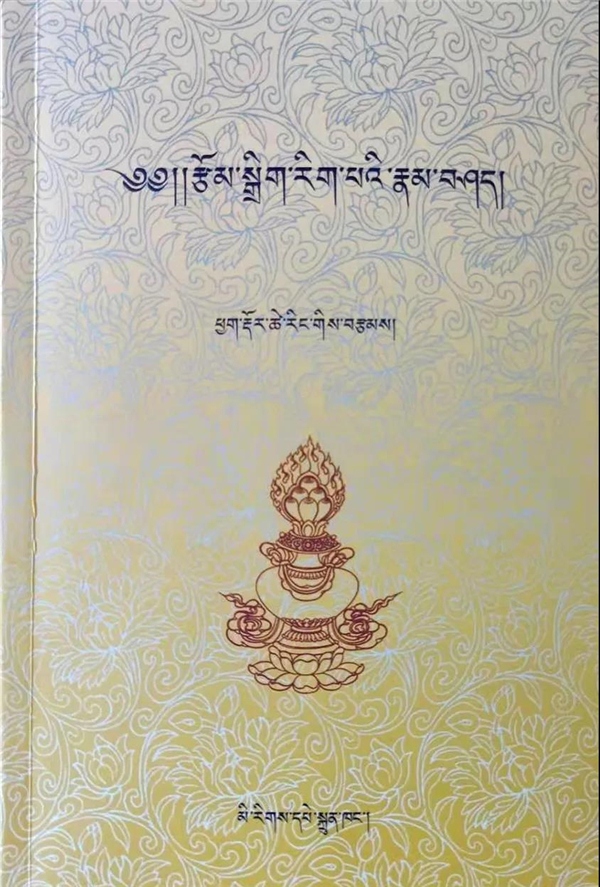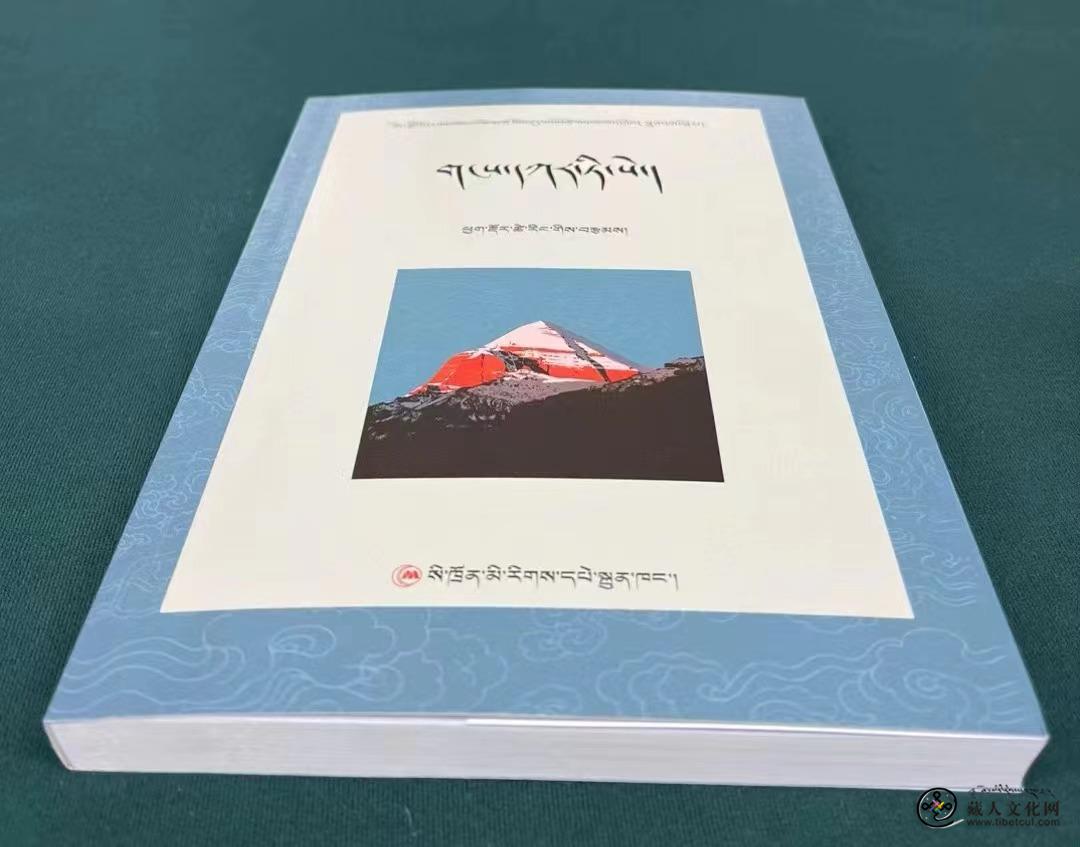гҖҖгҖҖ“жҲ‘зҡ„еҶҷдҪң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жёІжҹ“иҝҷзүҮй«ҳеҺҹеҰӮдҪ•зҘһз§ҳпјҢжёІжҹ“иҝҷдёӘй«ҳеҺҹдёҠзҡ„ж°‘ж—Ҹз”ҹжҙ»еҫ—еҰӮдҪ•и¶…然世еӨ–пјҢиҖҢжҳҜдёәдәҶзҘӣйҷӨйӯ…жғ‘пјҢе‘ҠиҜүиҝҷдёӘдё–з•ҢпјҢиҝҷдёӘж—ҸзҫӨзҡ„дәә们д№ҹжҳҜдәәзұ»еӨ§е®¶еәӯдёӯзҡ„дёҖе‘ҳгҖӮ他们жңҖжңҖйңҖиҰҒзҡ„пјҢе°ұжҳҜдҪңдёәдәә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зҘһзҡ„иҮЈд»ҶеҺ»з”ҹжҙ»гҖӮ”еҮӯеҖҹгҖҠжңәжқ‘еҸІиҜ—гҖӢпјҲе…ӯйғЁжӣІпјүиҺ·еҫ—“第дёғеұҠеҚҺиҜӯж–ҮеӯҰдј еӘ’еӨ§еҘ–·е№ҙеәҰжқ°еҮәдҪң家еҘ–”ж—¶пјҢдҪң家йҳҝжқҘиҝҷж ·иҜҙгҖӮ
гҖҖгҖҖиҝҷеҮ еӨ©пјҢйҳҝжқҘеёҰзқҖгҖҠжңәжқ‘еҸІиҜ—гҖӢеңЁеҗ„ең°дёҺиҜ»иҖ…и§ҒйқўпјҢеңЁдёҠжө·жҖқеҚ—иҜ»д№Ұдјҡзҡ„дёҖеңәеҜ№и°ҲдёҠпјҢд»–еҶҚж¬Ўз”Ё“дәәжҳҜеҮәеҸ‘зӮ№пјҢд№ҹжҳҜзӣ®зҡ„ең°”еҪ’зәіиҮӘе·ұзҡ„ж–ҮеӯҰи§ӮгҖӮд»–иҜҙпјҡ“жҲ‘еҒҸжү§ең°и®ӨдёәпјҢе°ҸиҜҙзҡ„ж·ұеәҰдёҚжҳҜжҖқжғіпјҢиҖҢжҳҜжғ…ж„ҹзҡ„ж·ұеәҰпјҢдҪ“йӘҢзҡ„ж·ұеәҰгҖӮж–ҮеӯҰзҡ„第дёҖиҰҒзҙ жҳҜиҜӯиЁҖпјҢ第дәҢиҰҒзҙ иҝҳжҳҜиҜӯиЁҖпјҢжҺ’еҲ°з¬¬дёҖзҷҫйӣ¶дёҖпјҢиҝҳжҳҜиҜӯиЁҖгҖӮ”
гҖҖгҖҖ1959е№ҙз”ҹзҡ„йҳҝжқҘ2000е№ҙеҮӯеҖҹй•ҝзҜҮе°ҸиҜҙгҖҠе°ҳеҹғиҗҪе®ҡгҖӢиҺ·з¬¬дә”еұҠиҢ…зӣҫж–ҮеӯҰеҘ–пјҢжҲҗдёәиҢ…зӣҫж–ҮеӯҰеҘ–еҸІдёҠжңҖе№ҙиҪ»зҡ„иҺ·еҘ–иҖ…гҖӮд»–зҡ„з®ҖеҺҶдёҠйҖҡеёёиҝҷж ·еҶҷйҒ“пјҡи—Ҹж—ҸгҖӮеҮәз”ҹең°пјҡеӣӣе·қзңҒ马尔еә·еҺҝпјҢдҝ—з§°“еӣӣеңҹ”пјҢеҚіеӣӣдёӘеңҹеҸёз»ҹиҫ–д№Ӣең°гҖӮйҳҝжқҘз§°иҮӘе·ұдёәдёҖдёӘз”ЁжұүиҜӯеҶҷдҪңзҡ„и—Ҹж—ҸдҪң家гҖӮжңүж—¶и°ҲеҲ°ж—ҸеҲ«пјҢд»–дјҡе№Ҫй»ҳең°иҜҙпјҡжҲ‘жҳҜдёҖдёӘиҝңзјҳжқӮдәӨе“Ғз§ҚгҖӮ
гҖҖгҖҖ“жҲ‘жҳҜдёҠе°ҸеӯҰжүҚејҖе§ӢеӯҰд№ жұүиҜӯзҡ„пјҢеӣ дёәиҜӯиЁҖдёҚйҖҡпјҢе°ҸеӯҰ第дёҖе№ҙдёҚиғҪдёҠиҜҫпјҢеҫ—д»Һз®ҖеҚ•зҡ„з»ҳз”»ејҖе§ӢеӯҰгҖӮеҗҺжқҘпјҢжҲ‘ж…ўж…ўеҸ‘зҺ°пјҢжұүиҜӯгҖҒзү№еҲ«жҳҜз”ЁжұүиҜӯеҶҷжҲҗзҡ„ж–ҮеӯҰдҪңе“ҒйҮҢпјҢеӨ§йҮҸз»ҸйӘҢжҳҜи—үз”ұиҜӯиЁҖжҸҗдҫӣзҡ„пјҢе’ҢжҲ‘з”ҹеӯҳзҡ„дё–з•ҢжІЎжңүе…ізі»гҖӮиҖҢжҲ‘еҚҙиҰҒз”Ёиҝҷз§Қж–°жҺҢжҸЎзҡ„иҜӯиЁҖжқҘи®Іиҝ°жҲ‘зҡ„з”ҹжҙ»пјҢе®ғеҸҜиғҪдјҡжҲҗдёәд»Җд№Ҳж ·пјҹ”йҳҝжқҘеӣһеҝҶпјҢ“еҪ“ж—¶жҲ‘жІЎжғіиҝҮжҲҗдёәдҪң家пјҢз”ҡиҮідёҚзҹҘйҒ“дё–з•ҢдёҠжңүдёҖз§ҚиҒҢдёҡеҸ«дҪң家пјҢдҪҶиҝҷдёӘй—®йўҳе§Ӣз»ҲеңЁеҝғеӨҙ——еҪ“жҲ‘们дҪҝз”ЁдёҖз§ҚиҜӯиЁҖпјҢдҪҶиҝҷдёӘиҜӯиЁҖдёӯ并没жңүеҢ…еҗ«иҮӘе·ұзҡ„з”ҹжҙ»з»ҸйӘҢпјҢиҖҢдё”д№ҹдёҚзҹҘйҒ“иҝҷз§Қз”ҹжҙ»з»ҸйӘҢеңЁж–°зҡ„иҜӯиЁҖдёӯеә”иҜҘеҰӮдҪ•иЎЁиҫҫж—¶пјҢжҖҺд№ҲеҠһпјҹжңҖеҗҺжҳҜзҝ»иҜ‘ж–ҮеӯҰй—ҙжҺҘең°и§Јзӯ”дәҶжҲ‘зҡ„з–‘жғ‘гҖӮзҰҸе…ӢзәіеҶҷзҡ„зҫҺеӣҪд№Ўжқ‘пјҢеҪ“жҲ‘们жҠҠе®ғзҝ»иҜ‘жҲҗдёӯж–Үж—¶иҜҘеҰӮдҪ•е‘ҲзҺ°пјҹжҜ”еҰӮзҰҸе…ӢзәіжңүдёҖдёӘе°ҸиҜҙеҸ«гҖҠзҶҠгҖӢпјҢеҶҷзҡ„жҳҜзӢ©зҢҺж–ҮеҢ–гҖӮзӢ©зҢҺеңЁжҲ‘иҮӘе·ұзҡ„з»ҸйӘҢдёӯеҪ“然еҫҲдё°еҜҢпјҢдҪҶеңЁжұүиҜӯдёӯеҮ д№ҺжІЎжңүиҝҷж ·зҡ„з»ҸйӘҢпјҢжІЎжңүдҪң家жҠҠе®ғжӯЈйқўеҪ“еҒҡдёҖз§Қж–ҮеӯҰеҜ№иұЎд№ҰеҶҷиҝҮгҖӮжҲ‘и§үеҫ—зҰҸе…Ӣзәізҡ„е°ҸиҜҙеҫҲжңүдәІеҲҮж„ҹпјҢиҮіе°‘жҜ”иҜ»гҖҠзәўжҘјжўҰгҖӢжӣҙдәІеҲҮпјҢеҸҚиҖҢж„ҹи§үеӨ–еӣҪе°ҸиҜҙзҰ»жҲ‘жӣҙиҝ‘гҖӮзҝ»иҜ‘иғҪжҠҠдёҖз§Қз»ҸйӘҢжҲҗеҠҹең°д»ҺдёҖз§ҚиҜӯиЁҖиҪ¬з§»еҲ°еҸҰдёҖдёӘиҜӯиЁҖдёӯпјҢиҖҢдё”иҝҳдҝқеӯҳеҫ—еҫҲйІңжҙ»гҖӮиҜӯиЁҖй—®йўҳжҳҜжҲ‘еңЁеҶҷдҪңиҝҮзЁӢдёӯжңҖйҮҚи§Ҷзҡ„пјҢеҸҜиғҪжӯЈжҳҜеӣ дёәжҲ‘зҡ„жҜҚиҜӯдёҚжҳҜжұүиҜӯгҖӮжҲ‘и§ӮеҜҹеҲ°зҡ„жұүиҜӯжј”еҸҳпјҢд»Һе…Ҳз§ҰеҲ°зҷҪиҜқж–ҮпјҢе®ғзҡ„дё°еҜҢе…¶е®һе°ұжҳҜдёҚж–ӯжҠҠејӮиҙЁж–ҮеҢ–зәіе…ҘиҮӘиә«иҜӯиЁҖзі»з»ҹдёӯзҡ„иҝҮзЁӢгҖӮжҲ‘з”ҡиҮіи§үеҫ—пјҢжҲ‘зҡ„еҶҷдҪңд№ҹжҳҜеңЁд»ҺдәӢжҹҗз§ҚзЁӢеәҰдёҠзҡ„зҝ»иҜ‘пјҢеёҢжңӣиғҪжңүж–°зҡ„иЎЁиҫҫпјҢеҜ№иҝҷдёӘдјҹеӨ§зҡ„иҜӯиЁҖдҪңеҮәдёҖзӮ№ж–°зҡ„иҙЎзҢ®гҖӮ”
гҖҖгҖҖеӨҡе№ҙжқҘпјҢйҳҝжқҘдёҖзӣҙжғідёәдёҖдёӘеҸӨиҖҒзҡ„и—Ҹж—Ҹжқ‘еә„еҶҷдёҖйғЁиө°еҗ‘ж–°з”ҹзҡ„еҺҶеҸІпјҢиҝҷе°ұжңүдәҶиҝҷйғЁж—§еҲ¶еәҰиў«жҺЁзҝ»еҗҺпјҢдёҖдёӘи—Ҹж—Ҹжқ‘иҗҪзҡ„еҪ“д»ЈеҸІгҖӮеҰӮжһңиҜҙгҖҠе°ҳеҹғиҗҪе®ҡгҖӢеҘҪжҜ”дёҖжқЎйЈҳйҖёзҒөеҠЁгҖҒеҲӣз”ҹдј еҘҮзҡ„жІіжөҒпјҢйӮЈд№ҲгҖҠжңәжқ‘еҸІиҜ—гҖӢе°ұжҳҜе…ӯеә§жңҙе®һжІүзЁігҖҒйҮҚзҺ°еҺҶеҸІзҡ„еұұеіҰ——е®ғ们зӣёйӮ»зқҖж•ЈеёғеңЁеӨ§ең°дёҠпјҢзңӢиө·жқҘзӣёдә’зӢ¬з«ӢпјҢеҶ…йғЁеҚҙж №и„үзӣёиЎ”пјҢеҗҲиҖҢе‘ҲзҺ°дәҶдёҖе№…зҫӨеұұ并з«ӢејҸзҡ„еҪ“д»Ји—Ҹж—Ҹд№Ўжқ‘е…ЁжҷҜгҖӮжӯЈеҰӮе…ӯйғЁжӣІд№ӢеҗҚжүҖзӨәпјҢйҳҝжқҘиҜҙпјҢиҝҷжҳҜ他继гҖҠе°ҳеҹғиҗҪе®ҡгҖӢд№ӢеҗҺпјҢеҸҲдёҖж¬Ў“дёӢе®ҡеҶіеҝғеҶҷдёҖзӮ№жүҖи°“еҸІиҜ—жҖ§зҡ„дёңиҘҝ”гҖӮ
гҖҖгҖҖгҖҠжңәжқ‘еҸІиҜ—гҖӢз”ұе…ӯйғЁжӣІз»„жҲҗпјҢжҜҸйғЁеҸҲеҲҶеҲ«з”ұдёҖйғЁе°Ҹй•ҝзҜҮгҖҒдёҖзҜҮдәӢзү©з¬”и®°е’ҢдёҖзҜҮдәәзү©з¬”и®°е…ұеҗҢз»„жҲҗгҖӮд№ӢжүҖд»ҘйҖүжӢ©иҝҷж ·дёҖз§ҚеҪўејҸпјҢйҳҝжқҘиҜҙпјҢжҳҜеӣ дёәж•…дәӢзҡ„йңҖиҰҒгҖҒзҺ°е®һзҡ„жҠҳе°„пјҢиҖҢйқһеҲ»ж„ҸиҝҪжұӮз»“жһ„зҡ„зӘҒз ҙгҖӮ“зҺ°еңЁпјҢжҲ‘们з»Ҹеёёз”Ё‘з ҙзўҺ’еҪўе®№д№Ўжқ‘пјҢе…¶е®һз ҙзўҺзҡ„иҝҮзЁӢеҫҲж—©е°ұејҖе§ӢдәҶгҖӮгҖҠе°ҳеҹғиҗҪе®ҡгҖӢйҮҢпјҢдёҖдёӘ家ж—ҸиҙҜз©ҝе§Ӣз»ҲпјҢе§Ӣз»ҲеңЁиҲһеҸ°дёӯеӨ®гҖӮеҰӮд»ҠпјҢд№Ўжқ‘е·Із»ҸеӨұеҺ»дәҶиҮӘе·ұзҡ„дёӯеҝғпјҢеңЁдёӯеҝғдҪҚзҪ®зҡ„дәәйҡҸж—¶еҸҳеҢ–гҖӮдёәд»Җд№ҲжҳҜ‘е…ӯйғЁжӣІ’пјҹжҜҸиҝҮ10жқҘе№ҙпјҢд№Ўжқ‘е°ұеҸҳдёҖж¬ЎпјҢи°ҒеңЁдёӯеҝғпјҢи°ҒжңҖиғҪд»ЈиЎЁж—¶д»Јзҡ„зү№еҫҒпјҢжҲ‘е°ұеҶҷи°ҒгҖӮеҸҜиғҪдёҖдёӘдәәзү©еңЁз¬¬дёҖйғЁе°ұжңүзҷ»еңәпјҢ第дәҢйғЁиө°еҲ°дәҶиҲһеҸ°дёӯеҝғпјҢ第дёүйғЁйҮҢиҝҳжҳҜжңүд»–пјҢдҪҶеҲ°дәҶиҫ№зјҳгҖӮеҸӘжңүиҝҷж ·зҡ„з»“жһ„жүҚиғҪеҜ№еә”д№Ўжқ‘зҡ„зҺ°е®һгҖӮ”
гҖҖгҖҖйҳҝжқҘиҜҙпјҢд№ҹи®ёеҶҚиҝҮ20е№ҙпјҢд»–иҝҳдјҡеҶҚеҶҷд№Ўжқ‘пјҢеҶҚд»ҘеҚҒе№ҙдёәдёҖдёӘеҚ•дҪҚпјҢеҶҷдёҖеҶҷж–°дё–зәӘзҡ„еҶңжқ‘ж–°зҡ„еҸҳеҢ–гҖӮдҪҶйўҳжқҗпјҢ并дёҚжҳҜи®Ёи®әж–ҮеӯҰзҡ„ж ҮеҮҶпјҢзҺ°е®һдё»д№үд№ҹ并йқһеҜ№зҺ°е®һзҡ„з…§зӣёејҸзҡ„и®°еҪ•гҖӮдҪң家еҜ№иҮӘе·ұжүҖе‘ҲзҺ°зҡ„еҜ№иұЎиҝҳжҳҜиҰҒжңүдёҖзӮ№и¶…и¶ҠжҖ§пјҢиҝҷз§Қи¶…и¶ҠеҸҜиғҪжҳҜд»Һж–ҮеҢ–еұӮйқўзҡ„и§ӮеҜҹпјҢжҲ–жҳҜдәәжҖ§гҖҒдәәйҒ“жҖқжғізҡ„з¬јзҪ©пјҢдҪҶжңҖйҮҚиҰҒзҡ„иҝҳжҳҜйҖҡиҝҮиҜӯиЁҖе»әжһ„иҮӘ然иҖҢ然дә§з”ҹзҡ„иҜ—ж„ҸгҖӮ“жҲ‘们иҰҒеҒҡзҡ„е°ұжҳҜеңЁиҜ—ж„ҸдёҖйңІеӨҙж—¶зҙ§зҙ§жҠ“дҪҸе®ғпјҢдҪҶеңЁеҫҲеӨҡе°ҸиҜҙдёӯпјҢжҲ‘们зңӢеҲ°пјҢиҝҷз§ҚиҜ—ж„ҸеҸҜиғҪй—ӘзғҒдёҖдёӢдҫҝж¶ҲеӨұдәҶпјҢеҶҚеәҰе •е…ҘзҗҗзўҺгҖҒеәёдҝ—зҡ„дё–дҝ—дёӯпјҢиҝҷж ·зҡ„ж–ҮеӯҰе°ұеӨұеҺ»дәҶж„Ҹд№үгҖӮ”йҳҝжқҘиҜҙ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