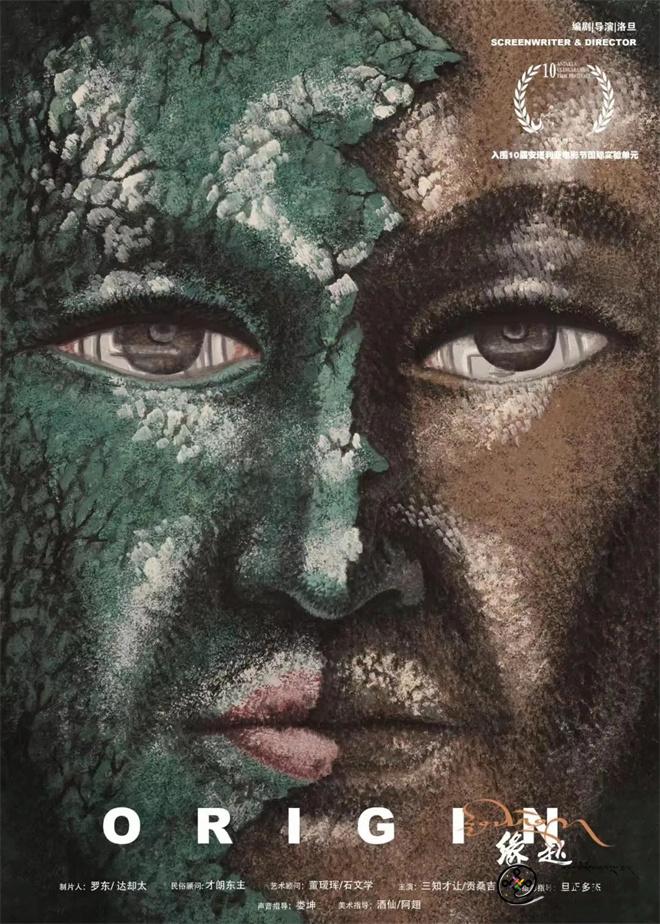喜欢现代舞的人,一定对《那一年 这一天》、《无以名状》、《前定的暗色》、《火柴人》这些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现代舞作品不会陌生。然而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作品的编者是谁呢?这些作品又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在什么环境中诞生的呢?当那触动心灵的舞蹈令你有如受到火的炙烤与冰的面膜,你会去挖掘这舞蹈背后的故事吗?你会有要与舞者、编舞者对话的冲动吗?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然这些作品的有效性将被存疑?其实要走进舞者与编舞者的内心,看起来是件很困难的事,但如果去尝试,未必不会有意外的收获与可能。比如我们刚说到的这些有名的舞蹈作品,它的作者就是桑吉加,一位在现代舞领域中备受注目的创作人。现代舞圈子里的同行和朋友都喜欢亲切地叫他“桑巴”,而不是:桑吉加。似乎桑巴是个更有魔力的舞蹈的符号,它可以让创作者起飞一样,也让国内的现代舞,多出一种语汇。
因为热爱自由地释放而选择现代舞
在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见到桑巴,其高大魁梧的身影倏地撞入眼帘,让我不禁感慨:实在是人如其名——一米八几的高个儿,因长年习舞养成的潇洒气质,让他的每一步每一行都饱溢着西部男人的力量——挺拔而刚强。可是,当我们就现代舞展开交谈,他文雅的语气、谦恭的姿态以及时不时不经意间加上的英语语助词“恩哼”,又透露出他特有的柔软和温情一面。
采访过程中,与他细聊学习、推广现代舞的从艺历程,言语之间对于现代舞的深邃理解和用诠释无不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只有当一个人全身心的喜爱、投入并为此孜孜不倦,他才能深谙他所从事的任何行当其中的趣致、伦理和况味。
虽然距离动辄回忆往事的年纪尚远,可是,仍然可以这样说,桑巴的习舞之路颇具几分创奇色彩。
中国的现代舞并没有形成民间舞、芭蕾舞那样大规模的普及度,从艺者并不多,而在这小众的群体之中,桑巴身上的藏族身份更是加重了外界对他的好奇和关注。甚至,这为他莫名赢得了“中国藏族现代舞第一人”的称号,然而,在桑巴自己看来,藏族血统并没有对他学习和表演现代舞有太多的促发作用。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有座著名的拉卜楞寺,保留有全国最好的藏传佛教教学体系,桑巴的老家就在这附近。在十二岁之前的时光里,幡旗经鼓、磕长头的香客、虔诚的诵经声……构成了一个少年的全部生活。直到1986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一群挑选苗子的舞蹈老师的突然出现,才使这个藏族少年的命运有了转机。当他脱下笨重的马靴,穿上轻盈的舞鞋,与舞蹈的结缘便有了开始。
尽管他长手长脚,先天条件优异,可是,桑巴清楚地记得:他的胯是伴随着泪水,硬被老师拉开的。因为同班的大部分孩子出身世家,已能够在把杆上听着口令娴熟的做出‘一位全蹲,一位半蹲……’的动作,而只有他是丑小鸭,课堂上教的动作与他们在草原上随心所欲的“锅庄”有着很大的区别。“那时学跳各种民族舞蹈,每一种都有它固定的动作和套路,你只能一招一式跟着学,当个模仿者,这样的舞蹈缺少自我,缺少对个体的生命的思考。”桑巴说。
经过六年的勤学苦练,桑吉加成长为一名能够生动表演各民族民间舞蹈的优秀舞者,并在桃李杯比赛中初露锋芒,斩获民间舞十佳演员奖等奖项。如果留在母校任教,桑巴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民间舞教师。可是,命运再次在转角处找到了新的方向。正如桑巴自己所言,“人生总会遇到一些重要的十字路口,在这个时候,指引我做出抉择的是那颗追求自由的心。”
1991年,广东现代舞团到京演出,桑巴去观摩,顿时被现代舞自由的样式,能极大展露生命的爆发力的舞蹈风格深深吸引。他说“我要跳这样的舞蹈!”舞蹈应该是有生命,有情感,应该是自由的!1993年,他抛弃掉学业,毅然收拾行囊南下,加入了广东现代舞团。尽管拥有民间舞的底子,可是,要完成两种完全不同舞种的转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常年接受讲究刻板套式的民间舞训练的他,要投入到以“释放自己”为精髓的现代舞中,第一个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抛弃过去的沉重自我。
于是,他疯狂地利用一切时间练舞,像一个陀螺,在疾速的旋转中将往昔的“我”全然甩出去,完成蜕变,这一过程有如置身在炼丹炉里的孙悟空,那种被熊熊烈焰烧灼的痛苦,唯有自知。蚕蛹化成蝴蝶,一切付出也终于迎来回报。1996年,他获得“第七届法国巴黎国际舞蹈大赛”现代舞男子独舞金奖,这一奖项也为他带来“最完美的舞者”的国际荣誉。他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扑朔》、《晃》、《一九七九》、《同志》、《静静地坐着》等也应邀参加世界各地的展演、巡演。
大概向往自由是所有藏族人的天性,这种性格促使桑巴选择更接近自由——无论从肢体还是灵魂的现代舞。当中国现代舞还属方兴未艾,远远未成气候的萌芽阶段,他的选择自然会令旁人大惑不解。因此,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相当勇敢的人,这种勇敢不仅表现在他敢勇于打破自我,挑战成规,还表现在他在大师面前的从容气度。
携同舞者穿行在舞蹈思想的监界
2002年,二十多位顶尖艺术大师组成的世界级评审团为“劳力士艺术大师启蒙计划”在全球众多舞蹈家的资料中评选出三位候选人,最后由舞蹈界泰斗威廉·弗斯特(William Forsythe)亲自面试选出一人作为自己的入室弟子,赴德学习编舞。在面试场上,当大师问他“你想跳一段什么舞给我看?” 与其他谦逊到亦步亦趋的参选者不同,桑巴大胆地回答道:“我想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两个小时内,您编一段舞给我,然后我再根据您给我的元素再编一段舞给您,我们都来即兴的,可以吗?”桑巴在权威面前的无畏和热情,以及对于现代舞的热爱和才情打动了大师,于是他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也成为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舞蹈家。
桑巴在2003年底到德国学习,本来是以一年为期,却因为威廉·弗斯特的挽留,一呆就是3年。从学徒到演员到排练助手,随着法兰克福芭蕾舞团周游列国,三年的欧洲游历大开桑巴的眼界,现代舞技艺与思想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2006年,许多国际知名艺术团体表达了希望他能够加盟的愿望,桑巴再次处于人生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然而,他再次做出了一个重大选择:回到祖国。就像桑巴自己描述的那样:“在我的生命中有两样最重要的寄托:一个是现代舞,它是吸引我不断前进、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动力;一个是家乡,它是承载我人生经历,使我能够回望的心灵依托。”
多年的“向外求学”,桑巴在现代舞专业方面取得了不少真经,认为现代舞的“解放思想”其实就是做一些“反常态的艺术生活”。在他回国之后,他逐渐完成着从舞者到编舞的转变,先后有《无以名状》《火柴人》等作品出自他的创意,这是他从威廉·弗斯特那里学到的营养:“别陷在自己的位置,看不到面前的演员,他们不应当成为你的工具,要试着把他们的个性拿到你的作品中来。”
桑巴是个随性的人,这表现在他与舞者的互动中,他从不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让演员们看图片,或者给他们一个Idea让他们自己体会,或者干脆就多听听他们讲自己的身体故事。
桑巴以其对现代舞的执著,穿行在舞蹈思想的监界。威廉·科西曾经评价桑巴是“未被污染的水”,这话在我眼观了他的作品和其深入交谈之后更得以深刻地印证。他不是个善谈的人,他的话语更多是舞动着的肢体,他将他的所思所想都安放在了舞台上的跳跃的身体中。他常会忘记“我”的存在,甚至忘记时间,以及时间在身体上的划痕,他满心欢喜地投入在释放中——那是属于他,也属于喜爱他的观众的现代舞桥段。
希望观众关注作品本身多于关注个人
舍客:你怎么看待“藏族现代舞第一人”这个名号?你的藏族血统和文化背景给你今天在现代舞上的成就带来了什么?
桑吉加:大家这样称呼我,我其实很无奈。这些称呼对我影响不大,对于我来说,我更在意自己的喜好。其实,你说的藏族血统对我的艺术经历没有太多关联。我在跳舞或者编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把它赋予太多的藏族色彩,我只会加入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现代舞已经让很多观众觉得难以理解,我不想因为我的身份加重这种神秘的包装色彩。我倒希望观众关注作品本身多于关注我这个人。
舍客:怎么评价你和威廉·弗西斯之间的关系?你从他身上学到什么样的精髓?
桑吉加:每个人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非常不容易,我非常幸运找到了人生之最爱。我从香港飞过去,能和威廉有两个小时的对话,已经觉得很满足。他本身的人格魅力吸引到了我。作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他从事创作的投入度和专注度以及在艺术上的不断超越精神感染了我,他可以扔掉以前几十年的积累,做出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启发着我。很多艺术家出名之后仍然牢牢抓住赖以成名的那个“点”,不断地重复自我,可是威廉却在不断地否定,否定之后再向前。这让我受益匪浅,也深受感动。再加上他本身的和善,愿意回答你任何一个无知的问题,绝不会表现出任何的不耐烦。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师风范。
舍客:你敢用对话的方式迎接他的挑选,在我看来很勇敢,一般人只会按照他的要求被动而为,这是你的个性使然么?
桑吉加:我的个性的确是这样,我不那么愿意墨守成规。国外的这些艺术家很尊重你的想法,非常愿意倾听你的心声。他们不会要求我作为一个舞者完全按照他们的概念去跳,而去尊重和保护你个性化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个性的展示最重要。这需要一种宽容和大度,他能放得下自己。
如今我作为一个编导,从来不会骂人,只会尽可能去观察舞者身上的特质,而不是我强求让他改变成跟我一样。所以,舞者跟我合作相对轻松,他们会按照他们的理解完成我需要的东西,主动地投入,而不是被动地重复我的想法。只是接受动作命令和指示的演员,我其实也不喜欢。舞蹈其实是一个集体行为,所有的舞者都可以给我提供各种思考和实践的可能性。
舍客:这是中国教育讲求的那种“教学相长”?
桑吉加:对,一定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一定是所有人集体而为的结果。
编舞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
舍客:当年结束了游学,为什么选择回国发展?
桑吉加:我出去时就想着要回来,这本身就不是一种重复。我想把四年的学习进行一个梳理,回来从事创作和思考。我非常喜欢编舞,它涉及的面更广,需要更多的学习和消化,这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从文学、音乐、美学角度更多地考量,可是舞者只是一个舞者,对我来说已经不够了。现代舞真的可以提供机会让你学习更多。学习是人生最大的一个价值体现。
舍客:从舞者到编舞,这之间需要完成怎样的角色转换?一个优秀的编舞,最核心的素质应该是什么?
桑吉加:我的转换并不是那么突然,1993年并不懂现代舞的时候,在曹诚渊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就已经开始尝试自编自演,在广东现代舞团,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作品都出自普通舞者,所以,在我身上,并没有发生大的SHIFT,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我现在仍然还是一个演员,只是不像年轻时演出那么多,转换了职业重心而已。
一个优秀的编舞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统筹者,光有专业知识还不够,还需要把不同人的好的想法凝聚在一起。跳舞和编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在练脑子,而不是简单地练身体。
舍客:中国当下的许多现代舞者几乎全来自民间舞、芭蕾舞等其他舞种,就像你一样,这种转换痛苦吗?
桑吉加: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许多人也退回到他们来的领域。可能一个套式真的是很难打破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完全突破自我。总的来说,当你真心投入,这种改变并不是很难。
中国缺少科学的舞评体系与成熟的“艺术消费”
舍客:评价一下如今中国观众对于现代舞的欣赏水平,你在编舞过程中怎么兼顾你自己的理解和媒体、公众的接受度?
桑吉加:中国的观众很厉害,他们比你聪明很多,你只有一双眼睛,而观众有成千上万双眼睛,他们会带着他们的阅历、知识和想法来观看现代舞,但是,中国缺少关于如何评价现代舞的引导和教育,一种科学的舞评体系并不存在。在中国当下,常常存在掺杂着强烈的个人喜好的评论,这都是不理智的,对于现代舞在中国的推广也是不利的。你们媒体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舍客:如果你编导的现代舞作品有观众反映看不懂,你怎么办?
桑吉加: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许多西方国家的观众也表示看不懂现代舞,当然,这也正是现代舞的魅力所在,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给观众自由发挥和理解留下了更多空间。可能许多观众,没有打开自己的心,投入到作品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他们没有动脑子。我其实在规避“叙事”,因为舞蹈作品一旦讲故事,就会变成“哑剧”,抹去了肢体、力量、节奏等元素,这对舞蹈的魅力都有所伤害。观众需要运用抽象的思维、情绪去“阅读”动作与动作之间的关系,这种阅读的习惯是需要培养和改变的。
舍客:你呆过很多舞团,怎么比较中外舞团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桑吉加:在任何国家,现代舞团都不是一个盈利机构,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比如香港,舞团的运营都得到了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然而在国内,现代舞团的生存更多地是一种个体行为,仅仅依靠赞助的活法就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中国,也不可能依靠票房来满足资金问题,当越来越高的定价却被政府买单成为赠票,而不是由普通老百姓出于对艺术的真正喜爱而自觉购票,用艺术来养活艺术,用作品养活团体,真的就是一厢情愿。再次,我呼吁成熟的“艺术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