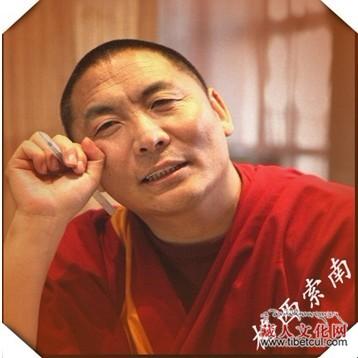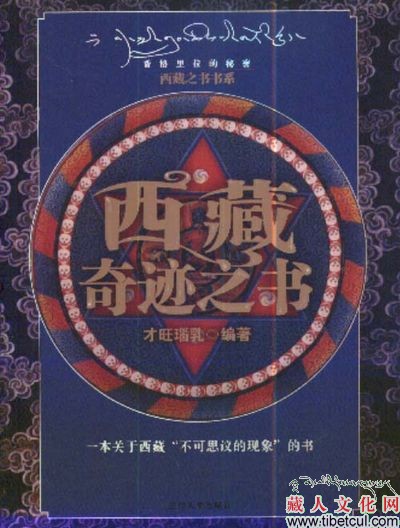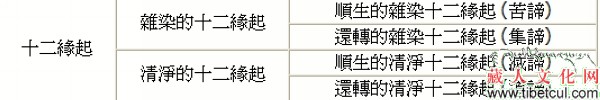вҖң
вҖңдҪӣеӯҰвҖқеҸ‘жәҗиҮӘвҖңиҘҝж–№вҖқзҡ„еҚ°度пјҢдј иҮівҖңдёңж–№вҖқзҡ„дёӯеӣҪгҖҒж—Ҙжң¬гҖҒжңқйІңиҖҢзӣӣеӨ§вҖҰвҖҰ然иҖҢпјҢжҜ”д№ӢеҚ°度пјҢжӣҙиҝңзҡ„ вҖңиҘҝж–№вҖқвҖ”вҖ”欧жҙІд№Ӣиҝ‘зҺ°д»Јзҡ„вҖңдҪӣеӯҰвҖқз ”з©¶пјҢеҚҙдҪҝеҫ—еҚҒд№қгҖҒдәҢеҚҒдё–зәӘд№Ӣй—ҙпјҢдҪңдёәеӯҰжңҜзҡ„вҖңдҪӣеӯҰвҖқз ”з©¶пјҢеҸҲд»Һжӣҙиҝңзҡ„вҖңиҘҝж–№вҖқвҖ”вҖ”欧жҙІпјҢеӣһдј еҲ°вҖңдёңж–№вҖқзҡ„ж—Ҙжң¬гҖҒдёӯеӣҪвҖҰвҖҰгҖӮвҖңдҪӣеӯҰвҖқдҪңдёәдёҖй—ЁзҺ°д»ЈеӯҰжңҜзҡ„еҲҶж”ҜвҖҰвҖҰдјјд№Һе§Ӣз»Ҳж‘ҶиҚЎдәҺвҖңдёңж–№вҖқдёҺвҖңиҘҝж–№вҖқд№Ӣй—ҙвҖҰвҖҰвҖңиҘҝж–№вҖқе®—ж•ҷж–ҮеҢ–зҡ„ж ёеҝғпјҢжҳҜвҖңеҹәзқЈж•ҷвҖқпјҢеҹәзқЈж•ҷеңЁиҘҝж–№еҸ‘еұ•了дёӨеҚғеӨҡ年пјҢз»ҸеҺҶдәҶж–ҮиүәеӨҚе…ҙгҖҒе®—ж•ҷж”№йқ©гҖҒ科еӯҰдёҺе·Ҙдёҡж–ҮжҳҺзҡ„жҙ—зӨјвҖҰвҖҰеңЁи®ёи®ёеӨҡеӨҡзҡ„еҸҳеҢ–гҖҒеҶІеҮ»дёӢпјҢ延з»ӯиҮід»Ҡзҡ„вҖңеҹәзқЈж•ҷвҖқзҘһеӯҰпјҢиғҪз»ҷеҗҢж ·еҺҶз»Ҹи®ёеӨҡеҸҳеҢ–дёҺеҶІеҮ»зҡ„вҖңдёңж–№вҖқе®—ж•ҷж–ҮеҢ–ж ёеҝғд№ӢдёҖвҖ”вҖңдҪӣж•ҷвҖқпјҢд»Җд№Ҳж ·зҡ„еҗҜзӨәдёҺеҸҚжҖқе‘ўпјҹ
йҰ–е…ҲпјҢжҲ‘们е…ҲжқҘеҸӮзңӢжі•еӣҪеҹәзқЈж•ҷзҘһз§ҳдё»д№үпјҲMysticismпјҢеҸҰиҜ‘вҖңеҜҶеҘ‘дё»д№үвҖқпјүжҖқжғіе®¶иҘҝи’ҷеЁң‧и–ҮдҫқпјҲSimone WeilпјҢ1909пҪһ1943пјүзҡ„и§ӮзӮ№гҖӮи–ҮдҫқжҳҜиў«иӘүдёәвҖңеҪ“д»Јеё•ж–ҜеҚЎе°”пјҲPascal,1623пҪһ1662пјүвҖқзҡ„дёҖдҪҚдјҹеӨ§жі•еӣҪеҘіжҖ§пјҢдёҖдҪҚиә«дҪ“еҠӣиЎҢеҹәзқЈзІҫзҘһпјҢ并具жңүй«ҳиҙөгҖҒеңЈжҙҒгҖҒеҜ№иӢҰйҡҫз”ҳд№ӢеҰӮйҘҙзІҫзҘһзҡ„еҘіжҖ§пјҢеҘ№д»ҘеҘ№иҮӘе·ұзҡ„еҝғзҒөеҺ»жӢҘжҠұдёҠеёқпјҢ并жӢ’з»қеҸ—жҙ—гҖҒжӢ’з»қеҸӮдёҺеңЈдәӢпјҢзҪ®иә«дәҺж•ҷдјҡе’ҢеҹәзқЈж•ҷеӣўдҪ“д№ӢеӨ–вҖҰвҖҰгҖӮи–ҮдҫқжҖқжғідёӯжңҖе…·дәүи®®жҖ§зҡ„дёҖзӮ№д№ғжҳҜпјҡвҖңеҹәзқЈзІҫзҘһдёҺеҹәзқЈе®—ж•ҷзҡ„еҢәеҲҶвҖқгҖӮеҘ№и®ӨдёәпјҡвҖңеҹәзқЈ精神不зӯүеҗҢдәҺеҹәзқЈе®—ж•ҷпјҢдҝЎд»°еҹәзқЈ不зӯүдәҺдҝЎд»°еҹәзқЈж•ҷпјҢжҲҗдёәеҹәзқЈеҫ’不зӯүдәҺжҲҗдёәеҹәзқЈж•ҷеҫ’пјҢеҸҚд№ӢдәҰ然гҖӮи–Үдҫқи®ӨеҗҢеүҚиҖ…пјҢиҖҢйқһеҗҺиҖ…гҖӮеҘ№дёҖзӣҙ不ж„ҝеҸ—жҙ—е…Ҙж•ҷвҖҰвҖҰвҖқ
з®ҖеҚ•ең°еҖҹз”Ёи–Үдҫқиҝҷж ·зҡ„жҖқжғіпјҢжҲ–и®ёд№ҹеҸҜд»Ҙз”ЁеңЁдҪӣж•ҷдёҺдҪӣж•ҷеҫ’дёҠпјҡдҪӣйҷҖзҡ„зІҫзҘһпјҢдёҚзӯүеҗҢдәҺдҪӣж•ҷзҡ„зІҫзҘһпјӣдҝЎд»°дҪӣйҷҖпјҢдёҚзӯүдәҺдҝЎд»°дҪӣж•ҷпјӣжҲҗдёәдҪӣйҷҖзІҫзҘһзҡ„иҝҪйҡҸиҖ…пјҢдёҚзӯүеҗҢдәҺжҲҗдёәдҪӣж•ҷеҫ’гҖӮдҪӣж•ҷеҸ‘еұ•дәҶеҚғзҷҫе№ҙпјҢйҡҫе…Қжңүдәӣи®ёдәәдёәгҖҒз»„з»ҮгҖҒж•ҷд№үеҸ‘еұ•вҖҰвҖҰзӯүзҡ„зјәйҷ·дёҺж— жі•йҖӮеә”ж—¶д»Јзҡ„зҠ¶еҶөпјҢйҮҚж–°еӣһеҪ’вҖңдҪӣйҷҖзІҫзҘһвҖқгҖҒиҝҪйҡҸвҖңдҪӣйҷҖзІҫзҘһвҖқпјҢжҲ–и®ёжҳҜдёҖдёӘеҖјеҫ—жҲ‘们ж·ұжҖқзҡ„иҜҫйўҳвҖҰвҖҰ更еҖјеҫ—ж·ұжҖқзҡ„жҲ–и®ёжҳҜпјҡвҖңдҪӣйҷҖзІҫзҘһвҖқпјҢдҪңдёәжңүеҲ«дәҺе…¶е®ғе®—ж•ҷзҡ„ж ёеҝғзҗҶи®әеҲ°еә•жҳҜд»Җд№ҲпјҹжҺҘзқҖпјҢжҲ‘们жқҘеҸӮиҖғеӨ©дё»ж•ҷзҘһеӯҰ家еҚЎе°”‧拉зәіпјҲKarl Rahner,1904пҪһ1984пјүеңЁд»–зҡ„зҘһеӯҰдәәзұ»еӯҰз»Ҹе…ёд№Ӣи‘—гҖҠеңЈиЁҖзҡ„еҖҫеҗ¬иҖ…гҖӢдёӯзҡ„и§ӮзӮ№гҖӮ拉зәіи®ӨдёәпјҡвҖңдәәеңЁд»–зҡ„жҜҸдёҖдёӘи®ӨиҜҶе’Ң行дёәдёӯ都еҗҢж—¶иӮҜе®ҡзқҖзҡ„д»–зҡ„иҝҷз§Қеҹәжң¬зҙ иҙЁпјҢжҲ‘们用дёҖдёӘиҜҚ來иЎЁзӨәе°ұеҸ«еҒҡвҖң精神жҖ§вҖқпјҲGeistigkeitпјүгҖӮдәәеҚі精神пјҢиҝҷе°ұжҳҜ說пјҢд»–жҖ»жҳҜеңЁдёҖз§ҚжҢҒз»ӯ不ж–ӯең°еҗ‘зқҖз»қеҜ№иҖ…зҡ„иҮӘжҲ‘дјёеұ•дёӯпјҢеңЁеҜ№дёҠеёқзҡ„ејҖж”ҫ狀жҖҒдёӯ度иҝҮд»–зҡ„дёҖз”ҹвҖҰвҖҰдәәд№ӢжүҖд»Ҙдёәдәәд»…д»…з”ұдәҺд»–жҖ»иө°еңЁйҖҡеҗ‘дёҠеёқд№Ӣ路дёҠпјҢ不з®Ўд»–жҳҜеҗҰжҳҺзЎ®зҹҘйҒ“иҝҷдёҖзӮ№пјҢеӣ дёәд»–еҜ№дёҠеёқж°ёиҝңдҝқжҢҒзқҖдёҖдёӘжңүйҷҗиҖ…д№Ӣж— йҷҗзҡ„ејҖж”ҫ狀жҖҒвҖҰвҖҰвҖқ
з®ҖеҚ•зҡ„說пјҢ拉зәіи®ӨдёәпјҢдәә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еӯҳжңүпјҢе°ұжҳҜдёҖдёӘвҖңеңЈиЁҖзҡ„еҖҫеҗ¬иҖ…вҖқпјҒд»–и®ӨдёәпјҢиҝҷжҳҜвҖңдҪңдёәи®әиҜҒиў«еңЈиЁҖеҗҜзӨәзҡ„еҸҜиғҪжҖ§зҡ„еӯҰ說вҖ”д№ӢдёҠзҡ„еҪўиҖҢдёҠдәәзұ»еӯҰзҡ„第дёҖдёӘе‘Ҫйўҳеӣ дёәиҝҷж ·зҡ„и§ӮзӮ№пјҢд»–и®Өдёәдё–з•ҢдёҠе…¶е®ғе®—ж•ҷзҡ„ж•ҷеҫ’гҖҒдҝЎд»°иҖ…пјҢйӮЈдәӣе®—ж•ҷжғ…ж“Қе……жІӣпјҢеҜҢжңүзҲұеҝғе–„иЎҢпјҢдҪҶз”ұдәҺеҗ„з§ҚеҺҹеӣ пјҢж— жі•жҺҘеҸ—еҹәзқЈе®—ж•ҷжҙ—зӨјзҡ„дәәпјҢйғҪжҳҜвҖңеҢҝеҗҚзҡ„еҹәзқЈеҫ’вҖқпјҲAnonymous ChristiansпјүгҖӮеҸӮз…§иҝҷж ·зҡ„и§ӮзӮ№пјҢдҪӣж•ҷдёӯзҡ„дҪӣжҖ§и®әиҖ…пјҢжҲ–и®ёд№ҹеҸҜд»ҘиҜҙпјҢдәә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еӯҳжңүпјҢе°ұжҳҜвҖңжңқеҗ‘и§үжӮҹпјҲиҸ©жҸҗпјүзҡ„еӯҳжңүвҖқпјҒдәә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дәәпјҢеҝ…е®ҡиҰҒеҗ‘зқҖи§үжӮҹпјҲиҸ©жҸҗпјүд№ӢйҒ“иҝҲиҝӣпјҒиҖҢе…¶е®ғе®—ж•ҷзҡ„ж•ҷеҫ’пјҢд№ҹйғҪжҳҜвҖңеҢҝеҗҚзҡ„дҪӣж•ҷеҫ’вҖқпјҲAnonymous BuddhistпјүпјҒиҝҷз§ҚеҖҹз”ЁпјҢеңЁе®—ж•ҷеҜ№иҜқдёҠпјҢеҸҜиғҪдјҡеҸҳеҫ—еҫҲжңүж„ҸжҖқвҖҰвҖҰжҺҘдёӢ來пјҢжҲ‘们жқҘдәҶи§Јжң¬дё–зәӘ欧жҙІжңҖжқ°еҮәзҡ„еҹәзқЈж–°ж•ҷзҘһеӯҰ家еҚЎе°”‧е·ҙзү№пјҲKarl Barth,1886пҪһ1968пјүзҡ„зҘһеӯҰи§ӮзӮ№гҖӮе·ҙзү№зҡ„зҘһеӯҰжӣҫиў«з§°дёәеҚұжңәзҘһеӯҰгҖҒиҫ©иҜҒзҘһеӯҰпјҢе®ғдә§з”ҹдәҺеҹәзқЈж•ҷдҝЎд»°зҡ„еҚұжңәд№ӢдёӯпјҲ第дәҢж¬Ўдё–з•ҢеӨ§жҲҳпјүпјҢ并еңЁеҚұжңәд№ӢдёӯпјҢдёәз»ҙжҠӨдёҠеёқзҡ„еҗҜзӨәиҖҢеҘӢж–—дёҚжҮҲгҖӮд»–зҡ„зҘһеӯҰпјҢжҳҜдҪңдёәиҝ”еӣһеҲ°е®—ж•ҷж”№йқ©зҡ„ж–°ж•ҷжӯЈз»ҹзҘһеӯҰпјҢж•…д»–зҡ„зҘһеӯҰпјҢеҸҲиў«з§°дёәвҖңж–°жӯЈз»ҹдё»д№үвҖқпјҲNeo-OrthodoxyпјүгҖӮ
д»–и®ӨдёәдёҠеёқеҸӘеҗҜзӨәеңЁеҹәзқЈиә«дёҠпјҢ并且дҪ“зҺ°еңЁдҝЎд»°дёӯпјҢжүҚиғҪиў«дәәжүҖи®ӨиҜҶгҖӮдёҠеёқжҳҜи¶…и¶Ҡзҡ„гҖҒе®Ңе…ЁеҸҰдҪҚзҡ„д»–иҖ…пјҲwholly otherпјүпјҢеҸӘжңүеңЁдёҠеёқзҡ„иҮӘжҲ‘еҗҜзӨәпјҲгҖҠеңЈз»ҸгҖӢпјүдёӯпјҢжүҚжҳҜеҸҜзҹҘзҡ„гҖӮжүҖд»ҘпјҢд»–и®Өдёә科еӯҰ家е’ҢзҘһеӯҰ家зҡ„з ”з©¶ж–№жі•е’Ңи®әйўҳжҳҜе®Ңе…ЁдёҚеҗҢзҡ„гҖӮ科еӯҰеҹәдәҺдәәзұ»зҡ„и§ӮеҜҹе’ҢзҗҶжҖ§пјҢзҘһеӯҰеҲҷеҹәдәҺдёҠеёқзҘһеңЈзҡ„еҗҜзӨәгҖӮ
е·ҙзү№е°ҶдёҠеёқдёҺдәәзҡ„и·қзҰ»пјҢйҮҚж–°拉еҮәдёҖжқЎж— жі•и¶…и¶Ҡзҡ„йёҝжІҹпјҢдәәж— жі•и—үз”ұиҮӘе·ұжқҘи®ӨзҹҘдёҠеёқпјҢдәәеҸӘиғҪи—үз”ұдёҠеёқзҡ„еҗҜзӨәи®ӨзҹҘдёҠеёқгҖӮе·ҙзү№зҡ„иҝҷз§Қи§ӮзӮ№пјҢеҸҜз§°д№ӢдёәвҖңдҝЎд»°зҡ„зҗҶжҖ§дё»д№үвҖқгҖӮ
иҖҢ科еӯҰе’ҢзҘһеӯҰж—ўжҳҜе®Ңе…ЁеҲҶзҰ»гҖҒдёҚзӣёе№Ізҡ„пјҢд№ҹе°ұжІЎжңү科еӯҰи§ӮзӮ№жҢ‘жҲҳзҘһеӯҰе‘Ҫйўҳзҡ„й—®йўҳпјҲеҰӮеҹәзқЈеӨҚжҙ»гҖҒеңЈжҜҚеӨ„еҘіз”ҹеӯҗгҖҒиҝӣеҢ–и®әдёҺеҲӣйҖ и®әзҡ„еҶІзӘҒвҖҰвҖҰзӯүпјүеӯҳеңЁгҖӮ若еҖҹз”Ёе·ҙзү№иҝҷж ·зҡ„и§ӮзӮ№пјҢжҲ‘们д№ҹдјјд№ҺеҸҜд»ҘйҮҚж–°жҸҗй«ҳдҪӣйҷҖвҖңеңЈиЁҖ量вҖқзҡ„ең°дҪҚпјҢжқҘйқўеҜ№дҪӣз»ҸдёӯзҘһйҖҡгҖҒз‘һзӣёгҖҒиҪ®еӣһвҖҰвҖҰзӯүпјҢйҒӯйҒҮеҲ°з§‘еӯҰи§ӮзӮ№зҡ„иҙЁз–‘пјҲзү№ж®Ҡзҡ„жҳҜпјҢдҪӣж•ҷеӣ жҳҺйҖ»иҫ‘еӯҰ家йҷҲйӮЈгҖҒжі•з§°пјҢеҸӘжүҝи®ӨвҖңзҺ°йҮҸвҖқгҖҒвҖңжҜ”йҮҸвҖқпјҢ并дёҚи®ӨеҸҜвҖңеңЈиЁҖ量вҖқзҡ„ең°дҪҚпјҢиҝҷдәӣдҪӣж•ҷйҖ»иҫ‘еӯҰ家пјҢжҲ–еҸҜи§ҶдёәдҪӣж•ҷдёӯзҡ„зҗҶжҖ§дё»д№үиҖ…вҖқпјүгҖӮйҮҚж–°жҸҗй«ҳдҪӣйҷҖвҖңеңЈиЁҖ量вҖқзҡ„ең°дҪҚпјҢйҷӨдәҶеҸҜд»ҘиҜҙжҳҺвҖңиҪ®еӣһвҖқзҡ„жҲҗз«ӢеӨ–пјҢдәҰжҲ–и®ёеҸҜд»ҘдҪҝи®ёеӨҡдҝ®йҒ“дёҺжҖқжғідёҠзҡ„е·®ејӮпјҢйҮҚж–°еӣһеҲ°дҪӣйҷҖзҡ„вҖңеңЈиЁҖвҖқжң¬иә«пјҒеҸӘжҳҜпјҢд»Җд№ҲжҳҜдҪӣйҷҖзҡ„еңЈиЁҖпјҹдҪӣж•ҷеҸІдёҠдёҖзӣҙеӯҳеңЁзқҖдәҶд№үдёҺ不дәҶд№үд№ӢдәүпјҢдёӯи§ӮгҖҒе”ҜиҜҶзҡ„з©әгҖҒжңүд№ӢдәүпјҢе°ұжҳҜдёҖ例пјҢиҝҷжҒҗжҖ•еңЁдҪӣж•ҷж•ҷд№үдёҠпјҢжҳҜдёҖдёӘйҡҫд»ҘзңҹжӯЈи§ЈеҶізҡ„й—®йўҳвҖҰвҖҰжңҖеҗҺпјҢжҲ‘们жқҘеҸӮиҖғйҳҝе°”ж–Ү‧жҷ®е…°дёҒж јпјҲAlvinPlantinga,1932пҪһ пјүи®әиҜҒеҹәзқЈж•ҷдҝЎеҝөеҸҜд»Ҙ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еҹәжң¬дҝЎеҝөзҡ„зҗҶз”ұгҖӮжҷ®е…°дёҒж јд»Ҙиҝҗз”ЁиӢұзҫҺе“ІеӯҰз•Ңзҡ„дё»жөҒжҖқжғівҖ”вҖ”еҲҶжһҗе“ІеӯҰз ”з©¶еҹәзқЈе®—ж•ҷпјҢиҖҢеңЁеҪ“д»ҠзҫҺеӣҪзҡ„еҹәзқЈж•ҷе“ІеӯҰз ”з©¶дёӯи‘—з§°гҖӮ1965 年пјҢд»–жҠҠжЁЎжҖҒйҖ»иҫ‘еј•иҝӣе…ідәҺдёҠеёқеӯҳеңЁзҡ„вҖңжң¬дҪ“иҪ®иҜҒжҳҺвҖқпјҲontological argumentпјүпјҢејҘиЎҘдәҶеә·еҫ·пјҲImmanuelKant ,1724пҪһ1804пјүжүҖжҢҮеҮәзҡ„пјҢиҜҘиҜҒжҳҺжҳҜж··ж·ҶдәҶвҖңжҳҜвҖқе’ҢвҖңеӯҳеңЁвҖқпјҲвҖңеӯҳеңЁвҖқ不жҳҜдёҖдёӘи°“иҜҚпјүзҡ„зҗҶи®әзјәйҷ·гҖӮиҝҷйЎ№з ”з©¶ж”№еҸҳ了дәҢзҷҫе№ҙжқҘиҘҝж–№е“ІеӯҰз•Ңзҡ„дёҖдёӘе®ҡи®әпјҡвҖңеә·еҫ·ж°ёиҝңжҺЁзҝ»了жң¬дҪ“иҪ®иҜҒжҳҺвҖқгҖӮ
еңЁе…ідәҺеҹәзқЈж•ҷдҝЎеҝөзҡ„зҹҘиҜҶи®әй—®йўҳдёҠпјҢжҷ®е…°дёҒж јеҜ№еҹәзЎҖдё»д№үзҹҘиҜҶи®әиҖ…пјҢжҸҗеҮәдәҶејәзғҲзҡ„жҢ‘жҲҳпјҢд»–е°–й”җең°й—®йҒ“пјҡдёәд»Җд№ҲдёҠеёқеӯҳеңЁзҡ„дҝЎеҝөпјҢе°ұдёҚиғҪжҳҜжҲ‘们жҒ°еҪ“зҡ„еҹәжң¬дҝЎ念д№ӢдёҖе‘ўпјҹе°ұеғҸвҖңеӨ–еңЁдё–з•ҢеӯҳеңЁвҖқиҝҷж ·дёҖдёӘе“ІеӯҰ家жҸҗеҮәиҙЁз–‘пјҢдҪҶдёҖиҲ¬дәәеҚҙи®ӨдёәжҳҜжҒ°еҪ“зҡ„еҹәжң¬дҝЎеҝөдёҖж ·пјҢжңү什д№ҲзҗҶз”ұи®ӨдёәвҖңдёҠеёқеӯҳеңЁвҖқдёҚеҸҜиғҪжҳҜдёҖдёӘжҒ°еҪ“зҡ„еҹәжң¬дҝЎ念пјҹпјҲжӯӨеӨ„йЎ»жіЁж„ҸпјҢжҹҗдёҖдёӘдҝЎеҝөжҳҜжҒ°еҪ“зҡ„еҹәжң¬дҝЎеҝөпјҢ并дёҚдҝқиҜҒйӮЈдёҖдҝЎеҝөзҡ„зңҹе®һжҖ§пјүгҖӮжҷ®е…°дёҒж јеӣ жӯӨи®ӨдёәвҖңдёҠеёқеӯҳеңЁвҖқпјҢеҜ№еҹәзқЈеҫ’иҖҢиЁҖпјҢеҸҜд»Ҙ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жҒ°еҪ“зҡ„еҹәжң¬дҝЎеҝөпјҲеӣ дёәжІЎжңүзҗҶз”ұи®ӨдёәвҖңдёҠеёқеӯҳеңЁвҖқдёҚеҸҜиғҪжҳҜдёҖдёӘжҒ°еҪ“зҡ„еҹәжң¬дҝЎеҝөпјүгҖӮиҷҪ然пјҢиҝҷ并дёҚиғҪдҝқиҜҒвҖңдёҠеёқеӯҳеңЁвҖқиҝҷдёӘдҝЎеҝөжҳҜзңҹзҡ„пјҢдҪҶеҚҙдёәдҝЎд»°еҹәзқЈж•ҷзҡ„дәәпјҢжҸҗдҫӣ了дёҖдёӘзҗҶжҖ§зҡ„дҝқиҜҒпјҡдёҠеёқеӯҳеңЁзҡ„дҝЎеҝөпјҢеҸҜд»ҘдҪңдёәжҲ‘们жҒ°еҪ“зҡ„еҹәжң¬дҝЎеҝөд№ӢдёҖгҖӮжҷ®е…°дёҒж јзҡ„иҝҷдёӘи®әиҜҒпјҢйўҮеҸ—жү№иҜ„пјҢеңЁе“ІеӯҰз•ҢдёӯпјҢжӯӨе·Іиў«з§°дёәвҖңеӨ§еҚ—з“ңе…Ҳз”ҹиҙЁз–‘вҖқ пјҲ Great PumpkinObjectionпјүпјҢеҚіжҢүз…§жҷ®е…°дёҒж је®ҡд№үвҖң什д№ҲжҳҜжҒ°еҪ“еҹәжң¬дҝЎ念вҖқзҡ„зЁӢеәҸпјҢжҹҗдёӘдҝЎд»°еӨ§еҚ—з“ңе…Ҳз”ҹеӯҳеңЁзҡ„дәәпјҢд№ҹеҸҜд»ҘеҗҲзҗҶең°еҫ—еҮәз»“и®әиҜҙпјҡеӨ§еҚ—з“ңе…Ҳз”ҹзҡ„еӯҳеңЁпјҢеҸҜд»Ҙ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жҒ°еҪ“зҡ„еҹәжң¬дҝЎеҝөгҖӮиҸІ利жҷ®‧еҘҺеӣ пјҲPhilip Quinn,1940пҪһ пјүеҚіиҜҙйҒ“пјҡвҖңеӣ°йҡҫеңЁдәҺвҖҰвҖҰ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ж— ж•°дәә都еҸҜд»Ҙ參еҠ зҡ„жёёжҲҸгҖӮз©ҶзҪ•й»ҳеҫ·зҡ„иҝҪйҡҸиҖ…гҖҒдҪӣйҷҖзҡ„иҝҪйҡҸиҖ…пјҢз”ҡиҮіжҳҜжӢңжңҲж•ҷзҡ„иҝҪйҡҸиҖ…都еҸҜ參еҠ иҝӣ來гҖӮвҖқ
иҷҪ然еҰӮжӯӨпјҢдҪҶжҷ®е…°дёҒж јеҜ№еҹәзЎҖдё»д№үзҹҘиҜҶи®әе…ідәҺзҹҘиҜҶвҖңеҗҲзҗҶжҖ§вҖқзҡ„иҙЁз–‘пјҢеҚҙжҳҜзӣёеҪ“ең°жҲҗеҠҹпјҢд»–жҸҗеҮәзҡ„вҖңдҝқиҜҒвҖқпјҲwarrantпјүдҪңдёәзҹҘиҜҶвҖңеҗҲзҗҶжҖ§вҖқзҡ„и§ӮеҝөпјҢжӣҫеңЁзҫҺеӣҪе“ІеӯҰз•ҢжҺҖиө·дёҖиӮЎвҖңдҝқиҜҒвҖқзғӯпјҢд»–еӣ жӯӨиў«з§°дёәвҖңж”№йқ©е®—и®ӨиҜҶи®әвҖқиҖ…гҖӮеҸӮиҖғжҷ®е…°дёҒж јзҡ„дёҠиҝ°и§ӮзӮ№пјҢжӯЈеҰӮдёҠйқўеҘҺеӣ жүҖ說зҡ„пјҢдҪӣж•ҷеҫ’д№ҹеҸҜд»ҘеҗҲ理ең°иҜҙпјҡдҪӣжҖ§гҖҒж¶…ж§ғгҖҒи§Ји„ұгҖҒиҪ®еӣһвҖҰвҖҰзӯүзҡ„еӯҳеңЁпјҢеҸҜд»Ҙ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жҒ°еҪ“зҡ„еҹәжң¬дҝЎ念пјҒвҖҰвҖҰеҸӘ不иҝҮпјҢвҖңдҪңдёәжҒ°еҪ“еҹәжң¬дҝЎ念зҡ„ж ҮеҮҶжҳҜ什д№ҲпјҹвҖқеҚҙжҳҜдёҖдёӘжӣҙж №жң¬гҖҒиҖҢйҡҫд»Ҙи§ЈеҶізҡ„е“ІеӯҰй—®йўҳпјҒдёҠйқўпјҢ笔иҖ…д»…еёҢжңӣи—үз”ұиҝҷеҮ дҪҚзҺ°гҖҒеҪ“д»ЈзҘһеӯҰ家зҡ„зҗҶи®әпјҢз»ҷдәҲдҪӣж•ҷжҲ–дҪӣеӯҰзҗҶи®әдёҖдәӣ刺жҝҖгҖҒ參иҖғвҖҰвҖҰиҖҢеҜ№дәҺжҜ”иҫғе“ІеӯҰжҲ–жҜ”иҫғе®—ж•ҷзҡ„з ”з©¶пјҢ笔иҖ…и®Өдёә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зӣёеҪ“еӣ°йҡҫзҡ„йўҶеҹҹпјҢеӣ дёәеҝ…йЎ»йӮЈдёӨдёӘпјҲжҲ–еӨҡдёӘпјүз ”з©¶еҜ№иұЎзҡ„еӯҰ說зҗҶи®әйғҪеҫҲзҶҹжӮүжүҚиғҪеҒҡеҮәдёҖдәӣе®ўи§Ӯзҡ„жҲҗжһң來вҖҰвҖҰгҖӮзӣёдҝЎпјҢдёҠйқўе…ідәҺдёҖдәӣзҘһеӯҰзҗҶи®әзҡ„д»Ӣз»ҚпјҢжҲ–еӨҡжҲ–е°‘еҸҜд»Ҙз»ҷдәҲжҲ‘们еңЁдҪӣеӯҰз ”з©¶дёҠдёҖдәӣеҸҚжҖқзҡ„з©әй—ҙвҖҰвҖҰиҝҷд№ҹжҳҜ笔иҖ…зҡ„е…ҙи¶Је’Ңз”ҹе‘ҪжҺўеҜ»иҜҫйўҳгҖӮеңЁе®—ж•ҷзҡ„йҖүжӢ©дёҠпјҢиӢұеӣҪи‘—еҗҚзҡ„еҺҶеҸІеӯҰ家жұӨжҒ©жҜ”пјҲArnold Toynbee , 1889пҪһ1975пјүжӣҫдҪңиҝҮиҝҷж ·зҡ„и§ӮеҜҹиҜҙжҳҺпјҡвҖңеҪ“д»ҠжІЎжңүдёҖдёӘжҙ»зқҖзҡ„дәәжңүи¶іеӨҹзҡ„зҹҘиҜҶпјҢдҪҝд»–еҸҜд»ҘжңүдҝЎеҝғиҜҙдёҖз§Қе®—ж•ҷжҜ”е…¶е®ғжүҖжңүе®—ж•ҷдјҳи¶ҠгҖӮвҖ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