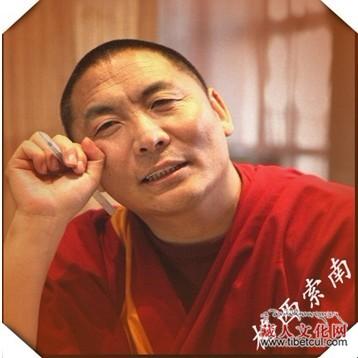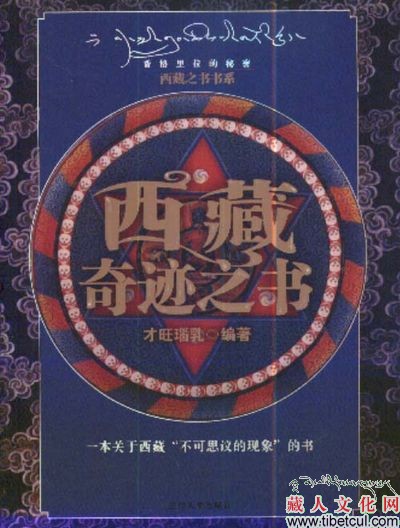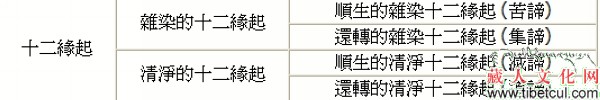еңЁе…¬е…ғеүҚе…ӯдё–зәӘдҪӣйҷҖж—¶д»Јзҡ„еҚ°еәҰпјҢеҮәзҺ°дәҶдёҖз§ҚеҸҚе©ҶзҪ—й—Ёдј з»ҹзҡ„жІҷй—ЁжҖқжҪ®гҖӮи®ёеӨҡдәәдёҚеӨҚд»ҘзҘӯзҘҖдёҮиғҪгҖҒз”ҹеӨ©ж°ёд№җд№ӢжҖқжғідёәж»Ўи¶іпјҢиҪ¬иҖҢеҜ»жұӮиҫҫжң¬з©·зҗҶпјҢдәҺжўөиЎҢ(е№је№ҙеӯҰдёҡ)гҖҒ家дҪҸ(дё»жҢҒ家дёҡ)д№ӢдёҠпјҢеҠ д»Ҙжһ—ж –гҖҒйҒҒдё–д№ӢиӢҰиЎҢз”ҹжҙ»пјӣдәҺзҘӯзҘҖз”ҹеӨ©д№ӢдёҠпјҢеҲӣзңҹжҲ‘и§Ји„ұд№ӢиҜҙгҖӮеёҢеҶҖд»Ҙе…ӢеҲ¶жғ…ж¬Ід№ӢвҖңиӢҰиЎҢвҖқпјҢйӣҶдёӯж„Ҹеҝ—д№ӢвҖңз‘ңдјҪвҖқпјҢеӨ–еҪўйӘёиҖҢеҶ…зҰ»еҰ„еҝөпјҢд»ҘеҘ‘дәәжўөжҲ‘д№Ӣе®һдҪ“гҖӮ他们еӣӣж–№дә‘жёёпјҢиҝҪйҡҸдәҺжҹҗдәӣе®—ж•ҷеҜјеёҲпјҢжҲ–йҡҗдәҺеұұжҙһпјҢжҲ–дҫқжӯўжһ—й—ҙпјҢжҲ–еұ…дәҺжқ‘еӨ–з©әй—Ід№ӢеӨ„пјҢеӨҡд»Ҙд№һйЈҹдёәз”ҹпјҢд№ғиҮід»ҘйҮҺжһңзӯүе……йҘҘгҖӮиҝҷдёҖж–№йқўеҫ—зӣҠдәҺеҚ°еәҰж°”еҖҷжё©жҡ–гҖҒйҮҺз”ҹжһңзү©е……и¶ізҡ„иҮӘ然зҺҜеўғпјҢдёҖж–№йқўеҫ—зӣҠдәҺз»ҹжІ»йҳ¶зә§е’Ңе№ҝеӨ§ж°‘дј—и®ӨеҗҢгҖҒеҙҮ敬гҖҒдҫӣе…»еҮә家дҝ®йҒ“иҖ…зҡ„зӨҫдјҡзҺҜеўғпјҺеҪ“е№ҙйҮҠиҝҰзүҹе°јеҚіжҳҜдј—еӨҡжІҷй—Ёдёӯзҡ„дёҖе‘ҳгҖӮд»–иҜҒйҒ“жҲҗдҪӣеҗҺдҫҝеӣӣж–№жёёеҢ–гҖҒдј ж’ӯж•ҷжі•гҖҒз»„е»әеғ§еӣўпјҢеңЁзӣёеҪ“й•ҝзҡ„дёҖж®өж—¶жңҹпјҢд»–дёҺеҮә家ејҹеӯҗ们йғҪжҳҜеұ…ж— е®ҡжүҖпјҢйҷӨдәҶеӣӣеӨ„дј ж’ӯдҪӣжі•д№ӢеӨ–пјҢе№іж—¶еҮҶд»ҘзҰ…иҜөдёәеҠЎ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Ҫӣж•ҷеңЁеҲӣз«Ӣд№ӢеҲқпјҢеҺҹж— жүҖи°“еҜәйҷўпјҺдёҺе…¶иҜҙжҳҜдёҖз§Қе®—ж•ҷпјҢдёҚеҰӮиҜҙжҳҜдёҖз§ҚжҖқжғіеӯҰжҙҫгҖӮд»ҘеҗҺйҡҸзқҖдҪӣж•ҷзҡ„е№ҝжіӣдј ж’ӯпјҢдҝЎдј—еўһеӨҡпјҢеғ§еӣўеЈ®еӨ§пјҢз»“еӨҸе®үеұ…еҲ¶еәҰзҡ„е®һиЎҢпјҢеғ§дәәжңүдҪҸдәҺдёҖеӨ„гҖҒиҒҡдј—зҶҸдҝ®зҡ„йңҖиҰҒпјҢдҝЎдј—жңүйҡҸж—¶дҫӣе…»гҖҒиҜ·зӣҠзҡ„йңҖиҰҒпјҢдәҺжҳҜеғ§еӣўжҺҘеҸ—дәҶдёҖдәӣзҺӢиҖ…еӨ§иҮЈй•ҝиҖ…еҜҢжҲ·жҚҗиҲҚзҡ„еӣӯжһ—пјҢжҲ–дёәеғ§дәәжҗӯе»әзҡ„з®Җжҳ“иҢ…жЈҡпјҢиҝҷж ·е°ұжңүдәҶж—©жңҹзҡ„вҖңеҜәйҷўвҖқгҖӮдёҚиҝҮйӮЈж—¶еғ§дәә们йҷӨдәҶдёүиЎЈгҖҒй’өгҖҒеҚ§е…·зӯүеҚҒеҮ з§ҚйҡҸиә«з”Ёе“Ғд№ӢеӨ–пјҢдёҚе…Ғи®ёгҖҒд№ҹжІЎжңүд»Җд№Ҳз§Ғжңүиҙўдә§пјҢйҒөеҫӘжүҳй’өд№һйЈҹеҲ¶еәҰпјҢеӨҡж•°ж—¶й—ҙд»ҚиҝҮзқҖеӣӣж–№жёёеҢ–зҡ„з”ҹжҙ»гҖӮеҜәйҷўеҸӘжҳҜз”ЁдәҺеҗ¬дҪӣиҜҙжі•гҖҒз»“еӨҸе®үеұ…пјҢжҲ–еҗ„еӨ„еғ§дәәдә‘жёёдёӯжҡӮж—¶дј‘жҶ©д№ӢжүҖгҖӮиҝҷдёҖж–№йқўдёәдәҶжӣҙеҘҪең°дј ж’ӯдҪӣжі•пјҢдёҖж–№йқўд№ҹжҳҜйҒөеҫӘдҪӣеҲ¶пјҢдёҚдәҺдҪҸеӨ„з”ҹиҜёиҙӘжҒӢгҖӮ
еҚ°еәҰзҡ„еҜәйҷўеңЁдҪӣйҷҖж—¶д»ЈеҚіе·ІеҪўжҲҗдёӨеӨ§зұ»пјҢдёҖзұ»еҸ«еҒҡвҖңеғ§дјҪи“қж‘©вҖқпјҢз®Җз§°вҖңдјҪи“қвҖқпјҢд№үдёәдј—еӣӯпјҢеҚіеӨ§дј—е…ұдҪҸзҡ„еӣӯжһ—гҖӮдёҖиҲ¬йғҪжҳҜеӣҪзҺӢжҲ–еӨ§еҜҢй•ҝиҖ…жүҖж–ҪиҲҚд»Ҙдҫӣеҗ„еӨ„еғ§дҫЈеұ…дҪҸзҡ„пјҢеҰӮзҘ—ж ‘з»ҷеӯӨзӢ¬еӣӯгҖҒз«№жһ—зІҫиҲҚзӯүгҖӮжҚ®жі•еӣҪи‘—еҗҚдҪӣж•ҷеӯҰиҖ…жӢүиҺ«зү№з»ҹи®ЎпјҢдҪӣйҷҖеңЁдё–ж—¶пјҢеғ§еӣўжӢҘжңү29еә§еӨ§зҡ„еҜәйҷўпјҡе…«еә§еңЁзҺӢиҲҚеҹҺпјҢеӣӣеә§еңЁеҚ«иҲҚзҰ»пјҢдёүеә§еңЁиҲҚеҚ«еҹҺпјҢеӣӣеә§еңЁйӘ„е§ҝзҪ—гҖӮеҸҰдёҖзұ»еҸ«еҒҡвҖңйҳҝе…°иӢҘвҖқпјҢз®Җз§°вҖңе…°иӢҘвҖқпјҢд№үдёәз©әй—ІеӨ„пјҢе°ұжҳҜеңЁеұұжһ—й—ҙе’Ңжқ‘й•ҮеӨ–з©әй—Ізҡ„ең°ж–№пјҢжҲ–зӢ¬иҮӘдёҖдәәпјҢжҲ–дәҢдёүдәәе…ұйҖ е°ҸжҲҝд»Ҙдёәеұ…дҪҸзҡ„жё…йқҷдҝ®йҒ“д№ӢжүҖ жҲ–дёҚйҖ жҲҝеұӢпјҢеҸӘжӯўжҒҜеңЁеӨ§ж ‘д№ӢдёӢпјҢд№ҹеҸҜд»ҘеҸ«еҒҡйҳҝе…°иӢҘеӨ„гҖӮ
еҫӢйғЁе°Ҹе“Ғи®°иҪҪдәҶеғ§еӣўз¬¬дёҖж¬ЎжҺҘеҸ—еғ§иҲҚжҚҗиө зҡ„жғ…еҪўпјҡвҖңйӮЈж—¶пјҢжҜ”дёҳжҳҜдёҚе…Ғ
еӨ§зҡ„еҜәйҷўйҷӨдәҶеҜәдё»д№ӢеӨ–пјҢйҖҡеёёйғҪиҰҒжҺЁдёҫдёҖдҪҚжҲ’и…Ҡй•ҝгҖҒеҫ·жңӣй«ҳзҡ„жҜ”дёҳдёәвҖңдёҠеә§вҖқпјҢиө·жҢҮеҜјгҖҒиЎЁзҺҮдҪңз”ЁгҖӮжңүзҡ„еҜәйҷўе®—ж•ҷд»ӘејҸжҜ”иҫғеӨҡпјҢйЎ»жңүдё“дәәдё»жҢҒпјҢз§°д№ӢдёәвҖңз»ҙйӮЈвҖқгҖӮеҜәдё»гҖҒдёҠеә§гҖҒз»ҙйӮЈд№ҹе°ұжҲҗдәҶеҗҺжқҘз§°дёәвҖңдёүзәІвҖқзҡ„еҜәйҷўз®ЎзҗҶиҖ…гҖӮж №жҚ®еҫӢеҲ¶зҡ„规е®ҡпјҢжҜ”дёҳеңЁеғ§еӣўдёӯиҰҒжұӮе…ӯе’ҢеҗҢеұ…пјҢжүҖи°“иә«е’ҢеҗҢеұ…гҖҒеҸЈе’Ңж— иҜӨгҖҒж„Ҹе’ҢеҗҢжӮҰгҖҒи§Ғе’ҢеҗҢи§ЈгҖҒжҲ’е’ҢеҗҢдҝ®гҖҒеҲ©е’ҢеҗҢеқҮпјҢжҜҸжңҲзҡ„жң”жңӣж—ҘйғҪиҰҒиҜөжҲ’пјҢиҝӣиЎҢзҫҜзЈЁпјҢдҪңжү№иҜ„дёҺиҮӘжҲ‘жү№иҜ„гҖӮж—©жңҹеҜәйҷўзҡ„з®ЎзҗҶдёҘж је®һиЎҢж°‘дё»и®®дәӢеҲ¶еәҰпјҢеҮЎжҳҜе…ізі»еӨ§дј—зҡ„дәӢеҠЎпјҢеғ§еӣўйғҪиҰҒеҸ¬ејҖдјҡи®®з ”з©¶пјҢеҫҒеҫ—жүҖжңүдәәзҡ„еҗҢж„ҸеҗҺж–№еҸҜжү§иЎҢгҖӮеҪ“е№ҙдҪӣйҷҖж №жҚ®еғ§еӣўеҸ‘еұ•дёӯеҮәзҺ°зҡ„з§Қз§Қй—®йўҳеҲ¶е®ҡдәҶдёҖзі»еҲ—зҡ„жҲ’规е’ҢвҖңеҜәйҷўвҖқз®ЎзҗҶеҠһжі•пјҢиҫҫеҲ°дәҶд»”з»Ҷдәәеҫ®зҡ„зЁӢеәҰпјҢдёәеҗҺдё–зҡ„еҜәйҷўжҲ–еғ§еӣўеҘ е®ҡдәҶеҶ…еңЁзҡ„иҝҗиЎҢжңәеҲ¶дёҺеӨ–еңЁзҡ„жҖ»дҪ“еҪўиұЎгҖӮдёҖиҲ¬жқҘиҜҙпјҢеҺҹе§ӢдҪӣж•ҷд№ғиҮійғЁжҙҫдҪӣж•ҷж—¶жңҹзҡ„еҜәйҷўжҲ–еғ§еӣўеҹәжң¬йҒөеҫӘе’ҢдҝқжҢҒдәҶеҪ“е№ҙдҪӣйҷҖеҲ¶е®ҡзҡ„жҲ’规е’ҢвҖңеҜәйҷўвҖқз®ЎзҗҶеҠһжі•гҖӮ
дәҶи§ЈеҚ°еәҰж—©жңҹдҪӣеҜәзҡ„жҖ§иҙЁдёҺзү№иүІпјҢеҜ№дәҺжҲ‘们жӯЈзЎ®и®ӨиҜҶе’ҢеҜ№еҫ…еҜәйҷўе’Ңеғ§еӣўеңЁеҸ‘еұ•иҝҮзЁӢдёӯеҮәзҺ°зҡ„з§Қз§ҚејӮеҢ–зҺ°иұЎпјҢжҗһеҘҪдҪӣж•ҷиҮӘиә«е»әи®ҫпјҢйғҪжңүзқҖеҚҒеҲҶйҮҚиҰҒзҡ„ж„Ҹд№үгҖӮжҰӮжӢ¬жқҘиҜҙпјҢеҚ°еәҰж—©жңҹзҡ„дҪӣеҜәе’Ңеғ§еӣўеңЁдҪӣйҷҖиә«ж•ҷдёҺиЁҖж•ҷзҡ„еҪұе“Қе’ҢжҢҮеҜјдёӢеҪўжҲҗдәҶеҰӮдёӢдёҖдәӣзү№иүІпјҡ
1гҖҒеҜәйҷўжҳҜеғ§дәәз»“еӨҸе®үеұ…зҡ„иҗҘең°пјҢдә‘жёёејҳжі•йҖ”дёӯжҡӮж—¶дј‘жҶ©зҡ„еңәжүҖпјҢжҳҜе®үзҪ®жңүз—…е’Ңе№ҙиҖҒжҜ”дёҳзҡ„дҪҸеӨ„пјҢжҳҜд№ з»ҸгҖҒеқҗзҰ…гҖҒиҜөжҲ’гҖҒдҪңзҫҜзЈЁеёғиҗЁзӯүжі•дәӢзҡ„йҒ“еңәгҖӮ
2гҖҒеҜәйҷўеӨҡе»әдәҺеұұжһ—дёӯжҲ–жқ‘й•Үиҫ№з©әй—Ід№ӢеӨ„гҖӮйҷӨдәҶеӣҪзҺӢеӨ§иҮЈй•ҝиҖ…еҜҢжҲ·дҝ®е»әжҲ–жҚҗзҢ®зҡ„д»ҘеӨ–пјҢеҜәйҷўе»әзӯ‘еӨҡдёәиҝӣиЎҢжі•дәӢжҙ»еҠЁжҲ–иҒҡдјҡи®®дәӢзҡ„еңәжүҖе’ҢжҜ”дёҳ们еұ…дҪҸзҰ…дҝ®зҡ„еғ§иҲҚпјҢи®ҫж–ҪдёҖиҲ¬йғҪеҚҒеҲҶз®ҖйҷӢгҖӮдёәиЎЁжі•е’ҢеҜ№дҪӣйҷҖзҡ„жҖҖеҝөпјҢеҜәйҷўдёӯжҲ–иө·иҲҚеҲ©еЎ”пјҢжҲ–жӨҚиҸ©жҸҗж ‘пјҡжҲ–йҘ°д»Ҙжі•иҪ®гҖҒдҪӣйҷҖи¶іеҚ°д№ғиҮіеҪ©з”»зӯүпјҢдёҚжҗһеҒ¶еғҸеҙҮжӢңгҖӮ
3гҖҒжҜ”дёҳ们д»ҘеҮәдё–и§Ји„ұдёәе®—ж—ЁгҖӮдҝ®иЎҢд»ҘжҢҒжҲ’гҖҒиҜөз»ҸгҖҒеқҗзҰ…дёәдё»пјҢд»Ҙжі•иҮӘеЁұгҖӮйҖҡиҝҮиҮӘдҝ®иҮӘеҫӢжқҘе®һи·өжӮҹиҜҒдҪӣжі•гҖҒеҪ°жҳҫдҪӣжі•е’Ңе®ЈзӨәдҪӣжі•пјҢд»ҺиҖҢеҢ–еҜјж°‘дҝ—пјҢеҲ©зӣҠзӨҫдјҡпјҢиҮӘеҲ©еҲ©д»–пјҢд»ҘжӯӨжқҘдҪ“зҺ°иҮӘе·ұзҡ„дәәз”ҹд»·еҖје’ҢзӨҫдјҡд»·еҖјгҖӮдёҚд№ е’’жңҜпјҢдёҚжҗһзҘӯзҘҖгҖӮиЎҢд№һйЈҹжі•пјҢеҜәйҷўеҶ…дёҚиө·зҒ«еҒҡйҘӯгҖӮжңүж—¶д№ҹеҲ°еұ…士家еә”дҫӣпјҢдёәеұ…еңҹ们讲解дҪӣжі•гҖӮжҜҸе№ҙжңүзӣёеҪ“дёҖж®өж—¶й—ҙеңЁдә‘жёёејҳжі•дёӯеәҰиҝҮпјҢеқҡжҢҒз»“еӨҸе®үеұ…еҲ¶еәҰгҖӮдҝ®иЎҢзІҫиҝӣпјҢеҝҚиҫұж…Ҳе’ҢпјҢдёҚиҙӘдә«еҸ—пјҢеҗҢж—¶дәҰдёҚе°ҡиӢҰиЎҢгҖӮ
4гҖҒеғ§дј—ж №жҚ®еҸ—жҲ’гҖҒжҢҒжҲ’жғ…еҶөеҸҠжҲ’и…Ҡй•ҝзҹӯжҺ’еәҸпјҢдҪҶеңЁдәәж јдёҠдёҚеҲҶз§Қ姓гҖҒиҙөиҙұдёҖеҫӢе№ізӯүгҖӮеғ§еӣўжҜ”иҫғдёҘж јең°е®һиЎҢж°‘дё»и®®дәӢеҲ¶еәҰпјҢеҜәдё»гҖҒдёҠеә§е’Ңз»ҙйӮЈзӯүз§үжүҝдҪӣеҲ¶е’ҢеӨ§дј—зҡ„ж—Ёж„ҸеҠһдәӢпјҢдёҚе…Ғи®ёдё“ж–ӯе’Ңжҗһзү№жқғгҖӮ
еҪ“然иҝҷеҸӘжҳҜе°ұжҖ»дҪ“иҖҢиЁҖгҖӮдҪӣйҷҖеңЁдё–ж—¶е°ҡжңүзҠҜжҲ’гҖҒз ҙе’ҢеҗҲеғ§зҡ„е…ӯзҫӨжҜ”дёҳд»ҘеҸҠи°Ӣе®ідҪӣйҷҖеҲҶиЈӮеғ§еӣўзҡ„жҸҗе©ҶиҫҫеӨҡзӯүпјҢдҪ•еҶөеҗҺдё–?жңүдәҶеәһеӨ§зҡ„еғ§еӣўе’Ңдј—еӨҡзҡ„еҜәйҷўпјҢдёҺзӨҫдјҡе’Ңж°‘дј—зҡ„дәӨеҫҖиҮӘ然ж—ҘзӣҠеўһеӨҡпјҢзӣёдә’еҪұе“Қе°ұж—ҘзӣҠеўһеӨ§пјҢжһ„жҲҗдёҖз§ҚејәеӨ§зҡ„зӨҫдјҡе®һдҪ“пјҢдҪӣеҜәд№ҹиў«йҷ„еҠ дәҶжӣҙеӨҡзҡ„е®—ж•ҷгҖҒж–ҮеҢ–ж•ҷиӮІзӯүж–№йқўзҡ„иҒҢиғҪгҖӮжҚ®еҸІж–ҷи®°иҪҪпјҢдҪӣзҒӯзҷҫе№ҙд№ӢеҗҺгҖӮеҗ„ең°еғ§еӣўеӣҙз»•зқҖвҖңеҚҒдәӢвҖқжҲ–вҖңдә”дәӢвҖқзӯүжҲ’еҫӢй—®йўҳдә§з”ҹеҲҶиЈӮпјҢеҪўжҲҗдәҶйғЁжҙҫдҪӣж•ҷгҖӮеҗ„жҙҫеғ§еӣўж №жҚ®иҮӘе·ұдәҶи§Је’Ңи®ӨиҜҶеҲ°зҡ„дҪӣжі•з»“йӣҶеҮәеҗ„иҮӘзҡ„з»ҸеҫӢи®әдёүи—ҸпјҢиҮӘ然еҗ„жҙҫжүҖеұһеҜәйҷўзҡ„规еҲ¶дёҺиҝҗдҪңд№ҹиЎЁзҺ°еҮәдёҖе®ҡзҡ„е·®ејӮгҖӮе…¶дёӯдёҠеә§йғЁеғ§еӣўеҖҫеҗ‘дәҺжҒӘе®ҲдҪӣйҷҖеҲ¶е®ҡзҡ„дёҖеҲҮжҲ’规пјҢжҜ”иҫғе®Ҳж—§пјҢз»ҷдәәд»ҘеҒҸйҮҚвҖңиҮӘеҲ©вҖқзҡ„ж„ҹи§үпјӣеӨ§дј—йғЁеғ§еӣўеҲҷеҖҫеҗ‘дәҺжҠҠжҸЎдҪӣйҷҖеҲ¶жҲ’зҡ„зІҫзҘһпјҢж №жҚ®еҗ„дёӘж—¶д»Је’Ңеҗ„ең°е…·дҪ“жғ…еҶөдҪңйҖӮеҪ“зҡ„еҸҳйҖҡпјҢвҖңиҲҚе°Ҹе°ҸжҲ’вҖқпјӣзғӯеҝғдәҺдҪӣж•ҷзҡ„дј ж’ӯе’ҢеҸ‘еұ•пјҢз»ҷдәәд»ҘеҒҸйҮҚвҖңеҲ©д»–вҖқзҡ„ж„ҹи§үпјҺе®һйҷ…дёҠиҝҷдәӣйғҪжҳҜеӣ зјҳжүҖз”ҹжі•пјҢжҲ‘们дёҚиғҪз®ҖеҚ•ең°еҺ»иҜ„еҲӨи°ҒеҜ№и°Ғй”ҷи°Ғдјҳи°ҒеҠЈгҖӮиҮідәҺд»ҘеҗҺзҡ„еӨ§д№ҳдҪӣж•ҷе’ҢеҜҶд№ҳдҪӣж•ҷзӣӣиЎҢпјҢеӨ§йҮҸеҗёж”¶дәҶеҚ°еәҰдј з»ҹе®—ж•ҷзҡ„еҶ…е®№пјҢеҰӮзҘӯзҘҖд»ӘиҪЁгҖҒе’’жңҜгҖҒеӨҡзҘһдҝЎд»°дёҺеҒ¶еғҸеҙҮжӢңзӯүпјҢдҪҝдҪӣж•ҷз»Ҹе…ёгҖҒеҜәйҷўеҠҹиғҪеҜ№еҗҺжқҘжұүдј дҪӣж•ҷгҖҒи—Ҹдј дҪӣж•ҷдә§з”ҹдәҶйҮҚеӨ§еҪұе“ҚгҖӮеҸҲдҪҝдҪӣж•ҷдёҺе©ҶзҪ—й—Ёж•ҷеҗҢеҢ–пјҢеҜјиҮҙдҪӣж•ҷеңЁеҚ°еәҰжң¬еңҹиҝҮж—©ж¶ҲдәЎ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