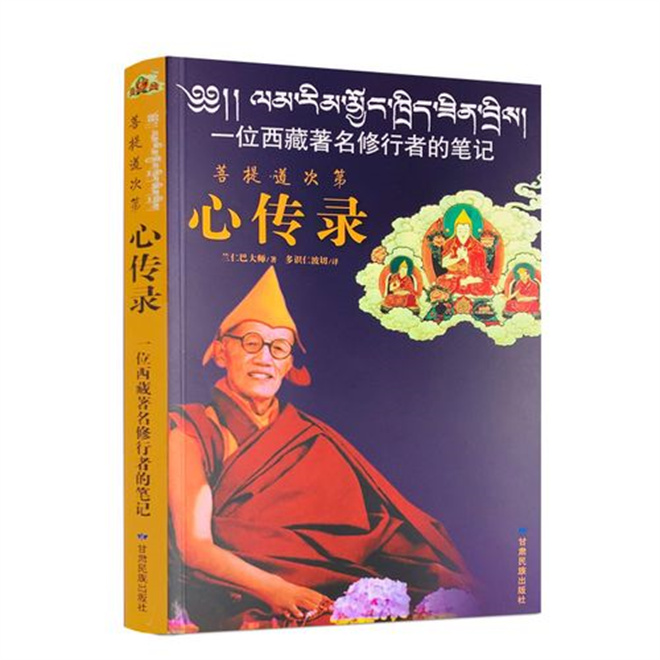гҖҖгҖҖ[ж‘ҳиҰҒ]йҳҝеә•еіЎжҳҜиҘҝи—ҸдҪӣж•ҷеҗҺејҳжңҹзҡ„дёҖдёӘе…ій”®дәәзү©пјҢе…¶и‘—дҪң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д№ҹеңЁиҘҝи—ҸдҪӣж•ҷеҸІдёҠеҚ жңүзӣёеҪ“йҮҚиҰҒзҡ„дҪҚзҪ®гҖӮеңЁжҲ‘еӣҪеӯҰжңҜз•ҢпјҢеҜ№йҳҝеә•еіЎеҸҠе…¶и‘—дҪңзҡ„з ”з©¶е°ҡдёҚеӨҡи§ҒгҖӮжң¬ж–Үд»Ҙ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дёәз ”з©¶еҜ№иұЎпјҢзқҖйҮҚеҲҶжһҗдәҶиҜҘи®әдёӯж¶үеҸҠзҡ„дёҖдәӣйҮҚиҰҒй—®йўҳпјҢеҰӮйҳҝеә•еіЎеңЁдҪ•йғЁжҙҫеҮә家гҖҒз”ҡж·ұи§ҒдёҺе№ҝеӨ§иЎҢзҡ„з»“еҗҲжҳҜеҗҰе§ӢиҮӘйҳҝеә•еіЎгҖҒйҳҝеә•еіЎеҜ№еҜҶе®—зҡ„жҖҒеәҰгҖҒйҳҝеә•еіЎзҡ„дҝ®жҢҒе®—и¶ЈзӯүпјҢ并з®ҖиҰҒиҜҙжҳҺдәҶ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Ҝ№иҘҝи—ҸдҪӣж•ҷеҸ‘еұ•зҡ„еҪұе“ҚгҖӮ
гҖҖгҖҖ[е…ій”®иҜҚ]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пјӣйҳҝеә•еіЎпјӣиҘҝи—ҸдҪӣж•ҷ
гҖҖгҖҖ
гҖҖгҖҖ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жҳҜ11дё–зәӘеҲ°иҘҝи—Ҹејҳжі•зҡ„еҚ°еәҰй«ҳеғ§йҳҝеә•еіЎжүҖи‘—гҖӮиҜҘи®әзҡ„жҸҗеҮәеҸҠе…¶жөҒдј еҜ№иҘҝи—ҸдҪӣж•ҷдә§з”ҹдәҶжһҒе…¶ж·ұиҝңзҡ„еҪұе“ҚгҖӮи®әдёӯжүҖйҳҗиҝ°зҡ„дҝ®еӯҰ次第被и—Ҹдј дҪӣж•ҷеҗҺејҳжңҹзҡ„иҜёеӨҡеӨ§еёҲжүҖеҗёж”¶гҖӮе°Өе…¶жҳҜе®—е–Җе·ҙ(tsongпјҚkhaпјҚpa)еӨ§еёҲ继жүҝгҖҒеҸ‘жү¬дәҶиҝҷж–№йқўзҡ„жҖқжғіпјҢеңЁжӯӨеҹәзЎҖдёҠеҶҷжҲҗгҖҠиҸ©жҸҗйҒ“次第е№ҝи®әгҖӢпјҢд»ҺиҖҢеҜ№ж јйІҒжҙҫ(dgeпјҚlugsпјҚpa)зҡ„еҲӣз«ӢгҖҒе…ҙж—әиө·еҲ°дәҶйҮҚиҰҒдҪңз”ЁгҖӮйҳҝеә•еіЎжң¬дәәеңЁиҘҝи—Ҹзҡ„е®—ж•ҷжҙ»еҠЁеҜ№йҮҚжҢҜиҘҝи—ҸдҪӣж•ҷеҠҹдёҚеҸҜжІЎгҖӮз”ұдәҺд»–зҡ„еҪұе“ҚпјҢи—Ҹдј дҪӣж•ҷеҷ¶еҪ“жҙҫ(bkavпјҚgdamsпјҚpa)еҫ—д»ҘеңЁиҘҝи—ҸеҲӣз«ӢгҖӮеҷ¶еҪ“жҙҫеғ§дәәжҢҒеҫӢи°ЁдёҘпјҢе®Ңе…ЁжҢүз…§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и®Іиҝ°зҡ„次第иҝӣиЎҢдҝ®еӯҰпјҢиҖҢеҗҺе®—е–Җе·ҙеӨ§еёҲеңЁжӯӨеҹәзЎҖдёҠеҲӣз«Ӣж јйІҒжҙҫпјҢеҸҲз§°ж–°еҷ¶еҪ“жҙҫгҖӮиҜҘжҙҫ继жүҝйҳҝеә•еіЎвҖңе…ҲжҳҫеҗҺеҜҶгҖҒжҳҫеҜҶ并йҮҚвҖқзҡ„дјҳиүҜеӯҰйЈҺпјҢ并з»ҸеҗҺиҫҲеӨ§еёҲдёҚж–ӯејҳжү¬пјҢйҖҗжёҗеҸ‘еұ•жҲҗдёәи—Ҹдј дҪӣж•ҷ第дёҖеӨ§жҙҫпјҢеҪұе“ҚжҢҒз»ӯиҮід»ҠгҖӮ笔иҖ…и®ӨдёәпјҢз ”з©¶и—Ҹдј дҪӣж•ҷпјҢе°Өе…¶жҳҜеҗҺејҳжңҹзҡ„и—Ҹдј дҪӣж•ҷпјҢе°ұеҝ…йЎ»з ”з©¶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ҸҠе…¶дҪңиҖ…йҳҝеә•еіЎпјҢиҝҷж ·жүҚиғҪеҜ№и—Ҹдј дҪӣж•ҷеҗҺејҳжңҹзҡ„иө°еҗ‘гҖҒеҸ‘еұ•еҸҠе…¶зү№зӮ№жңүдёҖдёӘиҫғдёәжё…жҘҡзҡ„дәҶи§ЈпјҢд»ҺиҖҢиғҪжӣҙж·ұеҲ»гҖҒжӣҙе…Ёйқўең°з ”究宗е–Җе·ҙеӨ§еёҲзҡ„жҖқжғігҖӮжң¬ж–Үзҡ„зӣ®зҡ„е°ұеңЁдәҺйҖҡиҝҮеҜ№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зҡ„еҲҶжһҗпјҢдәҶи§ЈеҪ“ж—¶зҡ„дј жі•иғҢжҷҜпјҢеҖҹд»ҘзӘҘи§ҒеҪ“ж—¶еҚ°и—ҸдҪӣж•ҷзҡ„дёҖдәӣзү№иүІгҖҒйҳҝеә•еіЎжң¬дәәзҡ„дҝ®жҢҒе®—и¶ЈеҸҠе…¶еҜ№и—Ҹдј дҪӣж•ҷеҗҺејҳжңҹзҡ„еҪұе“ҚпјҢдёәд»ҠеҗҺиҝӣдёҖжӯҘж·ұе…Ҙз ”з©¶еҚ°еәҰжҷҡжңҹеӨ§д№ҳдҪӣеӯҰеҸҠи—Ҹдј дҪӣж•ҷеҗ„ж•ҷжҙҫжҖқжғіжү“дёӢеҹәзЎҖгҖӮ
гҖҖгҖҖдёҖгҖҒиЎҢжі•д№Ӣеҫ’йЎ»дҫқиҮӘйғЁ
гҖҖгҖҖеңЁеҲ«и§Ји„ұеҫӢд»ӘдёӯпјҢйҳҝеә•еіЎйҮҮз”ЁдәҶ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зҡ„иҜҙжі•пјҢеҰӮд»–и®ІеҲ°д»Ҙ10з§Қж–№ејҸеҫ—е…·и¶іжҲ’ж—¶пјҢиҜҙиҝҷжҳҜвҖңиҜҙеҲҮжңүйғЁзҡ„жҢҒеҫӢиҖ…вҖ”вҖ”е°ҠиҖ…жі•ж•‘гҖҒз§°йҹігҖҒдё–еҸӢгҖҒи§үеӨ©гҖҒж„Ҹи¶ігҖҒеӨ§еӯҰиҖ…дё–дәІгҖҒе°ҠиҖ…йҮҠиҝҰеҸӢзӯүдәәзҡ„иҜҙжі•вҖқпјҢжүҖеј•з”Ёзҡ„10з§Қж–№ејҸд№ҹеҸ–йҮҮиҮӘгҖҠдҝұиҲҚи®әгҖӢгҖӮи®ІеҲ°иҲҚжҲ’еҺҹеӣ ж—¶пјҢжҳҜйҡҸпјҸйЎ·дё–дәІеңЁгҖҠдҝұиҲҚи®әгҖӢдёӯзҡ„иҜҙжі•гҖӮи®ІеҲ°еҚҒе…«йғЁжҙҫж—¶пјҢдёҺеӨҡзҪ—йӮЈе®ғ(Taranatha)гҖҠеҚ°еәҰдҪӣж•ҷеҸІгҖӢдёӯжүҖеҲ—жңүйғЁд№ӢиҜҙжі•е®Ңе…ЁдёҖиҮҙгҖӮд»Һиҝҷе„ҝжҲ‘们еҫ—еҮәзҡ„дёҖдёӘеҚ°иұЎжҳҜйҳҝеә•еіЎжҳҜд»Һ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еҮә家зҡ„пјҢеӣ дёәд№үеҮҖжӣҫд»ҺйғЁжү§зҡ„и§ӮзӮ№жқҘеҶіе®ҡи§ЈйҮҠиҝҗз”ЁжҲ’еҫӢзҡ„еҺҹеҲҷгҖӮд»–иҜҙпјҡвҖңеӣӣйғЁзҡ„еҫӢд»Әеҗ„еҲ«пјҢиҪ»йҮҚејҖеҲ¶дёҚеҗҢпјҢеҮә家зҡ„дәәеҸҜд»Ҙеҗ„дҫқйғЁжү§пјҢдёҚиҰҒйҒҝйҮҚе°ұиҪ»ең°йҮҮеҸ–他家зҡ„ејӮиҜҙпјҢд№ҹдёҚеҝ…йҒҝеҝҢиҮӘйғЁзӢ¬жңүзҡ„ејҖи®ёпјҢжҖ•дәә家е«ҢжҒ¶гҖӮвҖқжүҖд»Ҙд№үеҮҖжҖ»з»“дәҶдёҖжқЎвҖңиЎҢжі•д№Ӣеҫ’йЎ»дҫқиҮӘйғЁвҖқзҡ„еҺҹеҲҷгҖӮз”ЁиҝҷжқЎеҺҹеҲҷеҲӨж–ӯпјҢйҳҝеә•еіЎеҸҜд»ҘзЎ®еҲҮең°иҜҙе°ұжҳҜд»Һ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еҮә家зҡ„гҖӮдҪҶе®һжғ…еҚҙдёҚжҳҜиҝҷж ·пјҢиҜёд№ҰжүҖиҪҪеқҮе‘ҠиҜүжҲ‘们йҳҝеә•еіЎдҫқеӨ§дј—йғЁжҢҒеҫӢдёҠеә§еҮә家гҖӮиҝҷйҮҢе°ұдә§з”ҹдёҖдёӘз–‘й—®пјҡеҮә家дәәжүҖдҫқйғЁжҙҫдёҺжүҖжҢҒеӯҰиҜҙзҡ„е…ізі»жҳҜд»Җд№ҲпјҹжҳҜеҗҰеҮә家дәәиҮӘе·ұжүҖжҢҒзҡ„жҲ’еҫӢдёҺжүҖе®Јдј зҡ„жҲ’еҫӢеҸҜд»ҘдёҚдёҖиҮҙпјҹеҜ№жӯӨз–‘й—®еҸҜд»Ҙд»Һд»ҘдёӢеҮ дёӘж–№йқўжқҘеҲҶжһҗпјҡ
гҖҖгҖҖ第дёҖпјҢйҳҝеә•еіЎжң¬дәәжҢҒеӨ§дј—йғЁзҡ„жҲ’еҫӢпјҢдҪҶеңЁиҘҝи—Ҹдј жі•ж—¶пјҢз…§йЎҫеҲ°иҘҝи—Ҹе®һжғ…иҖҢе®Јдј 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зҡ„еҫӢгҖӮеңЁжӯӨжңүеҝ…иҰҒзЁҚзЁҚеӣһйЎҫдёҖдёӢиҘҝи—ҸдҪӣж•ҷзҡ„жҲ’еҫӢдј жүҝпјҡиҘҝи—ҸжңҖеҲқзҡ„7дёӘеҮә家дәәжҳҜдҫқеҜӮжҠӨдёәдәІж•ҷеёҲиҖҢеҮә家еҸ—жҲ’зҡ„гҖӮеҪ“ж—¶дёәдәҶдј жҺҲжҲ’еҫӢпјҢиҝҳдё“й—Ёд»ҺеҚ°еәҰиҝҺиҜ·дәҶвҖң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вҖқзҡ„12дҪҚжҜ”дёҳпјҢеҸҜи§ҒиҘҝи—ҸжңҖж—©жҺҘеҸ—зҡ„е°ұжҳҜ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зҡ„жҲ’еҫӢгҖӮиҮідәҺиҘҝи—ҸжҺҘеҸ—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зҡ„жҲ’еҫӢпјҢдёҖж–№йқўжҳҜеӣ дёәвҖң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жҳҜеҪ“ж—¶еңЁеҚ°еәҰеҠҝеҠӣиҫғеӨ§зҡ„дёҖдёӘе°Ҹд№ҳдҪӣж•ҷж•ҷжҙҫпјҢеҪ“ж—¶еҚ°еәҰеӨ§д№ҳдҪӣж•ҷеҫ’пјҢж— и®әжҳҫеҜҶпјҢеҸ—жҜ”дёҳжҲ’пјҢдёҖиҲ¬йғҪжҳҜд»Һ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еғ§дәәеҸ—жҲ’вҖқгҖӮеҸҰдёҖж–№йқўпјҢеҸҜиғҪдёҺ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зҡ„жҲ’еҫӢжң¬иә«еҫҲзі»з»ҹеҢ–гҖҒ规иҢғеҢ–пјҢжҢҒжҲ’дәәжҲ’еҫӢжё…дёҘжңүе…ігҖӮд№үеҮҖдёәи§ЈеҶіжҲ’еҫӢдёҠзҡ„з–‘й—®пјҢеҺ»еҚ°еәҰжұӮжі•пјҢд»–жүҖйҖүжӢ©зҡ„д№ҹжҳҜ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зҡ„жҲ’еҫӢгҖӮиҖҢдё”еҪ“ж—¶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еҮәдәҶдёҖдёӘжҢҒеҫӢеӨ§еҫ·еҫ·е…үпјҢд»–жҳҜдё–дәІзҡ„ејҹеӯҗгҖӮвҖңгҖҠе№ҝйҮҠгҖӢдёӯиҜҙпјҡвҖҳеңЈ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дёӯзҡ„жҢҒеҫӢеӨ§еҫ·пјҢеҮәиә«дәҺе©ҶзҪ—й—Ёзҡ„йҳҝйҳҮй»Һе°ҠиҖ…еҠҹеҫ·е…үпјҢд»–жҳҜд»ҺиҮӘд»–е®—жҙҫеӨ§жө·дёӯиҫҫеҲ°еҪ»еә•йҖҡиҫҫпјҢ并йҘұйӨҗеҰӮжқҘжҲ’еҫӢжӯЈжі•зҡ„з”ҳйңІзІҫжұҒпјҢиҖҢжҲҗдёәеӨ§жҷәзҺӢпјҢеӨҚеҜ№еҰӮжқҘжӯЈжі•еҝғиҰҒеӢӨеҘӢдҝ®еӯҰпјҢиҖҢз”ҹиө·дәҶзҫҺеҰҷеҠҹеҫ·вҖҷвҖқгҖӮеҫ·е…үзҡ„еӯҰиҜҙеҗҺеӨ§е®ҸдәҺиҘҝи—ҸпјҢж јйІҒжҙҫдә”йғЁеӨ§и®әдёӯзҡ„жҲ’еҫӢж–№йқўзҡ„и®әд№Ұе°ұжҳҜеҫ·е…үзҡ„гҖҠеҫӢз»ҸгҖӢгҖӮйүҙдәҺ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зҡ„жҲ’еҫӢзҡ„ж®Ҡиғңд№ӢеӨ„пјҢиҘҝи—ҸдҪӣж•ҷеҗҺжқҘдё»еҠЁйҖүжӢ©дәҶ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еҫӢгҖӮеҲ°и—ҸзҺӢиөӨзҘ–еҫ·иөһ(khriпјҚgtsugпјҚldeпјҚbtsan)жү§ж”ҝж—¶пјҢе®ЈеёғпјҡвҖңйҷӨ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жҲ’еҫӢд»Ә)еӨ–пјҢе…¶д»–еҫӢе®—пјҢеҸҠеҜҶе®—(жҡӮ)дёҚзҝ»иҜ‘вҖқгҖӮиҖғиҷ‘еҲ°иҝҷж ·дёҖз§Қжғ…еҶөпјҢйҳҝеә•еіЎд»Һдҝ®иЎҢе®һи·өзҡ„и§’еәҰеҮәеҸ‘пјҢдёҚеҶҚеҸҰеӨ–е®Јдј еӨ§дј—йғЁзҡ„жҲ’еҫӢпјҢиҖҢзӣҙжҺҘеҲ©з”ЁдәҶиҘҝи—ҸдҪӣж•ҷз•Ңж—©е·ІзҶҹжӮүзҡ„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жҲ’еҫӢпјҢе°Ҷе…¶з»„з»ҮеҲ°иҮӘе·ұзҡ„дҝ®иЎҢдҪ“зі»дёӯгҖӮдәӢе®һиҜҒжҳҺпјҢиҝҷз§Қж–№жі•жҳҜжҲҗеҠҹзҡ„гҖӮе®ғдҪҝеҫ—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йҳҗиҝ°зҡ„дҝ®еӯҰ次第жӣҙжңүй’ҲеҜ№жҖ§дёҺеҸҜж“ҚдҪңжҖ§гҖӮеҰӮжһңдёҚиҝҷд№ҲеҒҡзҡ„иҜқпјҢеҫҲйҡҫжғіеғҸйҳҝеә•еіЎдјҡжҲҗеҠҹгҖӮзӣёеҸҚзҡ„дёҖдёӘдҫӢеӯҗдҫҝжҳҜд№үеҮҖеӯҰжҲҗеӣһеӣҪеҗҺпјҢдёҖеәҰжғіз”Ё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зҡ„жҲ’еҫӢд»Јжӣҝжұүең°ж—©е·ІзҶҹзҹҘзҡ„гҖҠеӣӣеҲҶеҫӢгҖӢпјҢеҸҜжңҖз»ҲжңӘиҺ·жҲҗеҠҹгҖӮ
гҖҖгҖҖ第дәҢпјҢдёҠиҝ°еҲҶжһҗиҷҪеҸҜд»ҘиҫғеҗҲзҗҶең°и§ЈйҮҠйҳҝеә•еіЎеңЁжҲ’еҫӢдёҠзҡ„жҖҒеәҰпјҢдҪҶе®ғе®һйҷ…дёҠй»ҳи®ӨдәҶеҮә家дәәжүҖжҢҒжҲ’еҫӢдёҺе…¶жүҖе®ЈиҜҙзҡ„еҸҜд»ҘдёҚдёҖиҮҙпјҢиҝҷдёҺд№үеҮҖзҡ„иҜҙжі•зӣёзҹӣзӣҫгҖӮиҖҢйҳҝеә•еіЎжң¬дәәд№ҹзҹҘйҒ“вҖңиЎҢжі•д№Ӣеҫ’йЎ»дҫқиҮӘйғЁвҖқзҡ„еҺҹеҲҷпјҢеңЁгҖҠйҮҠж–ҮгҖӢдёӯжҸҗеҲ°пјҡвҖңе…ідәҺвҖҳд»Һи°Ғеҫ—жҲ’вҖҷзӯүж„Ҹд№үпјҢеә”еҪ“иҜ·й—®жҢҒеҫӢиҖ…并йҳ…иҜ»иҜёеҫӢе…ёгҖӮвҖҰвҖҰе…ідәҺвҖҳжҲ’дҪ“вҖҷд№ҹеә”иҜҘеҸӮйҳ…еҫӢе…ёпјҢ并еҗ‘иҮӘжҙҫзҡ„жҢҒеҫӢиҖ…иҜ·ж•ҷвҖқ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ҰӮжһңвҖңеҮә家дәәжүҖжҢҒжҲ’еҫӢдёҺжүҖе®Јжү¬зҡ„еә”дёҖиҮҙвҖқиҝҷжқЎеҺҹеҲҷжҲҗз«Ӣзҡ„иҜқпјҢйӮЈд№Ҳ笔иҖ…е°ұеҸҜд»ҘеҫҲеӨ§иғҶең°еҒҮи®ҫйҳҝеә•еіЎжҳҜд»ҺиҜҙдёҖеҲҮжңүйғЁеҮәзҡ„家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д»ҺеӨ§дј—йғЁеҮә家гҖӮеҪ“然пјҢеңЁжІЎжңүе……еҲҶиҜҒжҚ®зҡ„жғ…еҶөдёӢпјҢжҲ‘们еҸӘиғҪи®ӨдёәеҮә家дәәжүҖжҢҒжҲ’еҫӢдёҺжүҖе®Јдј зҡ„жҲ’еҫӢеҸҜд»ҘдёҚдёҖиҮҙпјҢжҲ–иҖ…йҳҝеә•еіЎ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зү№дҫӢпјҢд»–зҡ„еҒҡжі•жҳҜзү№ж®Ҡжғ…еҶөдёӢзҡ„зү№ж®ҠеҒҡжі•пјҢдёҚе…·жңүжҷ®йҒҚжҖ§гҖӮ
гҖҖгҖҖдәҢгҖҒж·ұи§Ӯе№ҝиЎҢеҲҶиҖҢеӨҚеҗҲ
гҖҖгҖҖжҚ®й•ҝе°ҫйӣ…дәәе…Ҳз”ҹз ”з©¶пјҢз”ҡж·ұе№ҝеӨ§(GambhirodaraжҲ–Gambhiryaudara)еңЁдёҖиҲ¬еӨ§д№ҳдҪӣж•ҷзҡ„и®әе…ёдёӯжҳҜ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иҜҚжқҘдҪҝз”Ёзҡ„пјҢиҝҷдёӘиҜҚеңЁеҗҺдё–зҡ„е“ІеӯҰдёӯйҖҗжёҗеҲҶзҰ»пјҢ并дҪҝз”ЁвҖңи§ӮвҖқе’ҢвҖңиЎҢвҖқдёӨеӯ—дҪҝд№ӢеҲҶиЈӮдёәдёӨдёӘиҜҚгҖӮиҮідәҺжҳҺзЎ®ең°з”ЁвҖңз”ҡж·ұи§ҒвҖқ(GambhiradarsanaпјҢzab-mo-ltaba)е’ҢвҖңе№ҝеӨ§иЎҢвҖқ(UdaracaritaпјҢrgya-chen-spyod-pa)жқҘз§°е‘јд»Ҙйҫҷж ‘гҖҒжҸҗе©Ҷдёәд»ЈиЎЁзҡ„дёӯи§Ӯзі»з»ҹе’Ңд»Ҙж— и‘—гҖҒдё–дәІдёәд»ЈиЎЁзҡ„з‘ңдјҪиЎҢзі»з»ҹпјҢеҸҜиғҪжңҖж—©и§ҒдәҺиҘҝи—Ҹзҡ„вҖңе®—иҪ®вҖқзұ»и‘—дҪңгҖӮйҖҡиҝҮеҜ№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Ҷ…е®№зҡ„еҲҶжһҗпјҢжҲ‘们еҸҜд»ҘеҸ‘зҺ°пјҢеңЁи®ІеҲ°дҪӣж•ҷжңҖж №жң¬зҡ„зҗҶи®әвҖңз©әвҖқж—¶пјҢ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Ңе…Ёз«ҷеңЁдёӯи§Ӯзҡ„з«ӢеңәдёҠпјҢд»Һеҗ„дёӘж–№йқўи®әиҜҒдәҶвҖңиҜёжі•з©әж— иҮӘжҖ§вҖқпјҢдҪҶеңЁе…·дҪ“зҡ„дҝ®иЎҢе®һи·өж–№йқўпјҢ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йҮҮз”ЁдәҶеӨ§йҮҸзҡ„з‘ңдјҪиЎҢжҙҫзҡ„иҜҙжі•гҖӮ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жүҖйҳҗиҝ°зҡ„дҝ®д№ 次第ж·ұж·ұең°еҪұе“ҚдәҶеҗҺејҳжңҹзҡ„иҘҝи—ҸдҪӣж•ҷгҖӮиҝҷйҮҢзҡ„дёҖдёӘй—®йўҳжҳҜпјҡе°ҶвҖңз”ҡж·ұи§ҒвҖқдёҺвҖңе№ҝеӨ§иЎҢвҖқз»“еҗҲиө·жқҘжҳҜеҗҰе§ӢиҮӘйҳҝеә•еіЎпјҹй•ҝе°ҫйӣ…дәәе…Ҳз”ҹиҜҙпјҡвҖңе®һйҷ…дёҠе°ҶдёӨеӯҰжҙҫеҚівҖҳе№ҝеӨ§иЎҢвҖҷе’ҢвҖҳз”ҡж·ұи§ҒвҖҷз»ҹдёҖиө·жқҘпјҢдҫҝжҳҜж јйІҒжҙҫзҡ„ж•ҷд№үпјҢиҝҷд№ҹжӯЈжҳҜж јйІҒжҙҫжҷ®йҒҚзҡ„дё»еј гҖӮиҝҷдёҖз»ҹдёҖз”ұејҖжҙҫеӨ§еёҲе®—е–Җе·ҙе®һиЎҢдәҶгҖӮжҲ–иҖ…еҶҚиҝҪжәҜеҫ—жӣҙиҝңдәӣпјҢе®—е–Җе·ҙжүҖиЎ·еҝғжҷҜд»°зҡ„йҳҝеә•еіЎе·Із»Ҹе®һиЎҢ дәҶвҖқгҖӮй•ҝе°ҫе…Ҳз”ҹиҝҳеҲ—дәҶдёҖдёӘдёӨжҙҫзҡ„дј жүҝиЎЁпјҢд»ҺиЎЁдёӯжҲ‘们еҸҜд»ҘзңӢеҮәпјҢйҳҝеә•еіЎеңЁдёӨжҙҫзҡ„дј жүҝдёӯеқҮйҮҚеӨҚеҮәзҺ°пјҢеҸҜд»Ҙжғіи§Ғйҳҝеә•еіЎзЎ®е®һеҒҡдәҶе°ҶдёӨжҙҫз»“еҗҲзҡ„еҠӘеҠӣгҖӮдҪҶжҚ®з¬”иҖ…зҡ„иҖғиҷ‘пјҢд№ӢжүҖд»ҘжҠҠйҳҝеә•еіЎдҪңдёәвҖңз”ҡж·ұи§ҒвҖқдёҺвҖңе№ҝеӨ§иЎҢвҖқзҡ„з»“еҗҲиҖ…пјҢдё»иҰҒжҳҜеӣ дёәд»–зҡ„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жҳҜдёҖжң¬зү№еҲ«е®һз”Ёзҡ„и®Іиҝ°дҝ®еӯҰ次第зҡ„вҖңжүӢеҶҢвҖқпјҢд»ҺиҖҢдёәиҘҝи—ҸдәәжүҖйҮҚи§ҶгҖӮе…¶е®һиҝҷз§ҚжҖқжғіиҝҳеә”иҜҘеҫҖеүҚиҝҪжәҜпјҢиҝҷе°ұзүөж¶үеҲ°дёӯи§ӮгҖҒз‘ңдјҪзҡ„еҲҶеҗҲй—®йўҳгҖӮ笔иҖ…жӯӨеӨ„д»…иғҪеҜ№иҝҷдёҖй—®йўҳжҸҗеҮәдёҖзӮ№зІ—жө…зҡ„зңӢжі•гҖӮ
гҖҖгҖҖд»ҺеҗҺжңҹеҚ°еәҰдҪӣж•ҷдёӯи§ӮгҖҒз‘ңдјҪзҡ„иһҚеҗҲжқҘзңӢпјҢдёӨжҙҫзҡ„еҜ№з«Ӣ并йқһжҳҜж°ҙзҒ«дёҚзӣёе®№зҡ„гҖӮеҜ№жӯӨ笔иҖ…зҡ„дёҖдёӘеҹәжң¬з«ӢеңәжҳҜпјҡдёӯи§ӮгҖҒз‘ңдјҪдёӨжҙҫзҡ„жҖқжғіж №жәҗйғҪеңЁдәҺиҲ¬иӢҘпјҢдёӨжҙҫеқҮи®ІдёӯйҒ“пјҢеҸӘдёҚиҝҮдҫ§йҮҚзӮ№дёҚеҗҢпјҢдёӯи§ӮзқҖйҮҚи®ІвҖңзңҹз©әвҖқпјҢз‘ңдјҪзқҖйҮҚи®ІвҖңеҰҷжңүвҖқгҖӮиҷҪ然жңҖз»Ҳзҡ„и§Ји„ұжҳҜзҰ»иЁҖз»қзӣёзҡ„пјҢдҪҶеңЁе…·дҪ“зҡ„дҝ®иЎҢиҝҮзЁӢдёӯеҲҷйңҖиҰҒдёҖдәӣеҲҮе®һзҡ„дҫқзқҖзӮ№пјҢиҝҷдҫҝжҳҜз‘ңдјҪгҖӮ既然дёӨжҙҫ并дёҚзӣёжӮ–пјҢйӮЈд№Ҳд»ҘеҗҺзҡ„еҗҲжөҒд№ҹжҳҜдёҖдёӘеҝ…然зҡ„и¶ӢеҠҝгҖӮвҖңз”ҡж·ұе№ҝеӨ§вҖқд»ҘеүҚжҳҜдёҖдёӘиҜҚпјҢиҝҷдёӘиҜҚвҖңдёҚзҹҘдёҚи§үвҖқең°иў«еҲҶдёәдёӨдёӘиҜҚиҖҢдҪңдёәеҜ№з«Ӣзҡ„еҗҚз§°з”ЁжқҘз§°е‘јдёӨдёӘеӯҰжҙҫгҖӮвҖң然иҖҢд№ҹжӯЈжҳҜиҝҷж ·пјҢд»Ҙиҝҷж ·зҡ„еҗҚз§°з§°е‘јдёӨеӯҰжҙҫеҸҲдёҚзҹҘдёҚи§үең°дҪҝдёӨеӯҰжҙҫиһҚеҗҲпјҢиҝҷдёҖиҝҮзЁӢжҳҜж„ҹи§үдёҚеҲ°зҡ„вҖқгҖӮдҪӣж•ҷиҷҪ然讲жҷәж…§и§Ји„ұпјҢ然дәҰејәи°ғдҝ®иЎҢгҖӮдҪӣйҷҖжҲҗйҒ“жҳҜеңЁиҸ©жҸҗж ‘дёӢйҖҡиҝҮзҰ…е®ҡиҖҢеҫ—пјӣдҪӣйҷҖе…ҘзҒӯж—¶д№ҹе…ҲиЎҢзҰ…е®ҡпјҢ然еҗҺеҮәе®ҡе…ҘзҒӯгҖӮжҚ®еҚ°йЎәжі•еёҲз ”з©¶пјҢж—©жңҹдҪӣж•ҷвҖңз©әвҖқзҡ„жҰӮеҝөеҚідёҺзҰ…е®ҡжңүе…ігҖӮеңЁеҲқжңҹдҪӣж•ҷз»Ҹе…ёдёӯпјҢз©әдёҺйҖӮеҗҲдәҺдҝ®д№ зҰ…и§Ӯзҡ„дҪҸеӨ„жңүе…ігҖӮвҖңдҪҸеңЁз©әеұӢдёӯпјҢжІЎжңүеӨ–жқҘзҡ„еҡЈжқӮзғҰжү°пјҢеҪ“然жҳҜе®Ғйқҷзҡ„пјҢй—ІйҖӮзҡ„гҖӮеңЁиҝҷйҮҢдҝ®д№ зҰ…ж…§пјҢдёҚдёәеӨ–еўғжүҖжғ‘д№ұпјҢдёҚиө·еҶ…еҝғзҡ„зғҰ(еҠЁ)жҒј(д№ұ)пјҢиҝҷз§ҚеҝғеўғпјҢдёҚжӯЈеҰӮз©әеұӢйӮЈж ·зҡ„з©әеҗ—пјҹвҖҰвҖҰд»Ҙз©әеұӢжқҘиұЎеҫҒеҝғз©әеҜӮзҡ„ж„Ҹд№үгҖӮвҖҰвҖҰдҝ®иЎҢиҖ…зҡ„зҰ…ж…§дҪҸеӨ„пјҢжӯЈеҰӮз©әеұӢйӮЈж ·пјҢдәҺжҳҜе°ұз§°дёәз©әдҪҸпјҢз©әдҪҸе®ҡдәҶгҖӮвҖҰвҖҰжүҖд»ҘзҰ…ж…§е®үдҪҸзҡ„еўғең°пјҢд№ҹеҗҚдёәдҪҸпјҢиҖҢжңүз©әдҪҸпјҢеҜӮйқҷдҪҸзӯүеҗҚзӣ®гҖӮжҖ»д№ӢпјҢеңЁз©әй—ІеӨ„дҝ®иЎҢпјҢеј•иө·дәҶд»Ҙз©әжқҘиұЎеҫҒзҰ…ж…§зҡ„еўғең°пјҢжҳҜвҖҳз©әвҖҷд№үдёҚж–ӯжҳӮжү¬зҡ„еҲқжңҹж„Ҹд№үвҖқгҖӮз”ұжӯӨеҸҜзҹҘдёӯи§Ӯе“ІеӯҰзҡ„вҖңз©әвҖқдёҺж—©жңҹзҰ…жі•зҡ„е…ізі»гҖӮдёӯеӣҪзҡ„ж—©жңҹиҜ‘з»Ҹд№ҹеӨҡжҳҜе…ідәҺе°Ҹд№ҳзҰ…ж•°еӯҰж–№йқўзҡ„пјҢеҰӮе®үдё–й«ҳжүҖиҜ‘гҖҠдҝ®иЎҢйҒ“ең°з»ҸгҖӢгҖӮе…¶д№ҰеҗҚдёҺгҖҠз‘ңдјҪеёҲең°и®әгҖӢжҳҜдёҖж ·зҡ„пјҢжҖқжғідәҰеҝ…然жңүдәӣзӣёйҖҡгҖӮгҖҠдҝ®иЎҢйҒ“ең°з»ҸгҖӢзҡ„ж’°йӣҶиҖ…жҳҜе…¬е…ғ1дё–зәӘе·ҰеҸіи‘—еҗҚзҡ„з‘ңдјҪеёҲеғ§дјҪзҪ—еҲ№(samgharaksaпјҢдј—жҠӨ)пјҢи—Ҹж–Үиө„ж–ҷйҮҢиҜҙеҗҺжңҹзҡ„дёӯи§ӮеӯҰ家дҪӣжҠӨгҖҒжё…иҫЁжҳҜдј—жҠӨзҡ„й—ЁдәәпјҢеҗ•еҫөе…Ҳз”ҹжҚ®жӯӨиҖҢиЁҖпјҡвҖңдёӯи§ӮжҙҫдёҺз‘ңдјҪиЎҢжҙҫйғҪжҳҜжқҘжәҗдәҺз‘ңдјҪеёҲзҡ„еҗҢдёҖзі»з»ҹгҖӮвҖқиҝҷдёҖз»“и®әеңЁеӨҡзҪ—йӮЈе®ғзҡ„гҖҠеҚ°еәҰдҪӣж•ҷеҸІгҖӢдёӯдәҰеҸҜеҫ—еҲ°еҚ°иҜҒпјҡвҖң(иҝҰи…»иүІиҝҰзҺӢеҺ»дё–д№Ӣж—¶)пјҢдҝ®жҢҒеӨ§д№ҳж•ҷжі•зҡ„дәәйғҪжҳҜз‘ңдјҪиЎҢиҖ…е”ҜиҜҶеёҲпјҢ他们е…ҲжҳҜеҲҶеҲ«еңЁеҚҒе…«йғЁдёӯеҮә家пјҢйҖҡеёёеҸҲжҳҜдёҺеҗ„йғЁзҡ„дәәеҗҢдҪҸвҖқгҖӮдёӯи§ӮгҖҒз‘ңдјҪиЎҢжҙҫзҡ„е…ұеҗҢзҡ„жқҘжәҗжҳҜз‘ңдјҪеёҲпјҢдҪҶе®ғ们е…ұеҗҢзҡ„зҗҶи®әеҹәзЎҖеә”жҳҜиҲ¬иӢҘз»ҸгҖӮдёӯи§ӮиҮӘдёҚеҝ…иҜҙпјҢйҫҷж ‘е°ұжӣҫйҖ иҝҮиҜҰз»Ҷи§ЈйҮҠиҲ¬иӢҘз»Ҹзҡ„гҖҠеӨ§жҷәеәҰи®әгҖӢпјҢз‘ңдјҪиЎҢжҙҫдәҰжңүи§ЈйҮҠеӨ§е“ҒиҲ¬иӢҘзҡ„гҖҠзҺ°и§Ӯеә„дёҘи®әгҖӢгҖӮз‘ңдјҪиЎҢжҙҫзҡ„ж— и‘—еңЁгҖҠж‘„еӨ§д№ҳи®әгҖӢдёӯиҜҙд»–зҡ„дёүжҖ§иҜҙжқҘиҮӘдәҺиҲ¬иӢҘз»ҸпјҢ并жҠҠе®ғдёҺиҲ¬иӢҘз»Ҹзҡ„йҒ“зҗҶеҠ д»ҘдјҡйҖҡгҖӮиҘҝи—ҸеҸІд№ҰиҜҙж— и‘—жғіеҲ°иҷҪ然е…ұйҖҡзҡ„дёүи—Ҹе’ҢеӨ§д№ҳзҡ„з»Ҹе…ёе®№жҳ“йҖҡжҷ“пјҢдҪҶиҰҒдёҚйҮҚеӨҚдёҚй”ҷд№ұең°зҗҶи§ЈиҲ¬иӢҘжіўзҪ—иңңеӨҡз»Ҹе…ёзҡ„ж„Ҹд№үпјҢе°ұеҫҲеӣ°йҡҫпјҢдәҺжҳҜдә§з”ҹдәІи§Ғжң¬е°ҠзҘһејҘеӢ’зҡ„ж„ҝжңӣпјҢйҖҡиҝҮдҝ®д№ пјҢжңҖз»ҲеңЁејҘеӢ’йқўеүҚеҗ¬еҸ—дәҶжүҖжңүдёҖеҲҮеӨ§д№ҳж•ҷжі•пјҢйҖҡиҫҫдёҖеҲҮз»ҸйғЁд№Ӣд№үзҗҶгҖӮеҗҺжңҹзҡ„з‘ңдјҪиЎҢжҙҫжӣҙдёәйҮҚи§ҶиҲ¬иӢҘз»ҸпјҢд»ҺиҫҫзЈЁжіўзҪ—зҺӢејҖе§ӢпјҢеҸӘжңүиҲ¬иӢҘж•ҷжі•еӨ§дёәзӣӣиЎҢпјӣеңЁйҳҗйҮҠиҲ¬иӢҘз»Ҹж—¶пјҢд№ҹеҗёж”¶дәҶдёӯи§Ӯж— иҮӘжҖ§зҡ„зҗҶи®әгҖӮз‘ңдјҪиЎҢиҖ…еёҲеӯҗиҙӨеңЁдёңеҚ°еәҰжӣҫеҫ—ејҘеӢ’жҺҲи®°пјҡеңЁи§ЈиҜҙиҲ¬иӢҘд№үзҗҶзҡ„и®әе…ёдёӯпјҢеә”з»јеҗҲеҗ„家еҗҲзҗҶйғЁеҲҶгҖӮеңЈиҖ…и§Ји„ұеҶӣдё“дј дё–дәІзҡ„иҲ¬иӢҘеӯҰпјҢд»–д»Ҙдёӯи§Ӯж— иҮӘжҖ§зҡ„д№үзҗҶи§ЈйҮҠгҖҠиҲ¬иӢҘе…«е“ҒдәҢдёҮйўӮгҖӢе’ҢгҖҠзҺ°и§Ӯеә„дёҘи®әгҖӢпјҢжҳҜжҸүе’ҢгҖҠиҲ¬иӢҘгҖӢдёҺгҖҠи§ӮзҺ°еә„дёҘи®әгҖӢиҖҢйҖ и®әзҡ„ејҖеҲӣиҖ…гҖӮеҸҜд»ҘиҜҙпјҢдёӯи§ӮгҖҒз‘ңдјҪдёӨжҙҫеңЁи§ЈйҮҠиҲ¬иӢҘз»ҸдёҠйҮҮз”ЁдәҶдёҚеҗҢзҡ„и§’еәҰпјҢдёӯи§Ӯд»ҺвҖңеҪ“дҪ“еҚіз©әвҖқзҡ„и§’еәҰжқҘжҺўи®Ёж— иҮӘжҖ§пјҢз‘ңдјҪиЎҢжҙҫеҲҷд»ҺеҝғиҜҶзҡ„и§’еәҰжҺўи®Ёж— иҮӘжҖ§гҖӮ гҖҠйҮ‘еҲҡз»ҸгҖӢдёӯиҜҙпјҡвҖңдёҖеҲҮжңүдёәжі•пјҢеҰӮжўҰе№»жіЎеҪұпјҢеҰӮйңІдәҰеҰӮз”өпјҢеә”дҪңеҰӮжҳҜи§ӮвҖқгҖӮжӯӨеӨ„зҡ„вҖңеҰӮжўҰе№»вҖқзӯүе°ұжҳҜжҢҮдәәзҡ„ж„ҸиҜҶжҲ–ж„ҸиҜҶзҡ„дҪңз”ЁпјҢжҠҠеӨ–зү©зҡ„еӯҳеңЁдёҺдәәзҡ„ж„ҸиҜҶиҒ”зі»иө·жқҘгҖӮгҖҠеӨ§жҷәеәҰи®әгҖӢдёӯи®ІпјҡвҖңдёүз•ҢжүҖжңүпјҢзҡҶеҝғжүҖдҪңвҖқгҖӮдәҰз»ҷз‘ңдјҪиЎҢжҙҫзҡ„еҸ‘еұ•жҸҗдҫӣдәҶжҖқи·ҜгҖӮеҸҰдёҖж–№йқўпјҢгҖҠеӨ§жҷәеәҰи®әгҖӢиҜҙпјҡвҖңж‘©иҜғиЎҚз©әй—ЁиҖ…пјҢдёҖеҲҮиҜёжі•жҖ§еёёиҮӘз©әпјҢдёҚд»Ҙжҷәж…§ж–№дҫҝи§Ӯж•…з©әвҖқгҖӮжҚ®ж—Ҙжң¬еӯҰиҖ…з ”з©¶пјҢиҜҙиҝҷеҸҘиҜқеҸҜиғҪе·Іжҡ—еҗ«дәҶе”ҜиҜҶеӯҰзҡ„дә§з”ҹгҖӮе”ҜиҜҶеӯҰе°ұжҳҜдёәдәҶеҜ»жүҫдёҖз§ҚеҸҰеӨ–зҡ„йҖ”еҫ„жқҘиҜҒжҲҗз©әд№үпјҢжқҘдҪҝдәә们и®ӨиҜҶеҲ°з©әгҖӮд»Һдҝ®иЎҢж–№йқўиҖҢиЁҖпјҢеҲқжңҹгҖҒдёӯжңҹдёӯи§ӮжҙҫйғҪдёҚеҝҪи§ҶиҸ©иҗЁеҚҒең°зҡ„з‘ңдјҪж–№жі•пјҢйҫҷж ‘дәҰеҘ–еҠұеҚҒең°з‘ңдјҪгҖӮжңҲз§°гҖҠе…Ҙдёӯи®әгҖӢйҖҡиҝҮи§ЈиҜҙдҪңдёәиҸ©иҗЁзҡ„дҝ®д№ йҳ¶дҪҚзҡ„еҚҒең°иҖҢйҳҗжҳҺдёӯи§ӮжҖқжғігҖӮжҠҠиҝҷеҚҒең°дёҺдёӯи§ӮжҖқжғіеҠ д»Ҙз»“еҗҲзҡ„еҖҫеҗ‘пјҢжҳҜе…¶еҗҺжңҹдёӯи§Ӯжҙҫзҡ„еӯҰиҖ…жүҖзү№еҲ«ејәи°ғзҡ„дәӢгҖӮ
гҖҖгҖҖз”ұдёҠжүҖиҝ°еҸҜзҹҘпјҢйҳҝеә•еіЎеңЁ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дёӯдјҡйҖҡдёӯи§Ӯз‘ңдјҪд№ӢиҜҙ并йқһеҒ¶з„¶пјҢиҖҢжңүе…¶ж·ұеҺҡзҡ„жҖқжғіжёҠжәҗгҖӮйҳҝеә•еіЎзҡ„жҖқжғіжӣҙзӣҙжҺҘзҡ„жқҘжәҗеә”жҳҜ8дё–зәӘе…Ҙи—Ҹејҳжі•зҡ„еҜӮжҠӨгҖӮеҜӮжҠӨжҳҜз‘ңдјҪиЎҢдёӯи§Ӯжҙҫзҡ„еҲӣе§ӢдәәпјҢд»–еңЁгҖҠдёӯи§Ӯеә„дёҘи®әгҖӢ第93йўӮдёӯпјҢеҚіжҠҠдёӯи§ӮдёҺе”ҜиҜҶжҜ”е–»дёә马иҪҰзҡ„дёӨжқЎзј°з»іпјҢиҜҙеҸӘжңүд№ еҫ—иҝҷдёӨеӯҰжҙҫзҡ„зҗҶи®әзҡ„дәәпјҢжүҚиғҪиҜҙжҲҗжҳҜеӨ§д№ҳдҪӣж•ҷеӯҰиҖ…гҖӮиҝҷз§ҚиҜҙжі•дёәдёӯи§Ӯе’Ңз‘ңдјҪиЎҢжҙҫзҡ„иһҚеҗҲжҢҮеҮәдәҶдёҖдёӘж–№еҗ‘пјҢйҳҝеә•еіЎжІҝзқҖиҝҷдёҖж–№еҗ‘пјҢе°Ҷе…¶е…·дҪ“еҢ–гҖҒе®һи·өеҢ–гҖӮиҝҷе°ұдҪ“зҺ°еңЁ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жүҖйҳҗиҝ°зҡ„次第зҡ„дҝ®д№ иҝҮзЁӢд№ӢдёӯпјҢд»ҺиҖҢдёәиҘҝи—ҸдҪӣж•ҷз•ҢжүҖи®ӨеҗҢгҖҒжҺҘеҸ—гҖӮжӯЈжҳҜеңЁиҝҷдёӘж„Ҹд№үдёҠпјҢжҲ‘们еҸҜд»ҘиҜҙз”ҡж·ұи§ҒдёҺе№ҝеӨ§иЎҢзҡ„з»“еҗҲе§ӢиҮӘйҳҝеә•еіЎгҖӮ
гҖҖгҖҖдёүгҖҒж®ҠиғңеҜҶд№ҳжҚҹзӣҠзҡҶзҰ»
гҖҖгҖҖж”№еҸҳеҪ“ж—¶дәә们еҜ№еҜҶе®—зҡ„дёҚеҗҢзңӢжі•пјҢз»ҷдәҲеҜҶе®—еңЁдҪӣж•ҷдҝ®иЎҢдҪ“зі»дёӯзҡ„еә”жңүдҪҚзҪ®пјҢиҝҷжҳҜйҳҝеә•еіЎ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зҡ„йҮҚиҰҒеҶ…е®№гҖӮеңЁиҝҷйҮҢпјҢйҳҝеә•еіЎзҡ„еҹәжң¬з«ӢеңәжҳҜвҖңдёҚиғҪжҠҠе°Ҹд№ҳгҖҒеӨ§д№ҳе’ҢйҮ‘еҲҡд№ҳи§Ҷдёәзӣёдә’еҲҶеүІзҡ„йғЁеҲҶпјҢеҝ…йЎ»жҠҠе®ғ们и§ҶдёәдёҖжқЎйҒ“и·Ҝзҡ„еҮ з§Қж ·еӯҗвҖқгҖӮиҖҢдё”пјҢеңЁдҝ®д№ еҜҶе®—д№ӢеүҚпјҢдҝ®д№ иҖ…йғҪеҝ…йЎ»зІҫйҖҡ并еқҡжҢҒдҝ®д№ еӨ§е°Ҹд№ҳдҪӣж•ҷзҡ„ж №жң¬жӯҘйӘӨгҖӮйӮЈд№ҲпјҢйҳҝеә•еіЎеҜ№еҜҶе®—зҡ„жҖҒеәҰ究з«ҹжҳҜжҖҺж ·е‘ўпјҹиҝҷеҸҜд»Ҙд»Һ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ҸҠзӣёе…іеҸІж–ҷдёӯеҫ—еҲ°иҜҙжҳҺгҖӮ
гҖҖгҖҖдёҚеҸҜеҗҰи®ӨпјҢеҜҶе®—дҝ®д№ еҜ№дәҺдёҖиҲ¬дәәиҖҢиЁҖпјҢжҳҜдёҖжқЎйқһеёёеҚұйҷ©зҡ„йҒ“и·ҜгҖӮдҪҶвҖңиҝҷз§ҚдҪҝжңӘе…Ҙй—Ёзҡ„еҰ„дәәе •е…Ҙж”ҫиҚЎгҖҒзҪӘжҒ¶зҡ„ең°зӢұзҡ„ж–№жі•пјҢеҚҙиғҪдҪҝе…Ҙй—Ёзҡ„з‘ңдјҪдҝ®иЎҢиҖ…иҫҫеҲ°еҪ»жӮҹвҖқгҖӮйҫҷж ‘д№ҹжӣҫиҜҙиҝҮпјҢеҜҶе®—зҡ„дҝ®д№ е°ұиұЎжҚүжҜ’иӣҮзҡ„еӨҙдёҖж ·пјҢжҺҢжҸЎеҫ—еҘҪзҡ„дәәиғҪд»ҺиӣҮеҸЈдёӯеҸ–еҮәиӣҮзҸ пјҢжҺҢжҸЎдёҚеҘҪзҡ„дәәеҸҚиҖҢдјҡдёәжҜ’иӣҮжүҖдјӨгҖӮйҳҝеә•еіЎж—©е№ҙжӣҫе…Ёиә«еҝғең°дҝ®жҢҒеҜҶжі•пјҢж·ұи°ҷе…¶дёӯзҡ„йҒ“зҗҶгҖӮдёәдәҶеӨ§еӨҡж•°ж №еҷЁе№іе№ізҡ„дәәзҡ„еҲ©зӣҠпјҢд»–еҜ№еҜҶе®—жҢҒдёҖз§Қдҝқз•ҷжҖҒеәҰгҖӮд»–29еІҒж—¶еҮә家пјҢиҪ¬еҗ‘еҜ№жҳҫж•ҷз»Ҹи®әзҡ„еӯҰд№ гҖӮеҗҺжқҘеңЁи¶…жҲ’еҜәж—¶пјҢд»–жӣҫй©ұйҖҗдёҖеҗҚеҜҶе®—еғ§дәәгҖӮиҜҘеғ§дәәжӣҫе°ҶеҘ¶еҸҳжҲҗй…’е–қпјҢвҖңд»–е–қзңӢдёҠеҺ»иұЎеҘ¶дёҖж ·зҡ„й…’пјҢеӣ иҖҢиў«йҳҝеә•еіЎиө¶еҮәи¶…жҲ’вҖқгҖӮиҝҷдәӣдәӢе®һйғҪиЎЁжҳҺдәҶйҳҝеә•еіЎеҜ№еҜҶе®—зҡ„дёҖз§ҚжҲҗзҶҹзҡ„жҖҒеәҰгҖӮйҳҝеә•еіЎе…Ҙи—Ҹејҳжі•пјҢ并жңӘз§ҜжһҒең°еҸӮдёҺеҜҶе®—з»Ҹе…ёзҡ„зј–иҫ‘дёҺзҝ»иҜ‘пјҢиҝҷз§ҚеҒҡжі•жӣҫйҒӯеҲ°еҗҺжңҹеҜҶе®—еӯҰиҖ…зҡ„й—ҙжҺҘжү№иҜ„гҖӮ他们жҠұжҖЁиҜҙе°Ҫз®Ўйҳҝеә•еіЎжң¬дәәйқһеёёзғӯеҲҮең°жғіе®Ји®ІеҜҶе®—пјҢдҪҶиў«е…¶ејҹеӯҗд»Іж•Ұе·ҙеҠқйҳ»иҖҢжІЎжңүе®һж–ҪгҖӮдәӢе®һдёҠпјҢйҳҝеә•еіЎжҳҜе°ҶиҮӘе·ұзҡ„ж•ҷеӯҰйҮҚзӮ№зҪ®дәҺвҖңз»Ҹе…ёзҡ„вҖқжҲ–вҖңеүҚжҖӣзү№зҪ—вҖқеҪўејҸзҡ„еӨ§д№ҳдҪӣж•ҷзҡ„зІҫй«“д№ӢдёҠпјҢиҝҷд»Һ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зҡ„з»„з»Үз»“жһ„дәҰеҸҜзңӢеҮәгҖӮ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Ёж–Ү68йўӮпјҢжңүе…іеҜҶе’’д№ҳзҡ„еҸӘеҚ дәҶ8йўӮгҖӮвҖңйҳҝеә•еіЎеқҡжҢҒеҜ№жҖӣзү№зҪ—е®һи·өзҡ„зңҹжӯЈж„Ҹд№үзҡ„жҙһеҜҹпјҢиҝҷз§ҚжҙһеҜҹж„Ҹе‘ізқҖд»–жң¬дәәеҜ№зҺ°иұЎз•Ңз”ҡж·ұзҰ…е®ҡзҡ„жҹҗдәӣеҪўејҸзҡ„жҺЁиҚҗгҖӮиҝҷдёӘзҺ°иұЎз•Ңжң¬иҙЁдёҠжҳҜдёҚзңҹзҡ„пјҢеӣ жӯӨпјҢд»»дҪ•зҡ„жү§и‘—еҜ№дј—з”ҹиҖҢиЁҖйғҪж„Ҹе‘ізқҖз—ӣиӢҰпјҢиӢҘе…Ғи®ёеҜ№жҖӣзү№зҪ—зҡ„йІҒиҺҪзҡ„е®һи·өпјҢ(е°ұдјҡеҜјиҮҙдј—з”ҹ)жІүиҝ·дәҺжҖӣзү№зҪ—зҡ„ж•‘иөҺпјҢдёҺжӯӨзӣёжҜ”пјҢйҳҝеә•еіЎжң¬дәәжӣҙејәи°ғйҒ“еҫ·зҡ„зәҜеҮҖгҖҒзҰҒж¬Ідё»д№үе’ҢзҰ…е®ҡзҡ„ж–№жі•вҖқгҖӮйҳҝеә•еіЎеҜ№еҜҶе®—жңүжүҖдҝқз•ҷпјҢдҪҶд»–дёҖзӣҙи®ӨдёәеҜҶе’’д№ҳиҫғиҲ¬иӢҘжіўзҪ—иңңеӨҡд№ҳи¶…иғңпјҢжҳҜж— дёҠеӨ§д№ҳдёӯзҡ„жңҖеӨ§д№ҳгҖӮд»–д»ҺжңӘе…¬ејҖиЎЁзӨәжҖҖз–‘еҜҶе®—ж•ҷзӨәзҡ„жқғеЁҒпјҢзӣёеҸҚпјҢд»–д»Қжү№иҜ„йӮЈз§ҚиҪ»и§ҶеҜҶе®—гҖҒжҖҖз–‘еҜҶе®—зҡ„жғіжі•гҖӮд»–еңЁиөҙи—Ҹз»Ҹе°јжіҠе°”ж—¶жӣҫй’ҲеҜ№дёҖдҪҚиҪ»и§ҶеҜҶе’’зҡ„еғ§дәәеҶҷдәҶгҖҠиЎҢйӣҶзҒҜгҖӢ(caryaпјҚsamgraha-pradipa)пјҢж–ҮдёӯиҜҙпјҡвҖңиҺ·еҫ—иҸ©жҸҗдёҚд»…йқ иҲ¬иӢҘжіўзҪ—иңңеӨҡпјҢиҖҢдё”иҝҳиҰҒдҫқйқ еҜҶе’’гҖӮвҖқгҖҠйҮҠж–ҮгҖӢдёӯд№ҹеҸҜзңӢеҲ°йҳҝеә•еіЎеҜ№еҜҶе®—зҡ„жҖҒеәҰпјҢд»–жү№иҜ„дәҶдёӨзұ»дәәпјҢиҜҙеҜ№еҜҶе’’д№ҳеўһзӣҠзҡ„дәәе°Ҷдјҡе •е…ҘжҒ¶и¶ЈпјҢеҜ№иҝҷдәӣдәәеә”д»ҘжӮІеҝғеҺ»жІ»зҪҡпјӣеҜ№еҜҶе’’д№ҳеҮҸжҚҹзҡ„дәәдјҡи¶Је…Ҙжңүжғ…ең°зӢұпјҢеҜ№иҝҷзұ»дәәеә”иҜҘж‘„еҸ—гҖӮе°Өе…¶еҜ№дәҺеҗҺиҖ…пјҢйҳҝеә•еіЎиҜҙпјҡвҖңеҜҶжі•ж—ўж·ұеҘҘеҸҲе№ҝеӨ§пјҢжҳҜеҲ©ж №иҖ…зҡ„иЎҢеўғпјҢжҳҜдҪӣж•ҷзҡ„зІҫеҚҺпјҢжҳҜжҹҗдәӣ(жңүзү№ж®Ҡ)еӣ зјҳгҖҒд№ ж°”е’Ңе–„ж №иҖ…зҡ„иЎҢеўғвҖқгҖӮиҝҷйӣҶдёӯиЎЁжҳҺдәҶйҳҝеә•еіЎеҜ№еҜҶе®—зҡ„жҖҒеәҰгҖӮ
гҖҖгҖҖеӣӣгҖҒеә”жҲҗиҮӘз»ӯеӯ°дёәдҫқжӯў
гҖҖгҖҖйҳҝеә•еіЎдёҖз”ҹжӢңеёҲж— ж•°пјҢеүҚеҗҺе…ұиҫҫ34дәәгҖӮеёҲжүҝе…ізі»д№ҹејӮеёёеӨҚжқӮгҖӮд»–жүҖдҫқжӯўзҡ„дёҠеёҲжңүи®ёеӨҡеҜҶе®—й«ҳеғ§пјҢжңүе°Ҹд№ҳеЈ°й—»еғ§дәәпјҢиҝҳжңүеӨ§д№ҳдёӯи§ӮеӯҰиҖ…еҸҠе”ҜиҜҶеӯҰиҖ…гҖӮдҪҶеңЁ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ҸҠгҖҠйҮҠж–ҮгҖӢдёӯжҳҺж–ҮжҸҗеҸҠзҡ„дёҠеёҲдё»иҰҒжңүиҸ©жҸҗиҙӨгҖҒйҮ‘жҙІжі•з§°еҸҠзҲӘе“ҮеІӣзҡ„д№һйЈҹжҜ”дёҳгҖӮиҸ©жҸҗиҙӨдј йҳҝеә•еіЎе®ҡеӯҰдёҺж…§еӯҰпјҢ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дёӯзҡ„иҝҷдёӨйғЁеҲҶеҮ д№Һе®Ңе…ЁйҮҮз”ЁдәҶиҸ©жҸҗиҙӨдёҖ家зҡ„иҜҙжі•гҖӮйҮ‘жҙІжі•з§°з»ҷдәҲйҳҝеә•еіЎеҸ‘иҸ©жҸҗеҝғзҡ„ж•ҷжҺҲгҖӮд№һйЈҹжҜ”дёҳеҜ№йҳҝеә•еіЎзҡ„еҪұе“Қдё»иҰҒжҳҜеҜҶе®—ж–№йқўзҡ„гҖӮиҝҷ3дҪҚдёҠеёҲдёӯпјҢйҳҝеә•еіЎжңҖдёәеҙҮ敬зҡ„еҸҲжҳҜеүҚдёӨдҪҚпјҢеңЁгҖҠйҮҠж–Ү)зҡ„еҪ’敬йўӮдёӯиҝҷж ·еҶҷйҒ“пјҡвҖңејҘеӢ’ж— и‘—дёҺйҮ‘жҙІпјҢж–Үж®ҠеҜӮеӨ©иҸ©жҸҗиҙӨпјҢиҜҡ敬зӨјиҜёдёҠеёҲе·ІпјҢйҖ еҰӮж—Ҙе…үйҡҫеӨ„йҮҠвҖқгҖӮд»Һ<иҸ©жҸҗйҒ“зӮ¬и®ә)еҶ…е®№зҡ„еҲҶжһҗеҸҠеҪ’敬йўӮпјҢжҲ‘们еҸҜд»ҘиҜҙйҳҝеә•еіЎеҜ№дёӯи§Ӯе’Ңз‘ңдјҪиЎҢжҙҫзҡ„и§ӮзӮ№еқҮжңүжүҖеҗёеҸ–гҖӮеҗ•еҫөе…Ҳз”ҹд№ҹи®Өдёәйҳҝеә•еіЎд№ӢиҜҙе…јйҮҮйҫҷж ‘гҖҒж— и‘—дёӨ家гҖӮиҖҢдё»иҰҒжҳҜвҖңдј еҜӮеӨ©е’Ңдјҡдёӯи§Ӯз‘ңдјҪд№ӢиҜҙеҸҠи¶…жҲ’еҜәиҙҜйҖҡжҳҫеҜҶд№Ӣе®—вҖқгҖӮеңЁдјҡдёӯи§Ӯз‘ңдјҪд№ӢиҜҙж—¶пјҢйҳҝеә•еіЎйҮҮз”Ёзҡ„ж–№жі•жҳҜд»Ҙдёӯи§Ӯи§ҒеҜјз‘ңдјҪиЎҢгҖӮйҳҝеә•еіЎжӣҫеңЁгҖҠйҮҠж–ҮгҖӢдёӯиҮӘиҝ°иҮӘе·ұзҡ„дёӯи§Ӯе®—дј жүҝжҳҜйҫҷж ‘гҖҒжҸҗе©ҶгҖҒжңҲз§°гҖҒжё…иҫЁгҖҒеҜӮеӨ©гҖҒиҸ©жҸҗиҙӨгҖӮиҖҢдё”йҳҝеә•еіЎи®Өдёәдҝ®д№ ж—¶еә”дҫқ照他们жүҖдј зҡ„еҸЈиҜҖгҖӮйҳҝеә•еіЎиҝҳд»Һиғңд№үи°ӣдёҠжү№иҜ„дәҶиҜёжі•е”Ҝеҝғзҡ„иҜҙжі•пјҢ并且иҜҙпјҡвҖңеӨ§з‘ңдјҪеЈ«зңҹжҷәдёӯпјҢдёҚи®ёжңүеҮәд»ҘеҸҠе…ҘпјҢжҳҜж•…дёҚеә”и®ёи§үиҖ…пјҢжңүиҜёж №жң¬дёҺеҗҺеҫ—вҖқгҖӮеҮЎжӯӨз§Қз§ҚпјҢйғҪиҜҙжҳҺйҳҝеә•еіЎзҡ„и§Ғи§ЈжҖ»дҫқдёӯи§ӮгҖӮ>
гҖҖгҖҖеҶҚиҝӣдёҖжӯҘе…·дҪ“еҲҶжһҗпјҢйҳҝеә•еіЎжҳҜдёӯи§Ӯеә”жҲҗжҙҫиҝҳжҳҜдёӯи§ӮиҮӘз»ӯжҙҫпјҹе®—е–Җе·ҙд»ҘеҸҠж јйІҒжҙҫзҡ„е…¶д»–еӨ§еёҲеқҮи®Өдёәйҳҝеә•еіЎжҳҜдёӯи§Ӯеә”жҲҗжҙҫзҡ„дәәзү©гҖӮиҝҷз§Қи§ӮзӮ№еҖјеҫ—е•ҶжҰ·гҖӮеӣ дёәеңЁеүҚйқўи®ІеҲ°дёӯи§Ӯжҙҫдј жүҝж—¶пјҢйҳҝеә•еіЎжҳҜе°ҶжңҲз§°дёҺжё…иҫЁе№¶дёҫпјҢиҖҢдё”д»–и®Өдёәдҝ®д№ ж—¶д№ҹеә”иҜҘвҖңеңЈиҖ…йҫҷж ‘дёҺеңЈеӨ©пјҢжңҲз§°жё…иҫЁдёҺеҜӮеӨ©пјҢе”Ҝеә”дҝ®еҪјжүҖдј иҜҖвҖқгҖӮд»–еҜ№жңҲз§°дёҺжё…иҫЁеҗҢж ·жҺЁеҙҮпјҡвҖңйҳҝйҳҮй»ҺжңҲз§°д№ҹдҫқеңЈйҫҷж ‘зҡ„еҸЈиҜҖиҖҢеҫ—еҲ°(зҺ°и§Ӯ)зңҹи°ӣзҡ„еҠ жҢҒпјҢдәҶжӮҹдёҖеҲҮжі•еҰӮе№»пјҢз•ҷдҪҸеҚ°еәҰеӣӣзҷҫе№ҙпјҢе”ҜиЎҢеҲ©з”ҹд№ӢдәӢгҖӮвҖҰвҖҰйҳҝйҳүй»Һжё…иҫЁд№ҹдҫқйҫҷж ‘зҡ„еҸЈиҜҖпјҢеҪ“з”ҹеҺ»еҲ°жҢҒжҳҺеӨ„вҖқгҖӮйҳҝеә•еіЎжң¬дәәзІҫйҖҡеӣ жҳҺпјҢ15еІҒж—¶пјҢд»…д»…еҗ¬й—»дәҶдёҖж¬ЎгҖҠжӯЈзҗҶдёҖж»ҙгҖӢпјҢ然еҗҺдёҺдёҖвҖңй» ж…§жҲҸи®әеӨ–йҒ“е…ҙиҫ©пјҢд»ӨеҪје •дјҸпјҢзҫҺиӘүйҒҚжү¬вҖқгҖӮдҪҶеңЁ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ҸҠгҖҠйҮҠж–ҮгҖӢдёӯпјҢжҲ‘们зңӢеҲ°йҳҝеә•еіЎжҳҜдёҚйҮҚи§Ҷеӣ жҳҺзҡ„пјҡвҖңиҮӘжҙҫд»ҘеҸҠд»–е®—жҙҫпјҢжҲ–з«ӢиҜёжі•д»ҘдёәжңүпјҢдҪҷиҜҙиҜёжі•д»Ҙдёәж— гҖӮиӢҘи§ӮеҜҹдәҺзңҹе®һжҖ§пјҢиҜҙжңүд»ҘеҸҠиҜҙдёәж— пјҢ究з«ҹд№үдёӯж— еҪјдәҢпјҢжҳҜд»ҘжҜ•з«ҹдёҚиғҪз«ӢгҖӮи„ұзҰ»дёҠеёҲдј жүҝиҖ…пјҢд»ҘжҜ”йҮҸж…§иҷҪиғҪз«ӢпјҢжңүж— д»ҘеҸҠеёёж–ӯзӯүпјҢ然еҪјеҫ’еҠідё”ж— зӣҠгҖӮеҰӮжі•з§°еҸҠжі•иғңзӯүпјҢиҷҪйҖ еӨҡз§Қеӣ жҳҺи®әпјҢ然зҡҶдёәйҷӨеӨ–йҒ“иҜӨпјҢж•…иҜёжҷәиҖ…йҖ ж–Ҝи®әгҖӮеӣ жӯӨдҝ®д№ иғңд№үж—¶пјҢдёҚеҝ…дҫқдәҺжҜ”йҮҸж…§пјҢжҲ‘дәҺд»–и®әе·Іи®®и®«пјҢдәҺжӯӨжҡӮжӢҫдёҚжӣҙиҜҙгҖӮжҳҜж•…еә”еҪ“ејғжҜ”йҮҸпјҢжҖқиҫ©дёәдё»иҜёи®әе…ёпјҢеә”иҜҘдҝ®д№ еңЈйҫҷж ‘пјҢж•ҷзҗҶдј жүҝеҰҷеҸЈиҜҖвҖқгҖӮеңЁиҝҷзӮ№дёҠпјҢйҳҝеә•еіЎд»ҝдҪӣдёҺжңҲз§°еә”жҲҗжҙҫзҡ„и§ӮзӮ№зӣёдјјпјҢеңЁи®ІеҲ°иғңд№үи°ӣзҡ„еҶ…е®№ж—¶пјҢгҖҠйҮҠж–ҮгҖӢзҡ„иҜҙжі•дёҺжңҲз§°гҖҠе…Ҙдёӯи®әгҖӢзҡ„иҜҙжі•е®Ңе…ЁдёҖиҮҙгҖӮгҖҠе…Ҙдёӯи®әгҖӢиҜҙпјҡвҖңеҰӮзң©зҝіеҠӣжүҖеҒҸи®ЎпјҢи§ҒжҜӣеҸ‘зӯүйў еҖ’жҖ§пјҢеҮҖзңјжүҖи§ҒеҪјдҪ“жҖ§пјҢд№ғжҳҜе®һдҪ“жӯӨдәҰе°”вҖқгҖӮгҖҠйҮҠж–ҮгҖӢдёӯиҜҙпјҡвҖңиӯ¬еҰӮзңјз–ҫжңӘзҷ”ж—¶пјҢдёҚиғҪд»Өи§Ғж— жҜӣеҸ‘пјҢдҪ•ж—¶зңјз–ҫеҫ—з—Ҡзҷ”пјҢдёҚиғҪд»Өи§ҒжңүжҜӣеҸ‘гҖӮиӯ¬еҰӮж— жҳҺзң и§үж—¶пјҢдёҚиғҪд»Өи§ҒжңүжўҰеўғпјҢд№ғиҮізқЎзң жңӘйҶ’и§үпјҢдёҚиғҪд»Өе…¶ж— жўҰеўғпјҢдҪ•ж—¶зңјзҝіз—…зҷ”е·ІпјҢеҸҠд»ҺжІүзқЎжўҰдёӯйҶ’пјҢеҲҷж— жҜӣеҸ‘зӯүеҸҠжўҰпјҢдәҰж— жү§еҪјд№ӢеҝғиҜҶгҖӮеҰӮжҳҜж— жҳҺзңјз–ҫйҷӨпјҢеҸҠеҪјжІүзқЎжё…йҶ’ж—¶пјҢжҳҫжңүеҸҠиҜёжүҖз«Ӣжі•пјҢйўҶеҸ—д№ӢиҜҶдәҰзҡҶж— вҖқгҖӮеҪ“然пјҢд»…еҮӯиҝҷдёӨеӨ„并дёҚиғҪиҜҙжҳҺйҳҝеә•еіЎе°ұжҳҜеә”жҲҗжҙҫдәәзү©пјҢиҖҢдё”пјҢ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ҢгҖҠйҮҠж–ҮгҖӢе…¶д»–ең°ж–№д№ҹдёҚиғҪжҳҺжҳҫең°зңӢеҮәйҳҝеә•еіЎзҡ„иҮӘз»ӯжҙҫжҲ–еә”жҲҗжҙҫеҖҫеҗ‘гҖӮеңЁйҳҝеә•еіЎзҡ„е…¶д»–и‘—дҪңдёӯпјҢеҰӮдё“иҜҙи§Ӯзҡ„гҖҠе…ҘдәҢи°ӣгҖӢпјҢжҚ®йҮҠеҰӮзҹіз ”究пјҢд№ҹжҳҜж—ўжңүиҮӘз»ӯжҙҫзҡ„иҜҙжі•пјҢдәҰжңүдёҖдәӣзәҜзІ№е®—дәҺжңҲз§°зҡ„иҜҙжі•гҖӮд№ӢжүҖд»Ҙдә§з”ҹиҝҷз§Қжғ…еҶөпјҢжҲ‘жғіеҸҜиғҪи·ҹйҳҝеә•еіЎйҮҚи§Ҷе®һи·өжңүе…іпјҢз”ҡиҮідёҚжҺ’йҷӨд»–еңЁиҝҷдёӘзӣ®зҡ„дёӢжңүж„Ҹи°ғе’ҢжңҲз§°дёҺжё…иҫЁзҡ„иҜҙжі•гҖӮиҖҢе®—е–Җе·ҙзӯүеӨ§еёҲе°Ҷйҳҝеә•еіЎеҪ’дёәеә”жҲҗжҙҫдәәзү©пјҢд№ҹдёҚжҳҜжІЎжңүзҗҶз”ұгҖӮеӣ дёәиҘҝи—Ҹд»ҘеүҚдј зҡ„йғҪжҳҜдёӯи§ӮиҮӘз»ӯжҙҫзҡ„и®әе…ёпјҢиҖҢеҫҲе°‘зҝ»иҜ‘д»Ӣз»ҚжңҲз§°зҡ„и‘—дҪңпјҢеҫ…йҳҝеә•еіЎе…Ҙи—ҸеҗҺд»Ӣз»ҚжңҲз§°еӯҰиҜҙпјҢе·ҙжӣ№В·е°јзҺӣжүҺзӯүиҜ‘еёҲжүҚеӨ§йҮҸзҝ»иҜ‘жңҲз§°зҡ„и‘—дҪңпјҢеә”жҲҗжҙҫд№ҹеңЁиҘҝи—Ҹе…ҙзӣӣиө·жқҘгҖӮжҲ–и®ёеҮәдәҺиҝҷдёӘеҺҹеӣ пјҢйҳҝеә•еіЎиў«еҲ’еҪ’дәҺдёӯи§Ӯеә”жҲҗжҙҫй—ЁдёӢгҖӮ
гҖҖгҖҖжҖ»д№ӢпјҢеңЁзӣ®еүҚзҡ„з ”з©¶зҠ¶еҶөдёӢпјҢжҲ‘们еҸӘиғҪиҜҙйҳҝеә•еіЎзҡ„дҝ®жҢҒе®—и¶ЈжҳҜд»Ҙдёӯи§Ӯи§ҒеҜјз‘ңдјҪиЎҢгҖӮ
гҖҖгҖҖдә”гҖҒ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Ҝ№иҘҝи—ҸдҪӣж•ҷзҡ„еҪұе“Қ
гҖҖгҖҖ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жҳҜй’ҲеҜ№иҘҝи—ҸдҪӣж•ҷз•Ңзҡ„ејҠз«ҜиҖҢеҶҷзҡ„пјҢеӣ жӯӨе®ғжҳҜж•ҙйЎҝиҘҝи—ҸдҪӣж•ҷзҡ„е®ЈиЁҖд№ҰдёҺжҢҮеҜјд№ҰгҖӮ 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јиҜҙз”ҡж·ұи§ҒдёҺе№ҝеӨ§иЎҢпјҢеңҶж»Ўе®ҢеӨҮпјҢеҸҜд»ҘиҜҙе°ҶеҪ“ж—¶еҚ°еәҰдҪӣж•ҷзҡ„зІҫеҚҺе®Ңе®Ңе…Ёе…Ёд»Ӣз»Қз»ҷдәҶиҘҝи—ҸдҪӣж•ҷз•ҢгҖӮ 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иЁҖз®Җж„Ҹиө…пјҢе…Ёйқўи®Іиҝ°дәҶеӨ§д№ҳдҪӣж•ҷдҝ®д№ зҡ„е…ЁиҝҮзЁӢпјҢе…¶дёӯвҖңе…ҲжҳҫеҗҺеҜҶпјҢжҳҫеҜҶеқҮйҮҚвҖқзҡ„и§ӮзӮ№дҪҝеҫ—иҘҝи—ҸдҪӣж•ҷз•ҢзҗҶи®әзі»з»ҹеҢ–пјҢдҝ®жҢҒ规иҢғеҢ–гҖӮ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д»ҘдҪӣж•ҷеҫ’зҡ„е®һйҷ…дҝ®иЎҢдёәйӘЁе№ІпјҢзі»з»ҹең°е®үжҺ’дәҶдҪӣж•ҷж•ҷеӯҰзҡ„жүҖжңүдё»иҰҒеҶ…е®№гҖӮдҪӣж•ҷзҡ„еҗ„з§ҚзҗҶи®әеқҮеҸҜеңЁиҝҷдёҖдҪ“зі»дёӯжүҫеҲ°зӣёеә”зҡ„дҪҚзҪ®гҖӮиҝҷдёӘдҪ“зі»е°ұжҲҗдёәеҪ“ж—¶жғҹдёҖзҡ„дёҖдёӘеҜ№ж•ҙдёӘдҪӣж•ҷзҡ„зі»з»ҹзҡ„зңӢжі•гҖӮиҝҷдёҖзӮ№пјҢдёҖж–№йқўдёәеҷ¶еҪ“жҙҫзҡ„е…ҙиө·еҮҶеӨҮдәҶжҖқжғіеҹәзЎҖпјҢдёҖж–№йқўеңЁиҘҝи—ҸдҪӣж•ҷз•ҢзЎ®з«ӢдәҶд»Ҙе®һдҝ®дёәдё»зҡ„зІҫзҘһгҖӮиҜҡеҰӮеҗ•еҫөе…Ҳз”ҹжүҖиЁҖпјҡвҖңи—Ҹдј дҪӣеӯҰе…ҲеҗҺеҗ„家йўҮејӮе…¶и¶ЈвҖҰвҖҰеҪ“其移иҜ‘е®Јжү¬пјҢеӣәиҺ«дёҚеҗ„иҮӘжҲҗзҗҶд»Ҙдёә究з«ҹпјҢ然еӨҡж•°ж—¶иҝҮеўғиҝҒпјҢж— д»Ҙдёә继пјҢе…¶еҪұе“ҚеҗҺдё–жңҖдёәж·ұиҝңиҖ…пјҢжғҹжңүйҳҝеә•еіЎдёҖ家иҖҢе·ІгҖӮжҷҡд»ЈжөҒиЎҢе®—е–Җе·ҙд№ӢиҜҙпјҢдәҺжӯӨжӨҚе…¶жёҠжәҗпјҢеӣәдёҚдҝҹиЁҖпјҢеҚіжүҖдҪҷж–°ж—§еҗ„家жҳҫеҜҶд№ӢеӯҰпјҢдәҰеӨҡе°‘дә’зӣёе…іж¶үпјҢж•…жҺЁи®әи—ҸеңҹдҪӣеӯҰдёӯдё»иҰҒд№ӢиҜҙи¶ід»ҘзәІз»ҙдёҖеҲҮиҖ…пјҢеҪ“иҮӘйҳҝеә•еіЎе§Ӣ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е…ӯгҖҒ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дёҺеҷ¶еҪ“жҙҫзҡ„еҲӣз«Ӣ
гҖҖгҖҖйҳҝеә•еіЎеңЁи—Ҹејҳжі•13е№ҙпјҢ收жҺҲејҹеӯҗж— ж•°гҖӮи‘—еҗҚзҡ„жңүйҳҝйҮҢең°еҢәзҡ„иҸ©жҸҗе…үгҖҒд»Ғй’ҰжЎ‘жіўгҖҒйӮЈжҺӘзІ—еўҖжқ°е“Ү(nagпјҚtshoпјҚtshulпјҚkhrimasпјҚrgyalпјҚba)зӯүдәәпјҢеҚ«и—Ҹең°еҢәзҡ„жһҜж•Ұе°ҠиҝҪйӣҚдёӯ(khuпјҚstonпјҚbrtsonпјҚvgrusпјҚgyungпјҚdrung)гҖҒзҝ»иҜ‘еёҲй„ӮеӢ’еҝ…еёҢз»•(rngogпјҚlegsпјҚpaviпјҚshesпјҚrab)гҖҒд»Іж•Ұжқ°еҫ®иҝҘд№ғ(vbromпјҚstonпјҚrgyalпјҚbviпјҚvbyungпјҚgnas)д»ҘеҸҠеӨ§з‘ңдјҪеёҲ(rnalпјҚvbyorпјҚchenпјҚpo)гҖҒиЎ®е·ҙе“Ү(dgonпјҚpaпјҚba)зӯүдәәгҖӮе…¶дёӯд»Ҙд»Іж•Ұе·ҙи·ҹйҡҸйҳҝеә•еіЎжңҖд№…пјҢжүҖеҫ—зҡ„ж•ҷжі•дәҰжңҖж·ұеҺҡе…ЁйқўгҖӮдј иҜҙйҳҝеә•еіЎиөҙи—ҸеүҚеӨ•еҗ‘е…¶жң¬е°ҠиҮіе°Ҡж•‘еәҰжҜҚиҜ·зӨәпјҢеҫ—еҲ°жҺҲи®°иҜҙпјҡвҖңеҺ»иҘҝи—Ҹе°ҶдјҡжңүзӣҠдәҺи—Ҹеңҹжңүжғ…пјҢзү№еҲ«жҳҜеҖҹеҠ©дәҺдёҖдјҳе©ҶеЎһд№ӢеҠӣиҖҢеҲ©зӣҠ(й»‘еҸ‘и—Ҹж°‘)гҖӮвҖқиҝҷйҮҢзҡ„дјҳе©ҶеЎһжҢҮзҡ„е°ұжҳҜд»Іж•Ұе·ҙгҖӮ
гҖҖгҖҖеҷ¶еҪ“жҙҫз”ұйҳҝеә•еіЎзҡ„дёҠйҰ–ејҹеӯҗд»Іж•Ұе·ҙе»әз«ӢгҖӮеҷ¶еҪ“жҙҫжҳҜд»Ҙе…¶жүҖдј ж•ҷжі•зҡ„ж„Ҹд№үжқҘе‘ҪеҗҚгҖӮеҚ•д»ҺиҝҷдёӘеҗҚз§°жҲ‘们е°ұеҸҜзңӢеҮә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зҡ„е·ЁеӨ§еҪұе“ҚгҖӮеӣ дёәеҷ¶(bkav)иҜ‘дёәж•ҷпјҢж•ҷеҚіиЁҖж•ҷпјҢжҢҮдҪӣж•ҷзҡ„дёҖеҲҮжҳҫеҜҶз»Ҹи®әпјӣеҪ“(gdams)иҜ‘дёәж•ҷиҜ«пјҢж•ҷжҺҲпјҢж„ҸдёәеҜ№еғ§еҫ’иЎҢжҢҒдҝ®д№ жҢҮеҜјгҖҒжҢҮзӨәгҖӮеҷ¶еҪ“иҝһиө·жқҘпјҢж„ҸжҖқжҳҜжҠҠдҪӣзҡ„дёҖеҲҮиЁҖж•ҷ(жүҖжңүжҳҫеҜҶз»Ҹи®ә)йғҪзңӢдҪңжҳҜеҜ№дәҺеғ§еҫ’зҡ„иЎҢдёәе’Ңдҝ®жҢҒ(иҝҷеҢ…жӢ¬ж—Ҙеёёзҡ„иЎҢдёәгҖҒвҖңдҝ®еҝғвҖқе’ҢеҜҶж•ҷдҝ®жі•гҖӮдёҖеҸҘиҜқпјҢеҚіжҢҮд»ҺеҮЎеӨ«еҲ°жҲҗдҪӣзҡ„ж•ҙдёӘиҝҮзЁӢ)зҡ„жҢҮзӨәгҖҒжҢҮеҜјгҖӮиҝҷз§ҚзІҫзҘһе’Ң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жҳҜдёҖи„үзӣёжүҝзҡ„гҖӮ
гҖҖгҖҖдәӢе®һд№ҹзҡ„зЎ®еҰӮжӯӨпјҢйҳҝеә•еіЎеңҶеҜӮеҗҺпјҢд»Іж•Ұе·ҙжҲҗдёәйҳҝеә•еіЎдј—еӨҡеҫ’ејҹе’ҢиҝҪйҡҸиҖ…зҡ„йҰ–йўҶе’ҢеёҲй•ҝгҖӮ1056е№ҙпјҢд»Іж•Ұе·ҙзҺҮдј—иҮізғӯжҢҜ(rvaпјҚsgreng)е»әз«ӢзғӯжҢҜеҜәпјҢеҷ¶еҪ“жҙҫеҚід»ҘжӯӨеҜәдёәеҹәең°йҖҗжёҗеҸ‘еұ•еЈ®еӨ§гҖӮд»Іж•Ұе·ҙжңү3дёӘи‘—еҗҚзҡ„ејҹеӯҗпјҡеҚҡеӨҡе“Ү(poпјҚtoпјҚba)гҖҒдә¬дҝ„е·ҙ(spyanпјҚsngaпјҚpa)гҖҒжҷ®з©№е“Ү(phuпјҚchungпјҚba)гҖӮеҚҡеӨҡе“ҮжһҒдёәйҮҚи§Ҷ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пјҢејҖеҮәдәҶеҷ¶еҪ“жҙҫдёӯзҡ„ж•ҷе…ёжҙҫдј жүҝпјҢе®Ји®Іи‘—еҗҚзҡ„вҖңеҷ¶еҪ“дёғи®әвҖқпјҢе…¶дёӯе°ұжңү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гҖӮеҷ¶еҪ“жҙҫзҡ„еҗҚеЈ°д№ҹз”ұдәҺеҚҡеӨҡе“Үзҡ„и®Із»ҸжҺҲеҫ’иҖҢеӨ§ејҳдәҺиҘҝи—ҸгҖӮдә¬дҝ„е·ҙеҲҷ继жүҝдәҶ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йҮҚе®һи·өгҖҒйҮҚдёҠеёҲзҡ„зІҫзҘһпјҢиҖҢејҖеҮәдәҶеҷ¶еҪ“жҙҫдёӯзҡ„ж•ҷжҺҲжҙҫдј жүҝпјҡ他们йҮҚи§ҶдҫқжӯўдёҠеёҲпјҢйҒөз…§дёҠеёҲзҡ„жҢҮеҜјпјҢиҮҙеҠӣдәҺдҝ®жҢҒгҖӮйҳҝеә•еіЎзҡ„еҸҰдёҖејҹеӯҗзәіжҺӘиҜ‘еёҲеҸҠеҶҚдј ејҹеӯҗз»’е·ҙз”Ізҙўе·ҙејҖеҮәдәҶеҷ¶еҪ“жҙҫзҡ„йҒ“йҳ¶жҙҫдј жүҝпјҢд№ҹд»Ҙ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дҪңдёәиҮӘе·ұзҡ„дҝ®жі•ж¬Ўз¬¬гҖӮеҷ¶еҪ“жҙҫеғ§дәәеҚ“еһ„е·ҙзҪ—иҝҪиҝҘд№ғ(groпјҚlungпјҚpaпјҚbioпјҚgrosпјҚvbyungпјҚgnas)дҫқжҚ®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иҖҢеҶҷжҲҗйҳҗйҮҠеҷ¶еҪ“жҙҫж•ҷд№үзҡ„гҖҠйҒ“次第е№ҝи®әгҖӢе’ҢгҖҠж•ҷ次第е№ҝи®әгҖӢгҖӮз”ұдәҺйҳҝеә•еіЎеҸҠе…¶ејҹеӯҗзҡ„еҠӘеҠӣпјҢеҷ¶еҪ“жҙҫеңЁиҘҝи—ҸдҪӣж•ҷз•Ңең°дҪҚж—ҘйҡҶпјҢеңЁе…¬е…ғ11гҖҒ12дё–зәӘиҘҝи—Ҹеҗ„ең°дёәж•°дј—еӨҡзҡ„иҜ‘еёҲдёӯпјҢи®ёеӨҡдәәиҷҪдёҺеҷ¶еҪ“жҙҫж— еёҲжүҝе…ізі»пјҢдҪҶеҚҙиҮӘз§°дёәеҷ¶еҪ“жҙҫдәәгҖӮе…ғжңқж—¶пјҢе…ғжңқе°ҶеҶӣеңЁеҗ‘зҡҮеёқдёҠе‘Ҳзҡ„гҖҠиҜ·зӨәиҝҺи°Ғдёәе®ңзҡ„иҜҰзҰҖгҖӢдёӯиҜҙпјҡвҖңеңЁиҫ№йҮҺзҡ„и—ҸеҢәпјҢеғ§дјҪеӣўдҪ“д»Ҙеҷ¶еҪ“жҙҫдёәеӨ§пјҢвҖҰвҖҰиҚЈиӘүеҫ·жңӣд»Ҙжһіз©ә·敬е®ү(spyanвҖ”ngag)еӨ§еёҲдёәе°ҠвҖҰвҖҰвҖқпјҢз”ұжӯӨдәҰеҸҜи§Ғеҷ¶еҪ“жҙҫзҡ„еҪұе“ҚгҖӮ
гҖҖгҖҖдёғгҖҒеҜ№еҷ¶дёҫжҙҫгҖҒиҗЁиҝҰжҙҫзҡ„еҪұе“Қ
гҖҖгҖҖз”ұдәҺ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ңЁиҘҝи—ҸдҪӣж•ҷз•Ңзҡ„еҪұе“ҚпјҢеҷ¶дёҫжҙҫ(bkavвҖ”brgyudвҖ”pa)гҖҒиҗЁиҝҰжҙҫ(saвҖ”skyaвҖ”pa)дәҰйқһеёёйҮҚи§ҶиҜҘи®әжүҖйҳҗиҝ°зҡ„дҝ®еӯҰ次第гҖӮеҷ¶еҪ“жҙҫе…ҙиө·еҗҺпјҢеҷ¶дёҫжҙҫгҖҒиҗЁиҝҰжҙҫзҡ„и®ёеӨҡеғ§дәәжӣҫеңЁеҷ¶еҪ“жҙҫеҶ…еӯҰд№ иҝҮгҖӮиҫҫжіўеҷ¶дёҫ(dvagsвҖ”poвҖ”bkavвҖ”brgyud)жҙҫзҡ„еҲӣе§ӢдәәеІ—жіўе·ҙ(sgamвҖ”poвҖ”pa)еӨ§еёҲжӣҫеңЁйӮ¬жұқеҢ—йғЁзҡ„еҳүиЈ•е“Ү(byaвҖ”yulвҖ”ba)гҖҒжҹіз»’е·ҙгҖҒз”Іж—ҘиҙЎе–Җе“ҮзӯүдёҠеёҲеә§еүҚеҗ¬еҸ—дәҶи®ёеӨҡеҷ¶еҪ“жҙҫзҡ„ж•ҷжі•в‘ўпјҢи‘—жңүгҖҠеҷ¶еҪ“ж•ҷ法次第и®әгҖӢпјҢеҗҺйҡҸзұіжӢүж—Ҙе·ҙ(miвҖ”laвҖ”rasвҖ”pa)дҝ®д№ еҜҶжі•пјҢиһҚеҗҲеҷ¶еҪ“жҙҫзҡ„ж•ҷжі•е’ҢеӨ§жүӢеҚ°жі•пјҢеҪўжҲҗиҮӘе·ұзҡ„дҪ“зі»гҖӮеҷ¶зҺӣеҷ¶дёҫжҙҫ(karmaвҖ”bkavвҖ”brgyud)зҡ„еҲӣе§ӢдәәйғҪжқҫй’Ұе·ҙ(dusвҖ”gsumвҖ”mkhyenвҖ”pa)пјҢе№ҙиҪ»ж—¶еңЁйҳҝеә•еіЎзҡ„ејҹеӯҗиЈ•еҚҙж—әеҸҠеҶҚдј ејҹеӯҗжүҺжғ№е“Үеә§еүҚеҗ¬еҸ—дәҶиҜёеӨҡйҳҝеә•еіЎзҡ„еҜҶжі•пјҢеҗҺеҸҲд»ҺеӨҸе°”е“Үе·ҙ(sharвҖ”baвҖ”pa)е’Ңе–ңз»•еғ§ж ј(shesвҖ”rabвҖ”sengвҖ”ge)еёҲеҫ’еӯҰеҷ¶еҪ“жҙҫж•ҷжі•6е№ҙгҖӮеҗҺжқҘд»–дҫқжӯўеІ—жіўе·ҙеӨ§еёҲгҖӮеІ—жіўе·ҙдёәд»–и®ІжҺҲдәҶеҷ¶еҪ“жҙҫзҡ„вҖңиҸ©жҸҗйҒ“次第вҖқпјҢ并еҜ№д»–иҜҙпјҡвҖңжҲ‘д№ҹжҳҜдҝ®жӯӨйҒ“次第пјҢдҪ д№ҹдҝ®еҗ§!вҖқиҫҫеһ„еҷ¶дёҫ(stagвҖ”lungвҖ”bkavвҖ”brgyud)жҙҫзҡ„еҲӣе§Ӣдәәиҫҫеһ„еЎҳе·ҙжүҺеёҢиҙқ(stagвҖ”lungвҖ”thangвҖ”paвҖ”bkraвҖ”shisвҖ”dpal)жӣҫи·ҹд»ҺжҖҜе–Җе·ҙ(vchadвҖ”khaвҖ”pa)зӯүдј—еӨҡдёҠеёҲеӯҰд№ жҳҫж•ҷз»Ҹи®әеҸҠеҷ¶еҪ“жҙҫж•ҷжі•гҖӮеҚҙй—·жң—(chosвҖ”smonвҖ”lam)е№је№ҙи·ҹд»ҺжҖҜе–Җе·ҙеӯҰд№ жҲ’еҫӢе’Ңеҷ¶еҪ“жҙҫзҡ„ж•ҷжі•пјҢй•ҝеӨ§еҗҺеҲӣз«Ӣйӣ…жЎ‘еҷ¶дёҫ(gyavвҖ”bzang)жҙҫгҖӮжӯӨеӨ–пјҢйҰҷе·ҙеҷ¶дёҫ(shangsвҖ”paвҖ”bkavвҖ”brgyud)жҙҫеҲқзҘ–зҗјжіўеҚ—дәӨ(khyungвҖ”poвҖ”rnalвҖ”vbyor)еңЁеҚҡеӨҡе“Үејҹеӯҗжң—ж—ҘеЎҳе·ҙ(glangвҖ”riвҖ”thangвҖ”pa)еә§еүҚеҸ—жҜ”дёҳжҲ’гҖӮиүІйЎ¶е“ҮВ·иҝ…йІҒеіЁе№је№ҙеҮә家пјҢеҗ¬еҸ—дәҶз”ұйҳҝеә•еіЎдј жқҘзҡ„гҖҠйҒ“次第ж•ҷжҺҲ)зӯүи®ёеӨҡж•ҷжі•иҖҢдҫқжі•дҝ®иЎҢпјҢд»ҘеҗҺжҲҗдёәеҷ¶дёҫжҙҫеӨ§еҫ·гҖӮиҗЁиҝҰжҙҫдәҰжңүеӨҡдәәеӯҰд№ еҷ¶еҪ“жҙҫзҡ„ж•ҷжі•гҖӮиҗЁиҝҰдәҢзҘ–зҙўеҚ—еӯңж‘©(bsodвҖ”namsвҖ”rtseвҖ”mo)жӣҫеңЁеҷ¶еҪ“жҙҫзҡ„еҜәеәҷжЎ‘жөҰеҜә(gsangвҖ”phu)дёӯи·ҹйҡҸжҒ°е·ҙеҚҙеҗүеғ§ж ј(phyaвҖ”paвҖ”chosвҖ”kyiвҖ”sengвҖ”ge)еӯҰд№ вҖңж…Ҳж°Ҹдә”и®әвҖқеҸҠжі•з§°зҡ„дёғйғЁйҮҸи®әпјҢеҘ е®ҡе…¶жҳҫж•ҷзҗҶи®әзҡ„еҹәзЎҖгҖӮиҗЁиҝҰеӣӣзҘ–иЎ®еҷ¶еқҡиөһ(kunвҖ”dgavвҖ”rgyalвҖ”mtshan)и·ҹйҡҸеӯЈжІғеӢӨе·ҙеҗ¬еҸ—еҷ¶еҪ“жҙҫзҡ„ж•ҷжҺҲгҖӮд»–зҡ„дёҖеҲҮе…ідәҺеӨ§д№ҳе…ұйҒ“зҡ„дҝ®иЎҢи‘—иҝ°пјҢйғҪе®Ңе…Ёдҫқз…§еҷ¶еҪ“жҙҫзҡ„宗规гҖӮиҗЁиҝҰжҙҫеҗҺжқҘзҡ„й«ҳеғ§еӨ§еҫ·пјҢд№ҹдҫқжӯӨиҖҢдҝ®иЎҢгҖӮ
гҖҖгҖҖе…«гҖҒеҜ№ж јйІҒжҙҫзҡ„еҪұе“Қ
гҖҖгҖҖеңЁиҘҝи—ҸдҪӣж•ҷеӣӣеӨ§жҙҫеҲ«дёӯпјҢ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Ҝ№ж јйІҒжҙҫзҡ„еҪұе“ҚжңҖдёәе·ЁеӨ§гҖӮж јйІҒжҙҫеҲӣе§Ӣдәәе®—е–Җе·ҙеӨ§еёҲжӣҫж №жҚ®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еҶҷжҲҗдёҚжңҪеҗҚи‘—гҖҠиҸ©жҸҗйҒ“次第е№ҝи®әгҖӢгҖӮеңЁгҖҠе№ҝи®әгҖӢејҖзҜҮпјҢе®—е–Җе·ҙе°ұиҜҙпјҡвҖңжҖ»жӯӨж•ҷжҺҲпјҢеҚіжҳҜиҮіе°Ҡж…Ҳж°ҸжүҖйҖ пјҢзҺ°и§Ӯеә„дёҘжүҖжңүж•ҷжҺҲпјҢеҲ«еҲҷжӯӨд№Ӣж•ҷе…ёпјҢеҚіжҳҜиҸ©жҸҗйҒ“зӮ¬пјҢж•…еҪјйҖ иҖ…пјҢдәҰеҚіжӯӨд№ӢйҖ иҖ…пјҢеҪјеӨҚеҚіжҳҜеӨ§йҳҝйҳҒй»ҺиғңзҮғзҒҜжҷәпјҢеҲ«и®іе…ұз§°иғңйҳҝеә•еіЎвҖқгҖӮзӣҙиЁҖдёҚи®іең°зӮ№еҮәдәҶйҳҝеә•еіЎеҜ№е…¶зҡ„еҪұе“ҚгҖӮ1409е№ҙе®—е–Җе·ҙеҲӣз«Ӣж јйІҒжҙҫгҖӮ1410е№ҙд»–йҖ дәҶдёҖйҰ–йҡҗиҜӯиҜ—пјҢеҖҹеҠ©зӣёе…іжіЁз–ҸпјҢжҲ‘们зҹҘйҒ“е®—е–Җе·ҙеңЁиҜ—дёӯејәи°ғ他继жүҝдәҶйҳҝеә•еіЎзҡ„ж•ҷжі•дј жүҝпјҢжё…жҘҡең°иЎЁжҳҺе®—е–Җе·ҙжүҖеҲӣз«Ӣзҡ„ж–°ж•ҷжҙҫдёҺйҳҝеә•еіЎејҖеҲӣзҡ„еҷ¶еҪ“жҙҫд№Ӣй—ҙзҡ„继жүҝе…ізі»гҖӮзҺӢжЈ®е…Ҳз”ҹи®ӨдёәвҖңиҝҷдёҖзӮ№еҜ№й»„ж•ҷ(жҢҮж јйІҒжҙҫвҖ”вҖ”еј•иҖ…)д№ӢйӘӨе…ҙеҫҲдёәйҮҚиҰҒпјҢеӣ дёәе®—е–Җе·ҙеҪ“ж—¶еЈ°еҠҝе·ІжһҒжҳҫиө«пјҢеҸҲеҸ—йҳҗеҢ–зҺӢзҡ„еӨ§еҠӣж”ҜжҢҒпјҢд»–ж—ўиҮӘи®Ө继жүҝеҷ¶дё№жҙҫ(еҚіеҷ¶еҪ“жҙҫвҖ”вҖ”еј•иҖ…)пјҢеҲҷдёҺеҷ¶дё№жҙҫеҗ„еҜәжҺҘдёҠжӣҙзӣҙжҺҘзҡ„еҗҢеұһдёҖжҙҫзҡ„е…ізі»гҖӮжӯӨеҗҺеҷ¶дё№жҙҫеӨ§йҮҸеҜәйҷўеӨҡиҮӘеҠЁж”№дёәй»„ж•ҷеұһеҜәпјҢеҜ№еўһејәй»„ж•ҷеҠҝеҠӣпјҢиө·дәҶеҶіе®ҡжҖ§зҡ„дҪңз”ЁвҖқгҖӮдёүеҚҒдёҮпјҢи§ҒгҖҠе…ғеҸІзәӘдәӢжң¬жңӘгҖӢгҖӮвҖҰвҖҰе…¶жүҖи—Ҹе°ҸеЎ”д№ғвҖҳж“Ұж“ҰвҖҷзұ»д№ҹвҖқгҖӮжҳҺеӨҸж—¶ж’°гҖҠй’ұеЎҳж№–еұұиғңжҰӮи®°гҖӢиҝ°пјҢеӨ§дҪӣеҜәз•”вҖңи·ҜжңүиҝҮиЎ—еЎ”пјҢд»ҠеәҹвҖқгҖӮдәӢе®һдёҠпјҢе®қзҹіеұұи—Ҹдј дҪӣиҸ©иҗЁеғҸгҖҒжўөж–Үж‘©еҙ–йҒ—иҝ№пјҢдёҺдёҠиҝ°ж–ҮзҢ®и®°иҪҪзҡ„е…ғ代壶瓶塔гҖҒиҝҮиЎ—еЎ”зӣёдә’еҚ°иҜҒпјҢиЎЁжҳҺиҘҝж№–е®қзҹіеұұе‘Ёиҫ№жҳҜе…ғд»Јжқӯе·һи—Ҹдј дҪӣж•ҷиҫғдёәжҙ»и·ғзҡ„дёҖдёӘеҢәеҹҹгҖӮеҪ“е№ҙзҹ—з«ӢдәҺиҘҝж№–еҢ—еІёе®қзҹіеұұйә“зҡ„и—ҸејҸдҪӣеЎ”гҖҒи—Ҹдј зҹіеҲ»дёҺиҘҝж№–еҚ—йқўзҡ„и—Ҹдј дҪӣеҜәеҗҙеұұе®қжҲҗеҜәйҡ”ж№–йҒҘжңӣпјҢжһ„жҲҗе‘јеә”д№ӢжҖҒгҖӮ
гҖҖгҖҖжқӯе·һең°еҢәзҺ°еӯҳжҳҺд»ЈйҖ еғҸдёәж•°дёҚеӨҡпјҢе®қзҹіеұұжҳҺд»ЈзҹіеҲ»йҖ еғҸйҒ—иҝ№дёәжң¬ең°еҢәжҷҡжңҹдҪӣж•ҷйҖ еғҸйўҳжқҗеҶ…е®№дёҺйЈҺж јзҡ„з ”з©¶еўһеҠ дәҶж–°зҡ„иҢғдҫӢпјҢд»Һйӣ•еҲ»жүӢжі•гҖҒйҫӣеғҸ规模дёҺйҫӣеғҸд№Ӣй—ҙзҡ„е…іиҒ”еәҰзңӢпјҢиҝҷдәӣйҖ еғҸзҡ„ж°‘й—ҙжҖ§иҙЁйўҮдёәжҳҫи‘—пјҢе…¶дёӯд»Ҙ第8йҫӣз«ӢеғҸжңҖе…·зү№иүІгҖӮиҖҢе…ғд»ЈйЈҺж јзҡ„第5йҫӣйҮҠиҝҰдёүе°Ҡж®Ӣиҝ№еҲҷжҲҗдёә继жқӯе·һйЈһжқҘеі°гҖҒеҗҙеұұе®қжҲҗеҜәдёҺзҰҸе»әжіүе·һжё…жәҗеұұд№ӢеҗҺпјҢжҲ‘еӣҪеҚ—ж–№зҡ„еҸҲдёҖе…·жңүи—Ҹдј дҪӣж•ҷиүәжңҜйҹөе‘ізҡ„ж‘©еҙ–йӣ•еҲ»йҒ—иҝ№гҖӮд»ҺйҖ еғҸзҡ„规模дёҺйӣ•еҲ¶жі•еәҰзңӢпјҢж–ҪйҖ иҖ…еҪ“дёәе…·жңүдёҖе®ҡең°дҪҚзҡ„еғ§дәәжҲ–е®ҳе‘ҳгҖӮе®қзҹіеұұйҖ еғҸд№ҹжҲҗдёәжҲ‘еӣҪдёңеҚ—ең°еҢәпјҢйҷӨйЈһжқҘеі°еӨ–第дәҢеӨ„еҮҝжұүи—ҸйҖ еғҸдәҺдёҖеҙ–зҡ„зҹіеҲ»йҖ еғҸзҫӨгҖӮе®қзҹіеұұжўөж–ҮзңҹиЁҖж‘©еҙ–дёҺйҮҠиҝҰдёүе°ҠеӨ§йҫӣдёәе…ғд»Ји—Ҹдј дҪӣж•ҷеңЁжұҹеҚ—дёҖеёҰзҡ„дј ж’ӯдёҺе…ҙзӣӣжҸҗдҫӣдәҶж–°зҡ„е®һзү©дҪҗиҜҒгҖӮ第5йҫӣзҡ„йҖ еғҸпјҢжҜҸе°Ҡйӣ•еЎ‘еҚ•зӢ¬ең°зңӢпјҢеқҮеҗ«иҫғжҳҺжҳҫзҡ„и—Ҹдј дҪӣж•ҷиүәжңҜзү№иүІпјҢдҪҶдёүе°Ҡзҡ„з»„еҗҲеҚҙжӣҙеӨҡең°иЎЁзҺ°еҮәдә”д»Је®Ӣд»ҘйҷҚжұүең°дҪӣгҖҒиҸ©иҗЁдёүе°Ҡзҡ„йҖ еһӢпјҢж•ҙдҪ“жһ„еӣҫдёҺиүәжңҜиЎЁзҺ°зӢ¬зү№гҖӮиҝҷж ·зҡ„йўҳжқҗдёҺйЈҺж јзҡ„дҪңе“ҒеңЁзӣ®еүҚе·ІзҹҘдҪӣж•ҷйӣ•еЎ‘дёӯе°ҡеұһйҰ–дҫӢгҖӮзҹіеҲ»йҒ—иҝ№еҜ№з ”究и—Ҹдј дҪӣж•ҷйҖ еғҸзҡ„йўҳжқҗеҶ…е®№гҖҒеӣҫеғҸеӯҰдёҺйЈҺж јзҡ„еҸ‘еұ•жј”еҸҳпјҢд»ҘеҸҠжұүи—ҸдҪӣж•ҷиүәжңҜзҡ„дәӨжөҒгҖҒеҪұе“ҚйғҪе…·жңүзӢ¬зү№зҡ„ж„Ҹд№үгҖӮ
гҖҖгҖҖдәҢгҖҒж·ұи§Ӯе№ҝиЎҢеҲҶиҖҢеӨҚеҗҲ
гҖҖгҖҖжҚ®й•ҝе°ҫйӣ…дәәе…Ҳз”ҹз ”з©¶пјҢз”ҡж·ұе№ҝеӨ§(GambhirodaraжҲ–Gambhiryaudara)еңЁдёҖиҲ¬еӨ§д№ҳдҪӣж•ҷзҡ„и®әе…ёдёӯжҳҜ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иҜҚжқҘдҪҝз”Ёзҡ„пјҢиҝҷдёӘиҜҚеңЁеҗҺдё–зҡ„е“ІеӯҰдёӯйҖҗжёҗеҲҶзҰ»пјҢ并дҪҝз”ЁвҖңи§ӮвҖқе’ҢвҖңиЎҢвҖқдёӨеӯ—дҪҝд№ӢеҲҶиЈӮдёәдёӨдёӘиҜҚгҖӮиҮідәҺжҳҺзЎ®ең°з”ЁвҖңз”ҡж·ұи§ҒвҖқ(GambhiradarsanaпјҢzab-mo-ltaba)е’ҢвҖңе№ҝеӨ§иЎҢвҖқ(UdaracaritaпјҢrgya-chen-spyod-pa)жқҘз§°е‘јд»Ҙйҫҷж ‘гҖҒжҸҗе©Ҷдёәд»ЈиЎЁзҡ„дёӯи§Ӯзі»з»ҹе’Ңд»Ҙж— и‘—гҖҒдё–дәІдёәд»ЈиЎЁзҡ„з‘ңдјҪиЎҢзі»з»ҹпјҢеҸҜиғҪжңҖж—©и§ҒдәҺиҘҝи—Ҹзҡ„вҖңе®—иҪ®вҖқзұ»и‘—дҪңгҖӮйҖҡиҝҮеҜ№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Ҷ…е®№зҡ„еҲҶжһҗпјҢжҲ‘们еҸҜд»ҘеҸ‘зҺ°пјҢеңЁи®ІеҲ°дҪӣж•ҷжңҖж №жң¬зҡ„зҗҶи®әвҖңз©әвҖқж—¶пјҢ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Ңе…Ёз«ҷеңЁдёӯи§Ӯзҡ„з«ӢеңәдёҠпјҢд»Һеҗ„дёӘж–№йқўи®әиҜҒдәҶвҖңиҜёжі•з©әж— иҮӘжҖ§вҖқпјҢдҪҶеңЁе…·дҪ“зҡ„дҝ®иЎҢе®һи·өж–№йқўпјҢ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йҮҮз”ЁдәҶеӨ§йҮҸзҡ„з‘ңдјҪиЎҢжҙҫзҡ„иҜҙжі•гҖӮ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жүҖйҳҗиҝ°зҡ„дҝ®д№ 次第ж·ұж·ұең°еҪұе“ҚдәҶеҗҺејҳжңҹзҡ„иҘҝи—ҸдҪӣж•ҷгҖӮиҝҷйҮҢзҡ„дёҖдёӘй—®йўҳжҳҜпјҡе°ҶвҖңз”ҡж·ұи§ҒвҖқдёҺвҖңе№ҝеӨ§иЎҢвҖқз»“еҗҲиө·жқҘжҳҜеҗҰе§ӢиҮӘйҳҝеә•еіЎпјҹй•ҝе°ҫйӣ…дәәе…Ҳз”ҹиҜҙпјҡвҖңе®һйҷ…дёҠе°ҶдёӨеӯҰжҙҫеҚівҖҳе№ҝеӨ§иЎҢвҖҷе’ҢвҖҳз”ҡж·ұи§ҒвҖҷз»ҹдёҖиө·жқҘпјҢдҫҝжҳҜж јйІҒжҙҫзҡ„ж•ҷд№үпјҢиҝҷд№ҹжӯЈжҳҜж јйІҒжҙҫжҷ®йҒҚзҡ„дё»еј гҖӮиҝҷдёҖз»ҹдёҖз”ұејҖжҙҫеӨ§еёҲе®—е–Җе·ҙе®һиЎҢдәҶгҖӮжҲ–иҖ…еҶҚиҝҪжәҜеҫ—жӣҙиҝңдәӣпјҢе®—е–Җе·ҙжүҖиЎ·еҝғжҷҜд»°зҡ„йҳҝеә•еіЎе·Із»Ҹе®һиЎҢ дәҶвҖқгҖӮй•ҝе°ҫе…Ҳз”ҹиҝҳеҲ—дәҶдёҖдёӘдёӨжҙҫзҡ„дј жүҝиЎЁпјҢд»ҺиЎЁдёӯжҲ‘们еҸҜд»ҘзңӢеҮәпјҢйҳҝеә•еіЎеңЁдёӨжҙҫзҡ„дј жүҝдёӯеқҮйҮҚеӨҚеҮәзҺ°пјҢеҸҜд»Ҙжғіи§Ғйҳҝеә•еіЎзЎ®е®һеҒҡдәҶе°ҶдёӨжҙҫз»“еҗҲзҡ„еҠӘеҠӣгҖӮдҪҶжҚ®з¬”иҖ…зҡ„иҖғиҷ‘пјҢд№ӢжүҖд»ҘжҠҠйҳҝеә•еіЎдҪңдёәвҖңз”ҡж·ұи§ҒвҖқдёҺвҖңе№ҝеӨ§иЎҢвҖқзҡ„з»“еҗҲиҖ…пјҢдё»иҰҒжҳҜеӣ дёәд»–зҡ„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жҳҜдёҖжң¬зү№еҲ«е®һз”Ёзҡ„и®Іиҝ°дҝ®еӯҰ次第зҡ„вҖңжүӢеҶҢвҖқпјҢд»ҺиҖҢдёәиҘҝи—ҸдәәжүҖйҮҚи§ҶгҖӮе…¶е®һиҝҷз§ҚжҖқжғіиҝҳеә”иҜҘеҫҖеүҚиҝҪжәҜпјҢиҝҷе°ұзүөж¶үеҲ°дёӯи§ӮгҖҒз‘ңдјҪзҡ„еҲҶеҗҲй—®йўҳгҖӮ笔иҖ…жӯӨеӨ„д»…иғҪеҜ№иҝҷдёҖй—®йўҳжҸҗеҮәдёҖзӮ№зІ—жө…зҡ„зңӢжі•гҖӮ
гҖҖгҖҖд»ҺеҗҺжңҹеҚ°еәҰдҪӣж•ҷдёӯи§ӮгҖҒз‘ңдјҪзҡ„иһҚеҗҲжқҘзңӢпјҢдёӨжҙҫзҡ„еҜ№з«Ӣ并йқһжҳҜж°ҙзҒ«дёҚзӣёе®№зҡ„гҖӮеҜ№жӯӨ笔иҖ…зҡ„дёҖдёӘеҹәжң¬з«ӢеңәжҳҜпјҡдёӯи§ӮгҖҒз‘ңдјҪдёӨжҙҫзҡ„жҖқжғіж №жәҗйғҪеңЁдәҺиҲ¬иӢҘпјҢдёӨжҙҫеқҮи®ІдёӯйҒ“пјҢеҸӘдёҚиҝҮдҫ§йҮҚзӮ№дёҚеҗҢпјҢдёӯи§ӮзқҖйҮҚи®ІвҖңзңҹз©әвҖқпјҢз‘ңдјҪзқҖйҮҚи®ІвҖңеҰҷжңүвҖқгҖӮиҷҪ然жңҖз»Ҳзҡ„и§Ји„ұжҳҜзҰ»иЁҖз»қзӣёзҡ„пјҢдҪҶеңЁе…·дҪ“зҡ„дҝ®иЎҢиҝҮзЁӢдёӯеҲҷйңҖиҰҒдёҖдәӣеҲҮе®һзҡ„дҫқзқҖзӮ№пјҢиҝҷдҫҝжҳҜз‘ңдјҪгҖӮ既然дёӨжҙҫ并дёҚзӣёжӮ–пјҢйӮЈд№Ҳд»ҘеҗҺзҡ„еҗҲжөҒд№ҹжҳҜдёҖдёӘеҝ…然зҡ„и¶ӢеҠҝгҖӮвҖңз”ҡж·ұе№ҝеӨ§вҖқд»ҘеүҚжҳҜдёҖдёӘиҜҚпјҢиҝҷдёӘиҜҚвҖңдёҚзҹҘдёҚи§үвҖқең°иў«еҲҶдёәдёӨдёӘиҜҚиҖҢдҪңдёәеҜ№з«Ӣзҡ„еҗҚз§°з”ЁжқҘз§°е‘јдёӨдёӘеӯҰжҙҫгҖӮвҖң然иҖҢд№ҹжӯЈжҳҜиҝҷж ·пјҢд»Ҙиҝҷж ·зҡ„еҗҚз§°з§°е‘јдёӨеӯҰжҙҫеҸҲдёҚзҹҘдёҚи§үең°дҪҝдёӨеӯҰжҙҫиһҚеҗҲпјҢиҝҷдёҖиҝҮзЁӢжҳҜж„ҹи§үдёҚеҲ°зҡ„вҖқгҖӮдҪӣж•ҷиҷҪ然讲жҷәж…§и§Ји„ұпјҢ然дәҰејәи°ғдҝ®иЎҢгҖӮдҪӣйҷҖжҲҗйҒ“жҳҜеңЁиҸ©жҸҗж ‘дёӢйҖҡиҝҮзҰ…е®ҡиҖҢеҫ—пјӣдҪӣйҷҖе…ҘзҒӯж—¶д№ҹе…ҲиЎҢзҰ…е®ҡпјҢ然еҗҺеҮәе®ҡе…ҘзҒӯгҖӮжҚ®еҚ°йЎәжі•еёҲз ”з©¶пјҢж—©жңҹдҪӣж•ҷвҖңз©әвҖқзҡ„жҰӮеҝөеҚідёҺзҰ…е®ҡжңүе…ігҖӮеңЁеҲқжңҹдҪӣж•ҷз»Ҹе…ёдёӯпјҢз©әдёҺйҖӮеҗҲдәҺдҝ®д№ зҰ…и§Ӯзҡ„дҪҸеӨ„жңүе…ігҖӮвҖңдҪҸеңЁз©әеұӢдёӯпјҢжІЎжңүеӨ–жқҘзҡ„еҡЈжқӮзғҰжү°пјҢеҪ“然жҳҜе®Ғйқҷзҡ„пјҢй—ІйҖӮзҡ„гҖӮеңЁиҝҷйҮҢдҝ®д№ зҰ…ж…§пјҢдёҚдёәеӨ–еўғжүҖжғ‘д№ұпјҢдёҚиө·еҶ…еҝғзҡ„зғҰ(еҠЁ)жҒј(д№ұ)пјҢиҝҷз§ҚеҝғеўғпјҢдёҚжӯЈеҰӮз©әеұӢйӮЈж ·зҡ„з©әеҗ—пјҹвҖҰвҖҰд»Ҙз©әеұӢжқҘиұЎеҫҒеҝғз©әеҜӮзҡ„ж„Ҹд№үгҖӮвҖҰвҖҰдҝ®иЎҢиҖ…зҡ„зҰ…ж…§дҪҸеӨ„пјҢжӯЈеҰӮз©әеұӢйӮЈж ·пјҢдәҺжҳҜе°ұз§°дёәз©әдҪҸпјҢз©әдҪҸе®ҡдәҶгҖӮвҖҰвҖҰжүҖд»ҘзҰ…ж…§е®үдҪҸзҡ„еўғең°пјҢд№ҹеҗҚдёәдҪҸпјҢиҖҢжңүз©әдҪҸпјҢеҜӮйқҷдҪҸзӯүеҗҚзӣ®гҖӮжҖ»д№ӢпјҢеңЁз©әй—ІеӨ„дҝ®иЎҢпјҢеј•иө·дәҶд»Ҙз©әжқҘиұЎеҫҒзҰ…ж…§зҡ„еўғең°пјҢжҳҜвҖҳз©әвҖҷд№үдёҚж–ӯжҳӮжү¬зҡ„еҲқжңҹж„Ҹд№үвҖқгҖӮз”ұжӯӨеҸҜзҹҘдёӯи§Ӯе“ІеӯҰзҡ„вҖңз©әвҖқдёҺж—©жңҹзҰ…жі•зҡ„е…ізі»гҖӮдёӯеӣҪзҡ„ж—©жңҹиҜ‘з»Ҹд№ҹеӨҡжҳҜе…ідәҺе°Ҹд№ҳзҰ…ж•°еӯҰж–№йқўзҡ„пјҢеҰӮе®үдё–й«ҳжүҖиҜ‘гҖҠдҝ®иЎҢйҒ“ең°з»ҸгҖӢгҖӮе…¶д№ҰеҗҚдёҺгҖҠз‘ңдјҪеёҲең°и®әгҖӢжҳҜдёҖж ·зҡ„пјҢжҖқжғідәҰеҝ…然жңүдәӣзӣёйҖҡгҖӮгҖҠдҝ®иЎҢйҒ“ең°з»ҸгҖӢзҡ„ж’°йӣҶиҖ…жҳҜе…¬е…ғ1дё–зәӘе·ҰеҸіи‘—еҗҚзҡ„з‘ңдјҪеёҲеғ§дјҪзҪ—еҲ№(samgharaksaпјҢдј—жҠӨ)пјҢи—Ҹж–Үиө„ж–ҷйҮҢиҜҙеҗҺжңҹзҡ„дёӯи§ӮеӯҰ家дҪӣжҠӨгҖҒжё…иҫЁжҳҜдј—жҠӨзҡ„й—ЁдәәпјҢеҗ•еҫөе…Ҳз”ҹжҚ®жӯӨиҖҢиЁҖпјҡвҖңдёӯи§ӮжҙҫдёҺз‘ңдјҪиЎҢжҙҫйғҪжҳҜжқҘжәҗдәҺз‘ңдјҪеёҲзҡ„еҗҢдёҖзі»з»ҹгҖӮвҖқиҝҷдёҖз»“и®әеңЁеӨҡзҪ—йӮЈе®ғзҡ„гҖҠеҚ°еәҰдҪӣж•ҷеҸІгҖӢдёӯдәҰеҸҜеҫ—еҲ°еҚ°иҜҒпјҡвҖң(иҝҰи…»иүІиҝҰзҺӢеҺ»дё–д№Ӣж—¶)пјҢдҝ®жҢҒеӨ§д№ҳж•ҷжі•зҡ„дәәйғҪжҳҜз‘ңдјҪиЎҢиҖ…е”ҜиҜҶеёҲпјҢ他们е…ҲжҳҜеҲҶеҲ«еңЁеҚҒе…«йғЁдёӯеҮә家пјҢйҖҡеёёеҸҲжҳҜдёҺеҗ„йғЁзҡ„дәәеҗҢдҪҸвҖқгҖӮдёӯи§ӮгҖҒз‘ңдјҪиЎҢжҙҫзҡ„е…ұеҗҢзҡ„жқҘжәҗжҳҜз‘ңдјҪеёҲпјҢдҪҶе®ғ们е…ұеҗҢзҡ„зҗҶи®әеҹәзЎҖеә”жҳҜиҲ¬иӢҘз»ҸгҖӮдёӯи§ӮиҮӘдёҚеҝ…иҜҙпјҢйҫҷж ‘е°ұжӣҫйҖ иҝҮиҜҰз»Ҷи§ЈйҮҠиҲ¬иӢҘз»Ҹзҡ„гҖҠеӨ§жҷәеәҰи®әгҖӢпјҢз‘ңдјҪиЎҢжҙҫдәҰжңүи§ЈйҮҠеӨ§е“ҒиҲ¬иӢҘзҡ„гҖҠзҺ°и§Ӯеә„дёҘи®әгҖӢгҖӮз‘ңдјҪиЎҢжҙҫзҡ„ж— и‘—еңЁгҖҠж‘„еӨ§д№ҳи®әгҖӢдёӯиҜҙд»–зҡ„дёүжҖ§иҜҙжқҘиҮӘдәҺиҲ¬иӢҘз»ҸпјҢ并жҠҠе®ғдёҺиҲ¬иӢҘз»Ҹзҡ„йҒ“зҗҶеҠ д»ҘдјҡйҖҡгҖӮиҘҝи—ҸеҸІд№ҰиҜҙж— и‘—жғіеҲ°иҷҪ然е…ұйҖҡзҡ„дёүи—Ҹе’ҢеӨ§д№ҳзҡ„з»Ҹе…ёе®№жҳ“йҖҡжҷ“пјҢдҪҶиҰҒдёҚйҮҚеӨҚдёҚй”ҷд№ұең°зҗҶи§ЈиҲ¬иӢҘжіўзҪ—иңңеӨҡз»Ҹе…ёзҡ„ж„Ҹд№үпјҢе°ұеҫҲеӣ°йҡҫпјҢдәҺжҳҜдә§з”ҹдәІи§Ғжң¬е°ҠзҘһејҘеӢ’зҡ„ж„ҝжңӣпјҢйҖҡиҝҮдҝ®д№ пјҢжңҖз»ҲеңЁејҘеӢ’йқўеүҚеҗ¬еҸ—дәҶжүҖжңүдёҖеҲҮеӨ§д№ҳж•ҷжі•пјҢйҖҡиҫҫдёҖеҲҮз»ҸйғЁд№Ӣд№үзҗҶгҖӮеҗҺжңҹзҡ„з‘ңдјҪиЎҢжҙҫжӣҙдёәйҮҚи§ҶиҲ¬иӢҘз»ҸпјҢд»ҺиҫҫзЈЁжіўзҪ—зҺӢејҖе§ӢпјҢеҸӘжңүиҲ¬иӢҘж•ҷжі•еӨ§дёәзӣӣиЎҢпјӣеңЁйҳҗйҮҠиҲ¬иӢҘз»Ҹж—¶пјҢд№ҹеҗёж”¶дәҶдёӯи§Ӯж— иҮӘжҖ§зҡ„зҗҶи®әгҖӮз‘ңдјҪиЎҢиҖ…еёҲеӯҗиҙӨеңЁдёңеҚ°еәҰжӣҫеҫ—ејҘеӢ’жҺҲи®°пјҡеңЁи§ЈиҜҙиҲ¬иӢҘд№үзҗҶзҡ„и®әе…ёдёӯпјҢеә”з»јеҗҲеҗ„家еҗҲзҗҶйғЁеҲҶгҖӮеңЈиҖ…и§Ји„ұеҶӣдё“дј дё–дәІзҡ„иҲ¬иӢҘеӯҰпјҢд»–д»Ҙдёӯи§Ӯж— иҮӘжҖ§зҡ„д№үзҗҶи§ЈйҮҠгҖҠиҲ¬иӢҘе…«е“ҒдәҢдёҮйўӮгҖӢе’ҢгҖҠзҺ°и§Ӯеә„дёҘи®әгҖӢпјҢжҳҜжҸүе’ҢгҖҠиҲ¬иӢҘгҖӢдёҺгҖҠи§ӮзҺ°еә„дёҘи®әгҖӢиҖҢйҖ и®әзҡ„ејҖеҲӣиҖ…гҖӮеҸҜд»ҘиҜҙпјҢдёӯи§ӮгҖҒз‘ңдјҪдёӨжҙҫеңЁи§ЈйҮҠиҲ¬иӢҘз»ҸдёҠйҮҮз”ЁдәҶдёҚеҗҢзҡ„и§’еәҰпјҢдёӯи§Ӯд»ҺвҖңеҪ“дҪ“еҚіз©әвҖқзҡ„и§’еәҰжқҘжҺўи®Ёж— иҮӘжҖ§пјҢз‘ңдјҪиЎҢжҙҫеҲҷд»ҺеҝғиҜҶзҡ„и§’еәҰжҺўи®Ёж— иҮӘжҖ§гҖӮ гҖҠйҮ‘еҲҡз»ҸгҖӢдёӯиҜҙпјҡвҖңдёҖеҲҮжңүдёәжі•пјҢеҰӮжўҰе№»жіЎеҪұпјҢеҰӮйңІдәҰеҰӮз”өпјҢеә”дҪңеҰӮжҳҜи§ӮвҖқгҖӮжӯӨеӨ„зҡ„вҖңеҰӮжўҰе№»вҖқзӯүе°ұжҳҜжҢҮдәәзҡ„ж„ҸиҜҶжҲ–ж„ҸиҜҶзҡ„дҪңз”ЁпјҢжҠҠеӨ–зү©зҡ„еӯҳеңЁдёҺдәәзҡ„ж„ҸиҜҶиҒ”зі»иө·жқҘгҖӮгҖҠеӨ§жҷәеәҰи®әгҖӢдёӯи®ІпјҡвҖңдёүз•ҢжүҖжңүпјҢзҡҶеҝғжүҖдҪңвҖқгҖӮдәҰз»ҷз‘ңдјҪиЎҢжҙҫзҡ„еҸ‘еұ•жҸҗдҫӣдәҶжҖқи·ҜгҖӮеҸҰдёҖж–№йқўпјҢгҖҠеӨ§жҷәеәҰи®әгҖӢиҜҙпјҡвҖңж‘©иҜғиЎҚз©әй—ЁиҖ…пјҢдёҖеҲҮиҜёжі•жҖ§еёёиҮӘз©әпјҢдёҚд»Ҙжҷәж…§ж–№дҫҝи§Ӯж•…з©әвҖқгҖӮжҚ®ж—Ҙжң¬еӯҰиҖ…з ”з©¶пјҢиҜҙиҝҷеҸҘиҜқеҸҜиғҪе·Іжҡ—еҗ«дәҶе”ҜиҜҶеӯҰзҡ„дә§з”ҹгҖӮе”ҜиҜҶеӯҰе°ұжҳҜдёәдәҶеҜ»жүҫдёҖз§ҚеҸҰеӨ–зҡ„йҖ”еҫ„жқҘиҜҒжҲҗз©әд№үпјҢжқҘдҪҝдәә们и®ӨиҜҶеҲ°з©әгҖӮд»Һдҝ®иЎҢж–№йқўиҖҢиЁҖпјҢеҲқжңҹгҖҒдёӯжңҹдёӯи§ӮжҙҫйғҪдёҚеҝҪи§ҶиҸ©иҗЁеҚҒең°зҡ„з‘ңдјҪж–№жі•пјҢйҫҷж ‘дәҰеҘ–еҠұеҚҒең°з‘ңдјҪгҖӮжңҲз§°гҖҠе…Ҙдёӯи®әгҖӢйҖҡиҝҮи§ЈиҜҙдҪңдёәиҸ©иҗЁзҡ„дҝ®д№ йҳ¶дҪҚзҡ„еҚҒең°иҖҢйҳҗжҳҺдёӯи§ӮжҖқжғігҖӮжҠҠиҝҷеҚҒең°дёҺдёӯи§ӮжҖқжғіеҠ д»Ҙз»“еҗҲзҡ„еҖҫеҗ‘пјҢжҳҜе…¶еҗҺжңҹдёӯи§Ӯжҙҫзҡ„еӯҰиҖ…жүҖзү№еҲ«ејәи°ғзҡ„дәӢгҖӮ
гҖҖгҖҖз”ұдёҠжүҖиҝ°еҸҜзҹҘпјҢйҳҝеә•еіЎеңЁ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дёӯдјҡйҖҡдёӯи§Ӯз‘ңдјҪд№ӢиҜҙ并йқһеҒ¶з„¶пјҢиҖҢжңүе…¶ж·ұеҺҡзҡ„жҖқжғіжёҠжәҗгҖӮйҳҝеә•еіЎзҡ„жҖқжғіжӣҙзӣҙжҺҘзҡ„жқҘжәҗеә”жҳҜ8дё–зәӘе…Ҙи—Ҹејҳжі•зҡ„еҜӮжҠӨгҖӮеҜӮжҠӨжҳҜз‘ңдјҪиЎҢдёӯи§Ӯжҙҫзҡ„еҲӣе§ӢдәәпјҢд»–еңЁгҖҠдёӯи§Ӯеә„дёҘи®әгҖӢ第93йўӮдёӯпјҢеҚіжҠҠдёӯи§ӮдёҺе”ҜиҜҶжҜ”е–»дёә马иҪҰзҡ„дёӨжқЎзј°з»іпјҢиҜҙеҸӘжңүд№ еҫ—иҝҷдёӨеӯҰжҙҫзҡ„зҗҶи®әзҡ„дәәпјҢжүҚиғҪиҜҙжҲҗжҳҜеӨ§д№ҳдҪӣж•ҷеӯҰиҖ…гҖӮиҝҷз§ҚиҜҙжі•дёәдёӯи§Ӯе’Ңз‘ңдјҪиЎҢжҙҫзҡ„иһҚеҗҲжҢҮеҮәдәҶдёҖдёӘж–№еҗ‘пјҢйҳҝеә•еіЎжІҝзқҖиҝҷдёҖж–№еҗ‘пјҢе°Ҷе…¶е…·дҪ“еҢ–гҖҒе®һи·өеҢ–гҖӮиҝҷе°ұдҪ“зҺ°еңЁ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жүҖйҳҗиҝ°зҡ„次第зҡ„дҝ®д№ иҝҮзЁӢд№ӢдёӯпјҢд»ҺиҖҢдёәиҘҝи—ҸдҪӣж•ҷз•ҢжүҖи®ӨеҗҢгҖҒжҺҘеҸ—гҖӮжӯЈжҳҜеңЁиҝҷдёӘж„Ҹд№үдёҠпјҢжҲ‘们еҸҜд»ҘиҜҙз”ҡж·ұи§ҒдёҺе№ҝеӨ§иЎҢзҡ„з»“еҗҲе§ӢиҮӘйҳҝеә•еіЎгҖӮ
гҖҖгҖҖдёғгҖҒеҜ№еҷ¶дёҫжҙҫгҖҒиҗЁиҝҰжҙҫзҡ„еҪұе“Қ
гҖҖгҖҖз”ұдәҺ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ңЁиҘҝи—ҸдҪӣж•ҷз•Ңзҡ„еҪұе“ҚпјҢеҷ¶дёҫжҙҫ(bkavвҖ”brgyudвҖ”pa)гҖҒиҗЁиҝҰжҙҫ(saвҖ”skyaвҖ”pa)дәҰйқһеёёйҮҚи§ҶиҜҘи®әжүҖйҳҗиҝ°зҡ„дҝ®еӯҰ次第гҖӮеҷ¶еҪ“жҙҫе…ҙиө·еҗҺпјҢеҷ¶дёҫжҙҫгҖҒиҗЁиҝҰжҙҫзҡ„и®ёеӨҡеғ§дәәжӣҫеңЁеҷ¶еҪ“жҙҫеҶ…еӯҰд№ иҝҮгҖӮиҫҫжіўеҷ¶дёҫ(dvagsвҖ”poвҖ”bkavвҖ”brgyud)жҙҫзҡ„еҲӣе§ӢдәәеІ—жіўе·ҙ(sgamвҖ”poвҖ”pa)еӨ§еёҲжӣҫеңЁйӮ¬жұқеҢ—йғЁзҡ„еҳүиЈ•е“Ү(byaвҖ”yulвҖ”ba)гҖҒжҹіз»’е·ҙгҖҒз”Іж—ҘиҙЎе–Җе“ҮзӯүдёҠеёҲеә§еүҚеҗ¬еҸ—дәҶи®ёеӨҡеҷ¶еҪ“жҙҫзҡ„ж•ҷжі•в‘ўпјҢи‘—жңүгҖҠеҷ¶еҪ“ж•ҷ法次第и®әгҖӢпјҢеҗҺйҡҸзұіжӢүж—Ҙе·ҙ(miвҖ”laвҖ”rasвҖ”pa)дҝ®д№ еҜҶжі•пјҢиһҚеҗҲеҷ¶еҪ“жҙҫзҡ„ж•ҷжі•е’ҢеӨ§жүӢеҚ°жі•пјҢеҪўжҲҗиҮӘе·ұзҡ„дҪ“зі»гҖӮеҷ¶зҺӣеҷ¶дёҫжҙҫ(karmaвҖ”bkavвҖ”brgyud)зҡ„еҲӣе§ӢдәәйғҪжқҫй’Ұе·ҙ(dusвҖ”gsumвҖ”mkhyenвҖ”pa)пјҢе№ҙиҪ»ж—¶еңЁйҳҝеә•еіЎзҡ„ејҹеӯҗиЈ•еҚҙж—әеҸҠеҶҚдј ејҹеӯҗжүҺжғ№е“Үеә§еүҚеҗ¬еҸ—дәҶиҜёеӨҡйҳҝеә•еіЎзҡ„еҜҶжі•пјҢеҗҺеҸҲд»ҺеӨҸе°”е“Үе·ҙ(sharвҖ”baвҖ”pa)е’Ңе–ңз»•еғ§ж ј(shesвҖ”rabвҖ”sengвҖ”ge)еёҲеҫ’еӯҰеҷ¶еҪ“жҙҫж•ҷжі•6е№ҙгҖӮеҗҺжқҘд»–дҫқжӯўеІ—жіўе·ҙеӨ§еёҲгҖӮеІ—жіўе·ҙдёәд»–и®ІжҺҲдәҶеҷ¶еҪ“жҙҫзҡ„вҖңиҸ©жҸҗйҒ“次第вҖқпјҢ并еҜ№д»–иҜҙпјҡвҖңжҲ‘д№ҹжҳҜдҝ®жӯӨйҒ“次第пјҢдҪ д№ҹдҝ®еҗ§!вҖқиҫҫеһ„еҷ¶дёҫ(stagвҖ”lungвҖ”bkavвҖ”brgyud)жҙҫзҡ„еҲӣе§Ӣдәәиҫҫеһ„еЎҳе·ҙжүҺеёҢиҙқ(stagвҖ”lungвҖ”thangвҖ”paвҖ”bkraвҖ”shisвҖ”dpal)жӣҫи·ҹд»ҺжҖҜе–Җе·ҙ(vchadвҖ”khaвҖ”pa)зӯүдј—еӨҡдёҠеёҲеӯҰд№ жҳҫж•ҷз»Ҹи®әеҸҠеҷ¶еҪ“жҙҫж•ҷжі•гҖӮеҚҙй—·жң—(chosвҖ”smonвҖ”lam)е№је№ҙи·ҹд»ҺжҖҜе–Җе·ҙеӯҰд№ жҲ’еҫӢе’Ңеҷ¶еҪ“жҙҫзҡ„ж•ҷжі•пјҢй•ҝеӨ§еҗҺеҲӣз«Ӣйӣ…жЎ‘еҷ¶дёҫ(gyavвҖ”bzang)жҙҫгҖӮжӯӨеӨ–пјҢйҰҷе·ҙеҷ¶дёҫ(shangsвҖ”paвҖ”bkavвҖ”brgyud)жҙҫеҲқзҘ–зҗјжіўеҚ—дәӨ(khyungвҖ”poвҖ”rnalвҖ”vbyor)еңЁеҚҡеӨҡе“Үејҹеӯҗжң—ж—ҘеЎҳе·ҙ(glangвҖ”riвҖ”thangвҖ”pa)еә§еүҚеҸ—жҜ”дёҳжҲ’гҖӮиүІйЎ¶е“ҮВ·иҝ…йІҒеіЁе№је№ҙеҮә家пјҢеҗ¬еҸ—дәҶз”ұйҳҝеә•еіЎдј жқҘзҡ„гҖҠйҒ“次第ж•ҷжҺҲ)зӯүи®ёеӨҡж•ҷжі•иҖҢдҫқжі•дҝ®иЎҢпјҢд»ҘеҗҺжҲҗдёәеҷ¶дёҫжҙҫеӨ§еҫ·гҖӮиҗЁиҝҰжҙҫдәҰжңүеӨҡдәәеӯҰд№ еҷ¶еҪ“жҙҫзҡ„ж•ҷжі•гҖӮиҗЁиҝҰдәҢзҘ–зҙўеҚ—еӯңж‘©(bsodвҖ”namsвҖ”rtseвҖ”mo)жӣҫеңЁеҷ¶еҪ“жҙҫзҡ„еҜәеәҷжЎ‘жөҰеҜә(gsangвҖ”phu)дёӯи·ҹйҡҸжҒ°е·ҙеҚҙеҗүеғ§ж ј(phyaвҖ”paвҖ”chosвҖ”kyiвҖ”sengвҖ”ge)еӯҰд№ вҖңж…Ҳж°Ҹдә”и®әвҖқеҸҠжі•з§°зҡ„дёғйғЁйҮҸи®әпјҢеҘ е®ҡе…¶жҳҫж•ҷзҗҶи®әзҡ„еҹәзЎҖгҖӮиҗЁиҝҰеӣӣзҘ–иЎ®еҷ¶еқҡиөһ(kunвҖ”dgavвҖ”rgyalвҖ”mtshan)и·ҹйҡҸеӯЈжІғеӢӨе·ҙеҗ¬еҸ—еҷ¶еҪ“жҙҫзҡ„ж•ҷжҺҲгҖӮд»–зҡ„дёҖеҲҮе…ідәҺеӨ§д№ҳе…ұйҒ“зҡ„дҝ®иЎҢи‘—иҝ°пјҢйғҪе®Ңе…Ёдҫқз…§еҷ¶еҪ“жҙҫзҡ„宗规гҖӮиҗЁиҝҰжҙҫеҗҺжқҘзҡ„й«ҳеғ§еӨ§еҫ·пјҢд№ҹдҫқжӯӨиҖҢдҝ®иЎҢгҖӮ
гҖҖгҖҖе…«гҖҒеҜ№ж јйІҒжҙҫзҡ„еҪұе“Қ
гҖҖгҖҖеңЁиҘҝи—ҸдҪӣж•ҷеӣӣеӨ§жҙҫеҲ«дёӯпјҢ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гҖӢеҜ№ж јйІҒжҙҫзҡ„еҪұе“ҚжңҖдёәе·ЁеӨ§гҖӮж јйІҒжҙҫеҲӣе§Ӣдәәе®—е–Җе·ҙеӨ§еёҲжӣҫж №жҚ®гҖҠиҸ©жҸҗйҒ“зӮ¬и®ә)еҶҷжҲҗдёҚжңҪеҗҚи‘—гҖҠиҸ©жҸҗйҒ“次第е№ҝи®әгҖӢгҖӮеңЁгҖҠе№ҝи®әгҖӢејҖзҜҮпјҢе®—е–Җе·ҙе°ұиҜҙпјҡвҖңжҖ»жӯӨж•ҷжҺҲпјҢеҚіжҳҜиҮіе°Ҡж…Ҳж°ҸжүҖйҖ пјҢзҺ°и§Ӯеә„дёҘжүҖжңүж•ҷжҺҲпјҢеҲ«еҲҷжӯӨд№Ӣж•ҷе…ёпјҢеҚіжҳҜиҸ©жҸҗйҒ“зӮ¬пјҢж•…еҪјйҖ иҖ…пјҢдәҰеҚіжӯӨд№ӢйҖ иҖ…пјҢеҪјеӨҚеҚіжҳҜеӨ§йҳҝйҳҒй»ҺиғңзҮғзҒҜжҷәпјҢеҲ«и®іе…ұз§°иғңйҳҝеә•еіЎвҖқгҖӮзӣҙиЁҖдёҚи®іең°зӮ№еҮәдәҶйҳҝеә•еіЎеҜ№е…¶зҡ„еҪұе“ҚгҖӮ1409е№ҙе®—е–Җе·ҙеҲӣз«Ӣж јйІҒжҙҫгҖӮ1410е№ҙд»–йҖ дәҶдёҖйҰ–йҡҗиҜӯиҜ—пјҢеҖҹеҠ©зӣёе…іжіЁз–ҸпјҢжҲ‘们зҹҘйҒ“е®—е–Җе·ҙеңЁиҜ—дёӯејәи°ғ他继жүҝдәҶйҳҝеә•еіЎзҡ„ж•ҷжі•дј жүҝпјҢжё…жҘҡең°иЎЁжҳҺе®—е–Җе·ҙжүҖеҲӣз«Ӣзҡ„ж–°ж•ҷжҙҫдёҺйҳҝеә•еіЎејҖеҲӣзҡ„еҷ¶еҪ“жҙҫд№Ӣй—ҙзҡ„继жүҝе…ізі»гҖӮзҺӢжЈ®е…Ҳз”ҹи®ӨдёәвҖңиҝҷдёҖзӮ№еҜ№й»„ж•ҷ(жҢҮж јйІҒжҙҫвҖ”вҖ”еј•иҖ…)д№ӢйӘӨе…ҙеҫҲдёәйҮҚиҰҒпјҢеӣ дёәе®—е–Җе·ҙеҪ“ж—¶еЈ°еҠҝе·ІжһҒжҳҫиө«пјҢеҸҲеҸ—йҳҗеҢ–зҺӢзҡ„еӨ§еҠӣж”ҜжҢҒпјҢд»–ж—ўиҮӘи®Ө继жүҝеҷ¶дё№жҙҫ(еҚіеҷ¶еҪ“жҙҫвҖ”вҖ”еј•иҖ…)пјҢеҲҷдёҺеҷ¶дё№жҙҫеҗ„еҜәжҺҘдёҠжӣҙзӣҙжҺҘзҡ„еҗҢеұһдёҖжҙҫзҡ„е…ізі»гҖӮжӯӨеҗҺеҷ¶дё№жҙҫеӨ§йҮҸеҜәйҷўеӨҡиҮӘеҠЁж”№дёәй»„ж•ҷеұһеҜәпјҢеҜ№еўһејәй»„ж•ҷеҠҝеҠӣпјҢиө·дәҶеҶіе®ҡжҖ§зҡ„дҪңз”ЁвҖқгҖӮдёүеҚҒдёҮпјҢи§ҒгҖҠе…ғеҸІзәӘдәӢжң¬жңӘгҖӢгҖӮвҖҰвҖҰе…¶жүҖи—Ҹе°ҸеЎ”д№ғвҖҳж“Ұж“ҰвҖҷзұ»д№ҹвҖқгҖӮжҳҺеӨҸж—¶ж’°гҖҠй’ұеЎҳж№–еұұиғңжҰӮи®°гҖӢиҝ°пјҢеӨ§дҪӣеҜәз•”вҖңи·ҜжңүиҝҮиЎ—еЎ”пјҢд»ҠеәҹвҖқгҖӮдәӢе®һдёҠпјҢе®қзҹіеұұи—Ҹдј дҪӣиҸ©иҗЁеғҸгҖҒжўөж–Үж‘©еҙ–йҒ—иҝ№пјҢдёҺдёҠиҝ°ж–ҮзҢ®и®°иҪҪзҡ„е…ғ代壶瓶塔гҖҒиҝҮиЎ—еЎ”зӣёдә’еҚ°иҜҒпјҢиЎЁжҳҺиҘҝж№–е®қзҹіеұұе‘Ёиҫ№жҳҜе…ғд»Јжқӯе·һи—Ҹдј дҪӣж•ҷиҫғдёәжҙ»и·ғзҡ„дёҖдёӘеҢәеҹҹгҖӮеҪ“е№ҙзҹ—з«ӢдәҺиҘҝж№–еҢ—еІёе®қзҹіеұұйә“зҡ„и—ҸејҸдҪӣеЎ”гҖҒи—Ҹдј зҹіеҲ»дёҺиҘҝж№–еҚ—йқўзҡ„и—Ҹдј дҪӣеҜәеҗҙеұұе®қжҲҗеҜәйҡ”ж№–йҒҘжңӣпјҢжһ„жҲҗе‘јеә”д№ӢжҖҒгҖӮ
гҖҖгҖҖжқӯе·һең°еҢәзҺ°еӯҳжҳҺд»ЈйҖ еғҸдёәж•°дёҚеӨҡпјҢе®қзҹіеұұжҳҺд»ЈзҹіеҲ»йҖ еғҸйҒ—иҝ№дёәжң¬ең°еҢәжҷҡжңҹдҪӣж•ҷйҖ еғҸйўҳжқҗеҶ…е®№дёҺйЈҺж јзҡ„з ”з©¶еўһеҠ дәҶж–°зҡ„иҢғдҫӢпјҢд»Һйӣ•еҲ»жүӢжі•гҖҒйҫӣеғҸ规模дёҺйҫӣеғҸд№Ӣй—ҙзҡ„е…іиҒ”еәҰзңӢпјҢиҝҷдәӣйҖ еғҸзҡ„ж°‘й—ҙжҖ§иҙЁйўҮдёәжҳҫи‘—пјҢе…¶дёӯд»Ҙ第8йҫӣз«ӢеғҸжңҖе…·зү№иүІгҖӮиҖҢе…ғд»ЈйЈҺж јзҡ„第5йҫӣйҮҠиҝҰдёүе°Ҡж®Ӣиҝ№еҲҷжҲҗдёә继жқӯе·һйЈһжқҘеі°гҖҒеҗҙеұұе®қжҲҗеҜәдёҺзҰҸе»әжіүе·һжё…жәҗеұұд№ӢеҗҺпјҢжҲ‘еӣҪеҚ—ж–№зҡ„еҸҲдёҖе…·жңүи—Ҹдј дҪӣж•ҷиүәжңҜйҹөе‘ізҡ„ж‘©еҙ–йӣ•еҲ»йҒ—иҝ№гҖӮд»ҺйҖ еғҸзҡ„规模дёҺйӣ•еҲ¶жі•еәҰзңӢпјҢж–ҪйҖ иҖ…еҪ“дёәе…·жңүдёҖе®ҡең°дҪҚзҡ„еғ§дәәжҲ–е®ҳе‘ҳгҖӮе®қзҹіеұұйҖ еғҸд№ҹжҲҗдёәжҲ‘еӣҪдёңеҚ—ең°еҢәпјҢйҷӨйЈһжқҘеі°еӨ–第дәҢеӨ„еҮҝжұүи—ҸйҖ еғҸдәҺдёҖеҙ–зҡ„зҹіеҲ»йҖ еғҸзҫӨгҖӮе®қзҹіеұұжўөж–ҮзңҹиЁҖж‘©еҙ–дёҺйҮҠиҝҰдёүе°ҠеӨ§йҫӣдёәе…ғд»Ји—Ҹдј дҪӣж•ҷеңЁжұҹеҚ—дёҖеёҰзҡ„дј ж’ӯдёҺе…ҙзӣӣжҸҗдҫӣдәҶж–°зҡ„е®һзү©дҪҗиҜҒгҖӮ第5йҫӣзҡ„йҖ еғҸпјҢжҜҸе°Ҡйӣ•еЎ‘еҚ•зӢ¬ең°зңӢпјҢеқҮеҗ«иҫғжҳҺжҳҫзҡ„и—Ҹдј дҪӣж•ҷиүәжңҜзү№иүІпјҢдҪҶдёүе°Ҡзҡ„з»„еҗҲеҚҙжӣҙеӨҡең°иЎЁзҺ°еҮәдә”д»Је®Ӣд»ҘйҷҚжұүең°дҪӣгҖҒиҸ©иҗЁдёүе°Ҡзҡ„йҖ еһӢпјҢж•ҙдҪ“жһ„еӣҫдёҺиүәжңҜиЎЁзҺ°зӢ¬зү№гҖӮиҝҷж ·зҡ„йўҳжқҗдёҺйЈҺж јзҡ„дҪңе“ҒеңЁзӣ®еүҚе·ІзҹҘдҪӣж•ҷйӣ•еЎ‘дёӯе°ҡеұһйҰ–дҫӢгҖӮзҹіеҲ»йҒ—иҝ№еҜ№з ”究и—Ҹдј дҪӣж•ҷйҖ еғҸзҡ„йўҳжқҗеҶ…е®№гҖҒеӣҫеғҸеӯҰдёҺйЈҺж јзҡ„еҸ‘еұ•жј”еҸҳпјҢд»ҘеҸҠжұүи—ҸдҪӣж•ҷиүәжңҜзҡ„дәӨжөҒгҖҒеҪұе“ҚйғҪе…·жңүзӢ¬зү№зҡ„ж„Ҹд№ү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