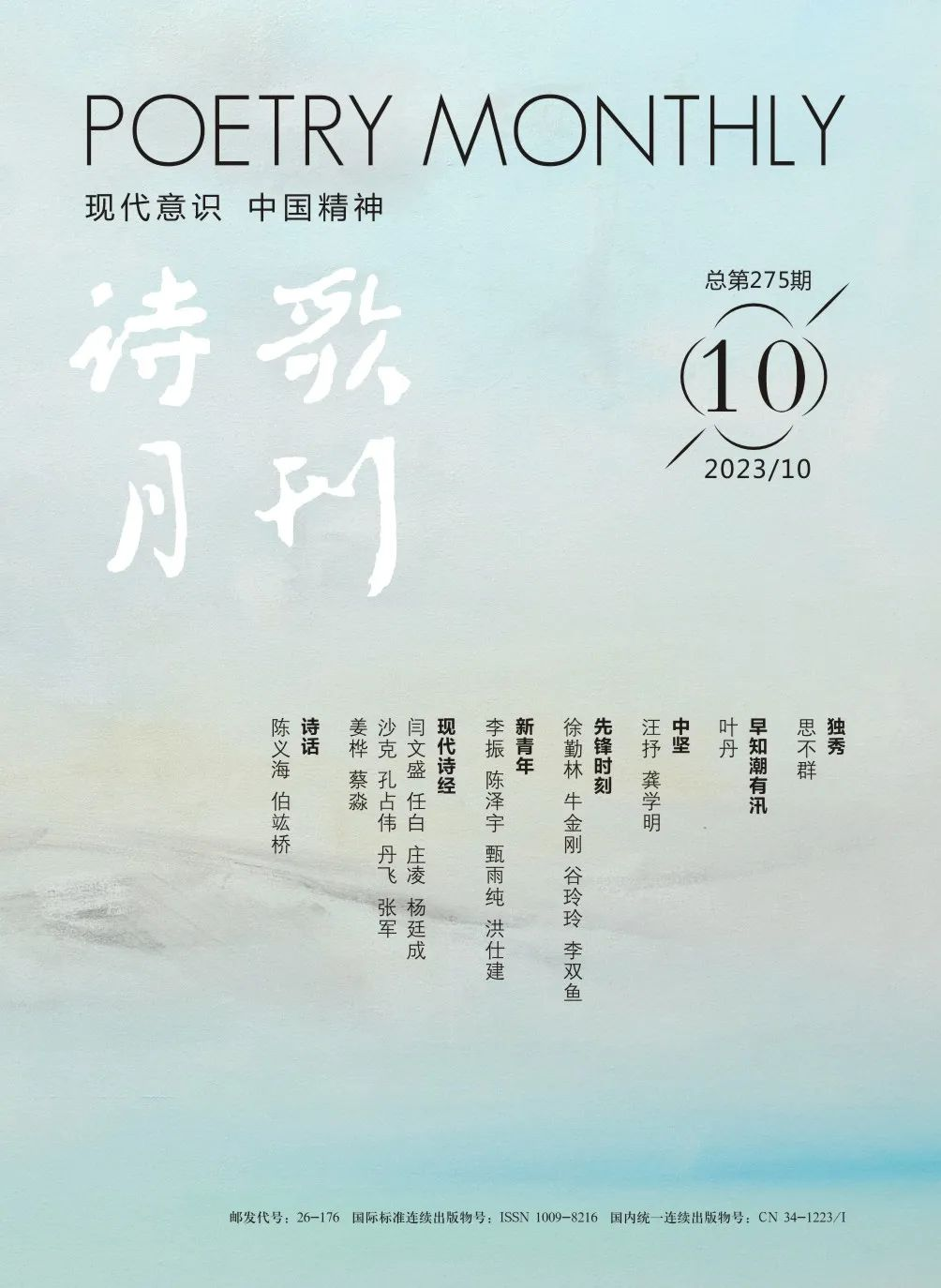
甘南之春
我在初春的翅膀上贴近时光的驿站,空气里带着清寒和料峭的风。
一切的风景都沾满了泥土的清新和残冰的破痕。
我俯视甘南大地,春的消息在沉寂的夜色里粗犷的穿行,把黄河和白龙江的肤色涂满银子的光泽,森林和群山竖成伟岸,众兽的目光瞭望远处洮水在春梦中复活影踪。
有生灵在呢喃的春风中吹醒黎明,可爱的春,娇小的身躯在高原隆起的胸口打着一声声口哨,撩拨着谁的一片伤情?
严冬的衣衫已被春的玉指揭开,裸露出新生命的肌肤,那是众生今年的寄予吗? 我在这空旷只剩骨头的缝隙里,瞅着不老的江河和花儿的芬芳迸出大地的硬壳,一路奔腾而去。
触摸那片初春的衣衫,我和春天的内心只隔着一缕阳光的距离。
今夜我伫立在祖国的西部,厮守冷雪在一片片大野中逐渐消融,想象那首曲和桑曲河水涌动的咆哮,会在初春的挽歌里喷薄而出?
一群灵魂就这样被草原的残雪沉寂着,与牧帐前深浅不一的脚印对望。
我的眼眸堆满甘南春的身影,哪朵云会放弃与冬日的对话,把塬上的暖风在雪域空旷的深处痴情地捧出?
聆听时远时近的牛角琴声,我的内心被嘹亮覆盖,黑夜失去了宁静。
天空依然抖动迷人的花瓣,将我孤独的身影紧密的包裹。
去初春的时光里放牧灵魂,让内心对青山和绿水的渴念在风的缠绵中迅疾的燃烧。
独坐北方,执着于对一群飞鸟的怅望。
独坐草原,那清凉的遐思在春意朦胧中虔诚的表白。
遥望临春的甘南,残雪在解冻的风铃中化为春水。
雪域的恋歌,在水草的露尖上舞蹈、歌唱。
我面对袒露的春之私语,鸣动那狂放的心弦,在春的蝉羽上抒写爱的乐章。远望草原深处,我用一种久病初愈的目光,撩拨高原悸动的心跳。
绝妙的精灵呵,今夜你撩动一个游子的魂,用飓风的手掌托起月光一样的歌喉。
在辽阔的青藏腹地,一条古老的河流在昼夜倾诉……
斯柔古城
清晨,我把目光投向甘加央曲河上游的舍京曲与恰莫涅曲两条支流的交汇点。
趁着初春料峭的寒风,思绪提前抵达一个特殊部落的核心区。
抬头向东北望去,虽目测遥远,但达力加神山高大雄伟的气息已倾压过来,让我仰望的眼神喘不过气。
横亘在甘加斯柔古村落北面的斯柔古城,只剩下错落斑驳的古城遗址,如一块块发青的残骨散落在夏河腹地。
时光逆行,我打开《吐蕃志》和《安多政教史》,想搜寻对这座神秘古城堡的片言只语,苍茫尘埃中,时间的碎片还原之后,显现公元1009年(宋真宗祥符二年)斯柔古城的身影,一个与吐蕃唃厮啰政权命运紧紧相连的军事要冲和象征权利的城堡,在星火燎原中敞开千年印痕,在甘青川辽阔的疆域抒写着一部青藏东部吐蕃政权的壮美凄凉的历史篇章。
回首一瞬,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某个夏天,戴着厚镜片的个头瘦小、性格倔强的李振翼,带着考古团队一脚踏进斯柔的领地,面对东南长约200多米的奇异城垣,师从学者赵俪生的天水人李振翼震撼了,他和团队惊愕于青藏瞬间的视角碰撞。
那些鲜明而特殊的筑城法和呈现的大量陶器、砖瓦、堞口、器具、饰品,浮现土著文化独有的印记。
翻看《甘加斯柔城勘测记》,我依稀看见甘南考古发掘的奠基人,挺着清矍而执着的背影,李振翼睿智的眸光和敏锐的洞察力,揭开了秘境甘加最神秘的历史底蕴,从此八角城旁边的古城遗址被赋予更巨大而旷远的命题,吐蕃赞普后裔唃厮啰的迁徙轨迹赫然在目。
今年夏天,我与那零散的古城遗址不期而遇,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寂浸透我的周身,遥想唃厮啰年少创业,雄心不泯,这斯柔古城便是他开创青唐伟业的一个历史基点,一种古朴神秘的力量牵引着探寻者永不停息的脚步一路向西。
当周山
清晨时分,我从羚城出发,沿囯道213线快速步行,三十分钟后进入当周景区,初夏的草原草色青青,远处云雾上升,隐约能看见当周神山的轮廓。
能聆听到野鸡、马鸡和云雀的鸣叫,声音是从青铜般的松林里发出的,要想寻声见影绝非易事。漫步入当周林卡边的栈道,云海飘弋中那帐篷城和财神殿似仙界琼楼,如梦如幻。
虽有些疲惫,但当周山巅栈道盘环而上,似龙腾虎跃,云层里透出金色,映射出万道霞光,瞬间震撼登山攀峰的人。
紧跟一群青年人的脚步,我开始觉察到自己的力不从心。爬上一个小山梁,回望远方,羚城已湮没在苍烟弥漫中,近处山脊上经幡猎猎,当周沟已成另一番光景,俨然海市蜃楼,只能谛听到百鸟合唱,牛羊低吟,晨露挂满草丛和树叶,在等待阳光顷刻间的抚慰。
离山顶近在咫尺,双腿已经僵硬,迈不开脚步,而山风浩荡,将我单薄的轻衫吹成咕咕作响的风筝。此刻,云海被晨光疾速划开口子,一张红彤彤的脸跳跃而出,极速攀上云雾缭绕,在众生仰望的高处收拢脚步,把光明之源洒向每一块尘埃和河流。
百年藏寨
发现是在一条迷茫的云雾中行进,一切被朦胧覆盖了。
车子在冰冷的隆冬直插车巴沟的心坎上。
没有人吱声,更没有人大口的呼吸,难道大伙儿窒息了吗?
眼前浮现的云雾阻挡了前行的车道,打开窗户,一股凌冽的风穿胸而过,瞬间僵硬了所有人的嘴巴和脑袋,只有一双惊愕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
些许时,云雾被亮光推散,两边山林里唱歌的野鸡和不知名、也不怕人的头冠发红的灵鸟拼命欢叫,似在警告前方的同类,有人类冒失的侵入了它们的领地。
晨曦来临时,远远地听到贡巴寺悠长的钟声响彻车巴河两岸,邂逅百年藏寨的时刻快要到了。
车子继续跳跃着身子爬行,清晰的听到了云雀的翠鸣和牛羊的哞咩声由远及近,先前沉默的一群人倏忽间唠叨起来,象扎堆的鹰隼,疯狂暗示着个人的存在。
云雾没有彻底消失,阳光没有露脸,寒流阵阵,一个大弯转过后眼前一下开阔,视野里车巴河的两岸都是藏寨,但泾渭分明,左边是美如仙地,右边如古拙沧桑的百年版画,坚硬地镶嵌在车巴沟尼巴一块台地的褶皱里,在晨雾里透视出一丝丝神秘的气息。
那就是一片百年历史的见证,外不见木,内不见土的尼巴古老村落连绵数里,不亢不卑的存在着,那些考古专家们迅速的穿梭其间,也不问是否能语言交流,一个个踪影全无,消失在百年藏寨的历史中。
仰望天穹,黒云合拢而来,倾刻间风云突变,狂雪飞舞,那藏寨象一条铁青色的硬汉,在这深冬的车巴沟伫立着,一切沉寂如初,好像没有打扰过。
偶有三五成群的老阿妈携着小孩经过,藏袍裹得严实,只有一双双饱经沧桑而深遂的眼睛一直盯着你,裸露出慈祥和善意。
那些保持百年不变的藏寨,就是车巴河沿岸藏人迁從历史的活化石,一个饱尝岁月磨砺的见证物。
光盖山
记忆中不止一次穿越光盖山麓,沿着它的脊梁踯躅而行。无论季节如何变化,从不畏惧大山的崎岖与凶险。
站在尼巴与江乾两村的中间,一条并不开阔的道路直插光盖山脚下,显得有些惊悚和不安!认识一座山是从脚下的路开始的。也许有人会问,爬那样一座高耸入云的山有啥意义?穿过光盖山还有多少危险悬机?
带着疑问和困惑,我的目光更加坚如磐石,一种强烈的探求和征服的欲望油然而生,车子盘旋而上,在云层中来回穿梭爬行,俯视山林满目柏树伫立如排箫,齐刷刷如将士出阵,在松涛狂啸中站稳脚跟,伺机而动。
在海抜三千三百多米以上,我谛听涅甘达洼神灵的呼唤,踩踏着山石堆砌的山路,横观左右山脊,奇石密布,层恋叠嶂,放眼远望,不远的高处玛尼石一堆堆赫然隆起,飓风再次发出狂啸,鼓胀的经幡冲天飞动,成片的经卷被风的喉咙诵读,震撼心灵的同时想冲动的面对喀斯特地貌的神斧神工的造化狂放呐喊!
铺展在眼前的便是世界罕见的第四世纪冰川遗址,天神将这一神迹抛落尘世,望人类惊奇的目光与这石镜山灰白色的奇峰交相辉映的巨大沟壑相遇,伫立山巅远眺,形态各异的百里石峰在厚积雪云的烘托中顿生浩渺烟波,银色峰峦与皑皑白雪衬映中熠熠生辉,恢宏壮观,仰望遥远的主峰九天门,犹如巨龙张开大嘴,吞吐着皓月与夕晖。
与扎尕那牵手而动的光盖山,在夜岚吹动中,伸出神秘的巨掌,接纳银河星落,晨昏交替。

牧风, 藏族,原名赵凌宏,藏名东主次力,甘肃临潭人。现任甘肃省甘南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州文联党组书记、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已在国内外各大报刊杂志发表散文诗、新诗、散文近五十多万字。作品入选全国多种散文诗及新诗权威选本和年选。著有散文诗集《记忆深处的甘南》《六个人的青藏》《青藏旧时光》、诗集《竖起时光的耳朵》。曾获甘肃省第六届黄河文学奖、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首届玉龙艺术奖,鲁迅文学院第22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创研培训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