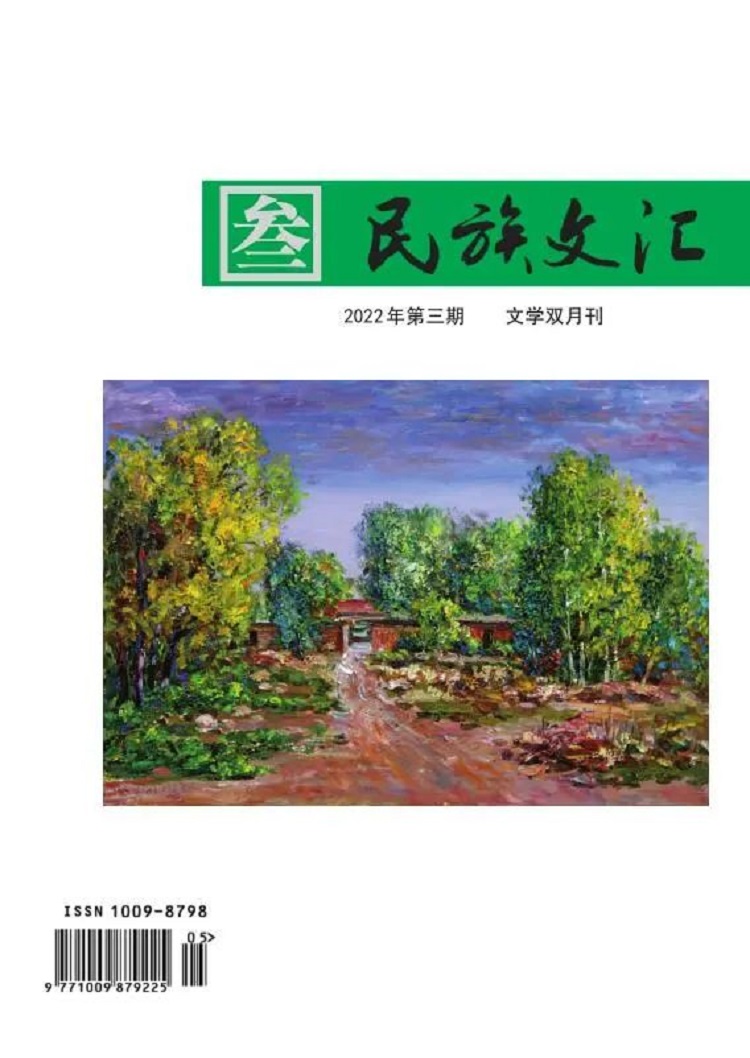
化石
巨大的骨骼和足痕,深埋于地底
该是经历了多么大的窒息,才能形成
亿万年后的扭曲。河南兽巨大的头骨上
尚有嶙峋的犄角,宣誓最后的张扬
突然想起那年漫游玉树大地
于高原一隅,得遇飞鸟巨大的趾甲
这些遗落的一鳞半爪,已不足以让我们坚信
麒麟,大鹏,飞龙和北冥之鱼
都曾是多么真实的存在
蛰伏人间太久了啊!利齿和想象
早已被温润的日子慢慢磨平
相较于眼前这些巨大的坚硬的肌体
我更愿意听到,那些无法封存的嘶吼
正从远古,遥遥而至
自白
立于林下,不再等待
那片薄雪从松针上缓缓滑落
行走在阴晴不定的春天
依旧喜欢,立于山冈之上
仔细端详那些寒酸的过往
一滴露珠打开整个世界
闭目而思,就能解开所有的羁绊吗?
我的父亲,您离开以后
苍老于我就有了真实的意义
遗忘
曾在一本厚厚的地方志里
找到过先祖一闪而过的名字
那幢百年老木屋拆除很多年了
承包到户的二十六亩山地
全部都已退耕还林
父亲辞世两年后的那个黄昏
沉寂七百多天的号码突然来电
——甥儿已经变声的话语里
能够听到甘南急促的风声:
“舅舅,我到县城读初中了,
现在用着爷爷留下的手机。”
默默改掉手机通讯录时
我知道,那个熟悉的称谓
就彻底成了过去
晨间
三月正以温暖的名义聚集
所有的花都在准备绽放
一扇封闭的窗爬满流萤
我两手空空,无法拯救
任何一个生命
惯走夜路的人在黑暗里寻找光明
斑驳干秃的笔终于不下墨了——
这些年,每个字都写得过于用力
凌乱的笔迹洇湿迟迈的人生
在北方,春华和秋月如此短暂
夏天和冬季却如此冗长
这些,多像我们的一生
足以让岁月露出疲容
温润如玉的婴孩降临人世
一枚叶片,在烛光里
展开精致的面容
整个世界都柔软了下来
春分
屋旁的无花果又开始抽出新芽
临江而居的耄耋老人走完了倔强的一生
他的儿孙们散落各地
在几种语言里转换着归去和远航
壬寅年春分,燕子尚未返回北国
碧桃、连翘、迎春和香荚蒾次第开放
如果能够绕过那些荒芜之所
黄河两岸,确实已经春风浩荡
昼夜等分,四野已经可以下种
那只鹰隼掠过辽远的天际
一双轻柔之手,抚平
不期而遇的灾难和悲怆
村庄
给每一座山都赋予伟岸的传说
给每一片海子,留下温婉的故事
冰雪凄迷的青藏大地,酥油花
就在零度以下盛开
卓尼普,农耕渐远的村庄
被一屡屡炊烟轻轻唤醒
岁月幽暗之处,万物众生
和我们一起走向光明
路过的人都是我们的亲人
途经的地方
一条又一条河流开始解冻
舟曲
沿途的柿子和石榴逐渐红了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居斯,居斯,高处的村庄
被一场古老的仪式庄重地唤醒
四野的庄稼都已颗粒归仓
大地再次裸露收割后的疲惫
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是很远
等在垭口的兄弟却已年逾不惑
一盏灯可以点亮暗夜
却无法开启内心的无明
老屋里再次挤满熟悉的面容
——在这个孤独的人世
我们尚能如此齐整地
吟唱那些吉祥的颂辞
冬日
健硕的骒马打着响鼻嘚嘚而来
衣着鲜亮的俊美少年
在平整的冰面上走得愈发忐忑
大路尽头,一身锈毛的老犏牛缓缓而至
负重的木车偶尔也会碾碎几片薄冰
群山很快就复归寂静了。静得只能听到
丁丁的伐木声从另一个时空遥遥传来
天地很快复归寂静。静得只能听到
尚未出窝的雏鹰又舒展一次翅翼
我们的内心很快也复归寂静
这个时候,就能听闻
一片雪花压低整个世界的声音
丰收
密密匝匝的蛛网结在门楼一角
远处归来的我,仿佛一个不速之客
惊扰了这个盘踞已久的主人
老木屋空空如也。那棵杏树
还像过去一样挂满了纠结
擦亮镜子,就能看到祖辈的面容
沿一条小路上山,露水丰盈
葳蕤的草木深陷在晨光里
懒懒散散的炊烟正在唤醒村庄
四野的庄稼又到了收割的季节
弯月般的镰刀插在架子上
那个豁口如此刺目
原刊于《民族文汇》2022年第三期

刚杰·索木东(1974—),藏族,又名来鑫华。甘肃卓尼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各类文学期刊,收入数十选本,译成多种文字。著有诗集《故乡是甘南》。现供职于西北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