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洮州深处的乡村牧歌
——访作家敏奇才
马桂珍
东界狄道,南依松叠,西靠黄河,北临枹罕,有一方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叫洮州。洮州,今临潭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位于甘肃省南部,甘南州东部,曾为“唐蕃古道”四大“茶马互市”之一,这里历史悠久,红色文化、历史文化底蕴厚重,自然景观秀丽,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独具魅力,先后被评为“全国拔河之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中国文学之乡”。洮州独特的地理历史、人文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一批极具特质的优秀作家,敏奇才是其中之一。扎实的写作态度,持重的步伐,质朴的性情使敏奇才在文学创作上具备了一种“洮州特质”,无论小说、散文还是剧本,他的创作视野不仅丰富多彩,还保留了一份古朴、多元、纯净的原生态气质。
从散文集《从农村的冬天走到冬天》《高原时间》到小说集《墓畔的嘎啦鸡》他以特有的地域体验和生命关怀为洮州大地书写着乡村牧歌式的篇章。他将高原诸多历史、人文、自然、风物、民俗汇聚笔端,将干净纯粹的故土情结融入文字里,将灵魂的颤动和生命的触痛感注入书写的过程中,使这片土地上广阔厚重的人文地理空间,生态文明,精神高度和心理情感得以凸显,呈现出具有包容性和原生态气质的文化品格。
地域对作家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对故乡的抒写,一直以来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敏奇才创作的主题之一。在辽阔的精神背景和人文视野之下,敏奇才将笔触深入到故乡洮州的内里,从历史记忆、家国情怀、民族担当到洮州大地的自然生态、民俗风情都做了细致深度的描写。在《三石一顶锅》中他开门见山便写道“生活在洮州大地上的人们,一生下来就像那随处可见的顽石一样,和草原、土地融在了一起,不曾分离......洮州有新旧两城,是草原深处江淮人家的团结之城、友爱之城、和谐之城,是三石支撑的稳固之城。那么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之民众,就是稳固之城的团结之民众,友爱之民众,和谐之民众。”真诚的笔触写出了一座有生命质感、精神内核和灵魂温度的高原小城。他在高原的初冬,顶着蓝汪汪白亮亮的天穹,迎着温烈的风尘,访古寻今,为洮州而歌“可曾有谁想到在这青藏高原的屋檐下,生活着一群江淮后裔,六百多年的风火岁月让他们变成了一群顶天立地时刻想念故土的青藏硬汉。正是这风火岁月的洗礼,造就了洮州人不同寻常的血脉......洮州人是活在久远而新鲜的历史故事里。但说白了,洮州人的历史是一部活着的移民守边史和奋斗史。”(《洮州,洮州》)他写洮州人,男人粗犷能干,内心和善,为人仗义,富有拼搏精神,女人活泼淳朴,风姿卓越“在日暮的傍晚,女人扛了锄头,领着顽童,牵了牛儿赶了羊儿,踩着山道的余热和青草的柔软,披了一身霞光,带了一身田野的馨香回来了,依然是云髻峨峨,高帽围纱,款款而至,在深切的思念中走出了一种神韵,一种姿态......”(《洮州人》)而“思谋、挖抓、诧人、土尘尘、吃不透、踢踏......庄稼都快瘦成驴身上的锈毛了。地不犁不酥,人不走不亲。”等洮州方言俗语的熟稔大胆而恰到好处地运用,使字里行间飘逸着一股浓浓的“洮州韵味”。敏奇才说,在故乡洮州这片土地上,他从小受到了地域性文化、传统江淮文化、移民文化、多元民族文化的深远影响和熏陶,这些珍贵的矿藏使他的创作浸润着古老的文化精神又凸显着一股独特浓厚的地域色彩。

敏奇才是从洮州腹地敏家咀走出来的作家,对乡村聚居生态极为熟悉,在他的散文集《高原时间》里可以清晰的触摸到“敏家咀”是一处灵魂的栖息地,它是原始的、质朴的、温情的、忧伤的、让人眷恋的。《高原时间》是2020年1月出版的散文选集,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由表及里的叙写了乡亲、亲情、友情与爱情的深刻体验,将对生活的领悟和人生的思考融入乡村如诗如画的意境中,如乡村牧歌、田园散曲。下部着重点在家乡的山水景致和牲灵野物,在他笔下,村落里的一草一木、一头牛、一只羊、一只喜鹊、一只掠飞的麻雀、一只微小的虫子乃至乡村里扶摇直上的炊烟,他都赋予它们鲜活的灵性,充满了悲悯之情,敬畏之心。他既关注时代变迁又关心着这片土地上小人物的悲喜,在对脚下的土地充满深切眷恋的同时又对日渐消逝的农耕文明充满了忧患意识。他在对乡情的抒怀中表达着一种对渐行渐远的风俗民情的呼唤,他通过乡村的风物倾诉着内心的热爱和眷恋。他写一只留守在村子里的喜鹊,读来却更像是一个人、一群人抑或是人心深处对故乡的守护之情“那只喜鹊在村子里相安无事但也很孤寂地生活了那么几年,用叫声唤醒了那些快要泯灭记忆的人们。终于有一天,他叫不动了。一日午后,它站在老敏家的院墙上瞌睡了似的头歪在以边沉沉地睡去了......”他写收割的麦子、满街游荡的老雌牛、赋予村庄灵气的麻雀和村庄里的月亮,带着自然质朴的气息和让人陶醉的温度,又有一点点怅惘、忧虑甚至痛感,让人在一种宁静的温情中看到一座村子淳朴自然的真实模样“割完麦子,我躺在院子里的长凳上歇缓身子骨。母亲则把那不能捆束子的麦穗拾来晒在院子里。在太阳底下我看到那些麦粒兴奋地跳跃着脱离穗壳,吐露着蕴藏的香气,弥漫在了家里的旮旮旯旯,又升腾飘逸开去,罩住了整个村子。成了老村精气的一部分。”(《守护村庄的东西》)。敏奇才说“我生养在农村,在农村长大,陪着青山绿水,牵着耷角牛赶着绵羊度过了我的童年。时至今日,我还时常梦见儿时的乡村和那些陪伴过我的山场、河流、玩伴和牛羊。而且我也自始至终认为敏家咀就是我的文学地域版图,这块土地上的人事物景常常让我写得手酸,离了这块土地我就成了无源之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虽说都是一个文学概念,但他们都是以此走向了世界文坛。我虽然没有那么大的理想,也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但是我以敏家咀作为我灵魂和写作的高地,是写不完写不尽的,因此,就把写作当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当我写作枯竭的时候,会回到敏家咀小住几天,写作的灵感就会喷薄而出。”
敏奇才是一个安静的、质朴的、有情怀、有温度、有坚定信念和创作目标的作家,纵观他的作品,没有太多华丽炫目的辞藻,没有深奥繁冗的哲理,也没有刻意去追求艺术技巧,却有一股静水深流照亮人心的力量,这大概与敏奇才的创作心态有关。他说,首先一个作家心中要有大爱,这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怀。有了这种情怀作家就会拉近与自然生态的距离,展开深邃的思考,重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让哪怕是一只鸟、一条狗、一只羊、一只野生、一头牛,一块石头,都承载和记录不同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成长影像。从而尽量追求与人类友爱,与生灵为善,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境界。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墓畔的嘎啦鸡》散文《进村的野生》《孤狼》《狼王》都能感知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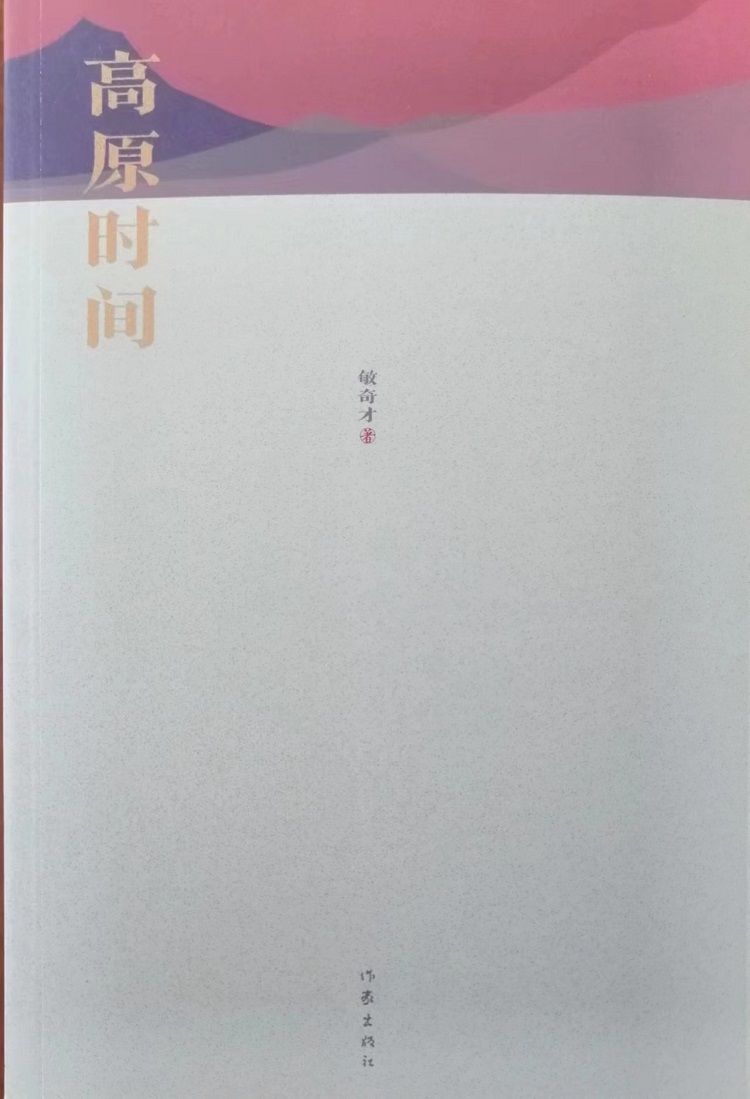
谈到他的文学创作之路,敏奇才说自己与文学结缘,可以追溯到1993年至1995年上大学期间。“那时,遇到了两位对我影响非常大的老师,一位是主讲古诗词的买鸿德老师,一位是讲写作学的朱广贤老师。买鸿德老师能把一首《春江花月夜》讲一个星期,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讲起来滔滔不绝,让我一个星期陶醉在那无限美好的景象中不能自拔。而朱广贤老师的散文或小说课则把我引入到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描述和感悟中,而更多的是无限美妙的细节描写当中。这个时候,我就压不住胸中饱满的激情,想对我熟悉的敏家咀这片土地和父老乡亲有所倾诉,于是写起了小说和散文。1997年,第一篇短篇小说《墓畔的嘎拉鸡》发在《飞天》头条,接着又发了《猎手》和散文《二爷》等,从此对自己的写作有了更大的自信心,一直坚持了下来。就这样,一路走来,断断续续地写了二十多年。”天道酬勤,二十多年的坚持和努力使敏奇才在创作上收获颇丰,他的作品频频发表于《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天涯》《延河》等国内重点期刊;2000年他获甘肃省第三届黄河文学奖;2007年获第五届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奖;2000年获全国“五彩梦﹒同心圆”民族团结进步征文一等奖;1999年获第五届新月文学奖一等奖等奖项。散文、小说入选多种权威选本。2021年加入了中国作协。谈起他自己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时,敏奇才谦虚地说“虽然我结集出版了散文集《从农村的冬天走到冬天》《高原时间》和中短篇小说集《墓畔的嘎拉鸡》。但至今还没有哪部作品是自己最满意的,也许最满意的作品今后会奉献给读者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甘南作家,我的创作源泉来自对故乡洮州的挚爱和眷恋,多年来,是故乡的历史人文,风物景致滋养着我,召唤着我,激励着我。在写作上,我认为无论小说、散文和剧本是互通的,对我来说,体裁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到文字里,只要你倾注了情感,带着丰富的情感去写,一定会成功的。”敏奇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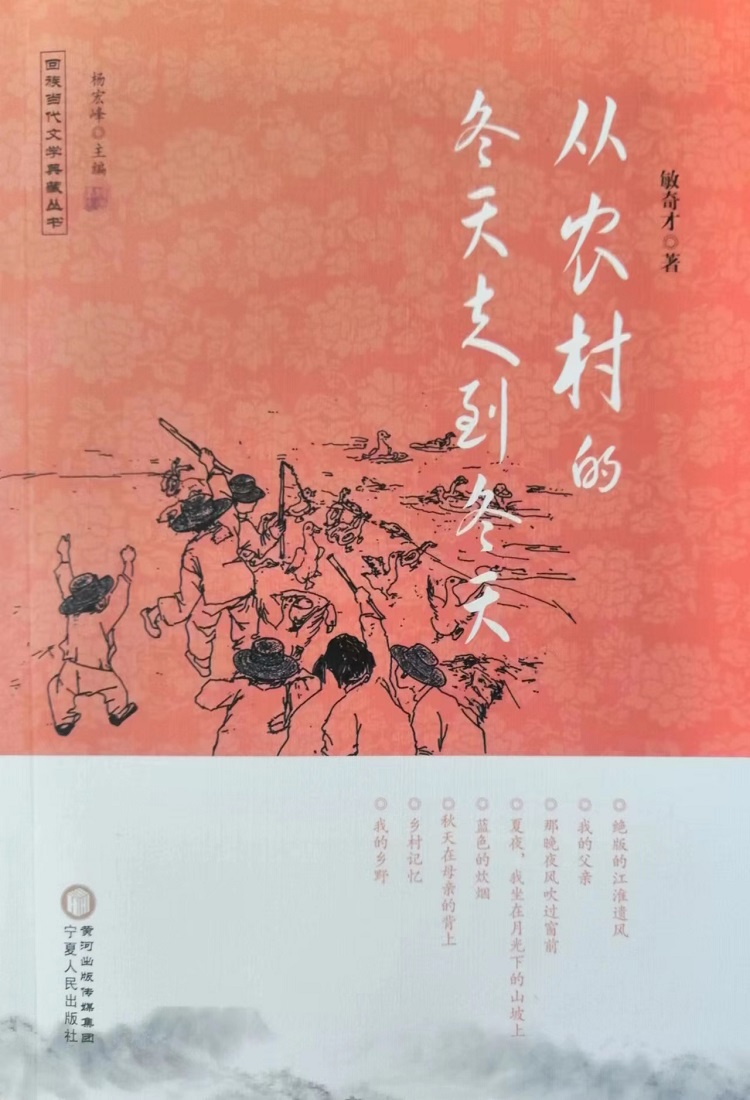
【佳作选读】敏奇才:洮州,洮州(节选)
站在城墙上,在瑟瑟的微风中,踩着斑驳润滑的泥雪,望着一马平川的城外,旷野里的雪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的耀眼眩目。几只野鸡在雪地里甩着长尾巴旋来飞去,寻找着覆盖在雪被下的吃食。冬日的远村少了历史的风烟,只是潦草、斑驳、孤寂、无序的存在着,有气无力地飘荡着缕缕炊烟,有了几分生机,更像守卫卫城的士兵,有着几分坚硬和刚气。城内零零落落的高大白杨树,在高楼大厦的掩映中显得干瘦、老荒、寥落,直直地展示它们的年轮和经历过的那些风与火的岁月。大街上拉土的牛车缓慢走过,叮叮当当的古老牛铃声响彻穿梭在无人的空巷,空灵清幽、悦耳动听,多了一份历史的沧桑。只是有点担忧,这古老空灵的牛铃声在洮州大地上还能存在着响彻多久呢。
一声粗壮而悠扬的洮州花儿扯着长调徐徐飘进了耳朵,这是久违了的山野的声音,花草的声音。在十几年前的洮州大地上,男男女女出来都会哼唱几句花儿的,就是不会唱花儿的也都会说几句,用花儿来表达难以诉说的难肠。可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已经不会唱花儿了,流行歌替代了花儿的对唱。在这温烈的冬季里,能听到花儿,实属不易。大冬天的在山野里扯开嗓子唱花儿的人那一定是一个孤寂、无助、落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在那无人的旷野里扯开嗓子吼几声,排解心中的郁闷和不快,也多多少少带点古老的味道。
让我们还是走进洮州的江淮人家吧。一路走来,一个个的村子,不一样的布局,一进一出一芡套的平房,掩映在房前屋后的白杨树、柳树、李子树和杏树中间,便有了江南水乡的味道,要是门前再有一条小河在春季里缓缓流淌起来,那定是另外一番景象。屋前一般是空旷的打碾场,在白天空闲时,便有一群年轻的回族或是汉族媳妇们围坐在碾石上,或是自带的小木凳上,带着江淮吴语的浓浓韵味,互相诉说一些家常和往事,或是争先恐后地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时至晌午,有一小儿从大门的偏门洞里蹦出来,喊道;“娘!阿婆让你喊上婶子们,叫吃晌午来呢。晌午阿婆做好了,是拿手的铁锅粑,端放到堂屋炕桌上呢。”孩子的娘招呼众人去吃,竟无一人去吃,便推辞着哗地散了,扭着婀娜的腰肢,迈开急促的步子轻快地走了。她们走开时,汉族媳妇们头上的银泡和鬓花在阳光下熠熠闪亮,把原本就水灵漂亮、婀娜多姿的人衬托得像仙女下凡似的;回族媳妇们头上的纱巾倒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只是缺了一些江淮的水色而已。她们的衣摆刚好齐膝,端庄大方,不拖泥带水,这和江淮无异。只是在这青藏屋檐之下,缺了一分水色,一分温润,不然和江淮真有一比。600多年的洮州生活,江淮移民后裔们娇嫩的面容变了,变成了青藏高原的红褐色。带着江淮吴语的浓浓韵味的语言也在流传中和当地人的语言互相交融,互相借用,形成了独特的洮州方言。你带着洮州方言,到了江淮一带的乡村,不用绕舌,更不用鹦鹉学舌,也能和那里的江淮人心情愉快地交流一番。心与心交流着,此刻便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拉近了洮州和江淮的距离。然而600多年来对想象中江淮水乡老家那种蚀骨的思念,使得他们竭力地保持着先人的一些服饰习惯,没有和当地人形成融合,顽强保留了江淮人的痕迹,留住了一些念想和记忆。回到十几年前,走在洮州任何一地的大街上,洮州的汉族妇女,服饰打扮极具特色,和江南女子的打扮毫无二致。未出阁的女孩子纤秀温婉,身着浅蓝色齐膝长衫,散腿裤子,足穿绣花鞋,梳独辫或者双辫。而称之为尕娘娘的那些出嫁了的媳妇们则面容娇艳,含羞顾盼,明眸善睐,头梳大髻,戴银饰镂花压鬓,发髻插满银泡,耳戴叮当作响的银饰坠子,发插流苏步摇。头顶双折对角花头巾,穿浅蓝色齐膝长衫,下穿撒花裤子并绑裤脚缠腿带,脚蹬鸳鸯戏水或是花色艳丽的绣花鞋。若逢赶集或庙会进城,身背精致小背篼,臂挽一精致竹笼。走起路来一步三摇,婀娜多姿,款款而至,像走在江淮的某一小镇或大街上,再要是有那温润的小桥流水陪衬着,一抹蓝天下的洮州确也不亚于江淮。平面红石铺就的古巷里,几位少女穿着鲜艳的衣裙飘然而至,说说笑笑,那浓浓的江淮吴语让来人仿佛置身于江南某地,又恍若古典诗词中的江南意象,让人留恋激动不已,遐思向往不已。
金陵的血脉生生的印在了这些后裔们的血液和语言里,也印在了这些后裔们的故事里。走在偏远的山村里,随便拉住一个人一问,你的祖上是哪里人,他会自豪地告诉你,我的祖上是金陵人。只要打开了话头,他会滔滔不绝地给你讲下去,讲出一个个洮州人的故事来,不仅是明仁宗贵妃麻娘娘的故事,而是要讲上三天三夜让你听不完也听不烦的故事来。要是那个作家到了洮州,听完了洮州人的故事,他一定会在洮州的那个乡庄里住上几月甚至几年,把那美丽动人的故事一个个地写出来。其实,洮州人是活在久远而新鲜的历史故事里。但说白了,洮州人的历史是一部活着的移民守边史和奋斗史。
……
原刊于《甘南日报》2022年6月1日三版

敏奇才,男,回族,1973年生于甘肃省临潭县,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天涯》《南方文学》《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剧本,其中散文、小说入选多种选本。曾获甘肃省第三届黄河文学奖,第五届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奖,第五届新月文学奖,全国“五彩梦﹒同心圆”民族团结进步征文一等奖。出版散文集《从农村的冬天走到冬天》《高原时间》,小说集《墓畔的嘎拉鸡》。甘肃省临潭县文联专职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十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

马桂珍,女,回族,笔名法蒂玛•白羽, 1976年生,甘肃省夏河县人,现居甘南合作市。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散文选刊》《民族文学》《回族文学》《黄河文学》等刊物。获2019《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2018年第六届《格桑花》文学奖、2021年第六届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