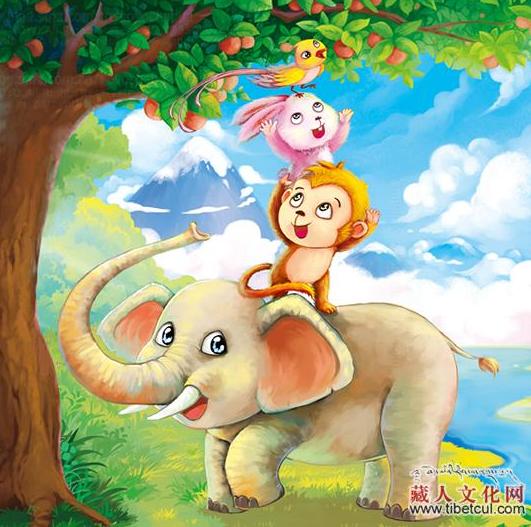ж‘ҳиҰҒпјҡеҜ№жӯҢжҳҜйҒҚеҸҠйӣӘеҹҹиҘҝи—ҸеҸҠе…¶е‘Ёиҫ№еҗ„ж°‘ж—Ҹең°еҢәзҡ„дёҖз§ҚдјҙйҡҸд»ӘејҸиҖҢеұ•ејҖзҡ„ж°‘й—ҙж–ҮеҢ–еЁұд№җжҙ»еҠЁгҖӮе®ғж—ўжҳҜдәәзұ»йЎәеә”еӨ©ж—¶гҖҒиҗҢеҸ‘жҳҘжғ…гҖҒзҘҲзӣјдё°ж”¶зҡ„д»ӘејҸйўӮиөһе’ҢзҫӨдҪ“еҖҫиҜүпјҢдҪ“зҺ°дәҶдәәдёҺиҮӘ然д№Ӣй—ҙзҡ„ж–ҮеҢ–е…іиҒ”пјҢеҸҲжҳҜи·ЁжҖ§еҲ«гҖҒи·Ёең°еҹҹгҖҒи·ЁзӨҫдјҡйӣҶеӣўзҡ„дәӨжөҒж–№ејҸе’ҢиҒ”姻жүӢж®өпјҢдҪ“зҺ°дәҶзӨҫдјҡзҫӨдҪ“д№Ӣй—ҙзҡ„иЎҖзјҳдёҺж–ҮеҢ–зҡ„иҒ”еҗҲгҖӮ
иҘҝи—Ҹзҡ„и—ҸгҖҒй—Ёе·ҙгҖҒзҸһе·ҙгҖҒеғңгҖҒеӨҸе°”е·ҙзӯүж°‘ж—Ҹжҷ®йҒҚжңүеҜ№жӯҢгҖҒиөӣжӯҢзҡ„д№ дҝ—гҖӮж—¶й—ҙйҖҡеёёе®үжҺ’еңЁдёҖдәӣйҮҚеӨ§иҒҡйӣҶжҖ§жҙ»еҠЁд№ӢеҗҺпјҢең°зӮ№дёҖиҲ¬еңЁйҮҺеӨ–иҫғе®Ҫйҳ”зҡ„ең°ж–№гҖӮиҘҝи—Ҹзҡ„и®ёеӨҡеӨ§еһӢе®—ж•ҷжҖ§жҙ»еҠЁйғҪдјҙжңүжӯҢиҲһжҙ»еҠЁпјҢиҝҷдәӣжӯҢиҲһжҙ»еҠЁеҚҒеҲҶзғӯй—№пјҢдёҖйҰ–и—Ҹж—Ҹж°‘жӯҢиҝҷж ·жҸҸиҝ°зқҖпјҡвҖңе№ҙиҪ»зҡ„жңӢеҸӢ们е”ұеҜ№жӯҢпјҸиҪ¬еңҲе„ҝе”ұеҜ№жӯҢеҝғжғ…жңҖж¬ўз•…вҖқгҖӮи—Ҹж—Ҹйқ’е№ҙеёёеёёйҖҡиҝҮе®—ж•ҷеәҶе…ёдёӯзҡ„жӯҢиҲһжҙ»еҠЁйҖүжӢ©жҒӢдәәпјҢиҝҷж ·зҡ„дҫӢеӯҗеұЎи§ҒдёҚйІңпјҡвҖңиҚүеҺҹдёҠжңүдёҖдёӘдјҡеңәпјҸйҖӣдјҡзҡ„дәәжңүеҚғеҚғдёҮдёҮ пјҸдәәзҫӨдёӯжңүеҝғзҲұзҡ„姑еЁҳ пјҸ姑еЁҳжЁЎж ·зҫҺдёҚзҫҺжҲ‘дёҚз®ЎпјҸеҸӘзҲұеҘ№еҝғиӮ еҘҪе“©вҖқпјӣвҖңжқҘеҲ°ж¬ўд№җиҲһеңәпјҸй”…еә„дёҚи·ідҪ•ж—¶и·іпјҸи§ҒеҲ°еҝғзҲұзҡ„дәәе„ҝпјҸжңүиҜқдёҚиҜҙдҪ•ж—¶иҜҙвҖқвҖңдҪ еҗ¬жӯҢеЈ°еӨҡзғӯй—№пјҸ йқ’е№ҙз”·еҘіеҚғеҚғдёҮдёҮ пјҸиҲһе§ҝеҘҪдјјеҪ©дә‘йЈҳпјҸиҰҒжүҫжғ…дәәиҺ«иғҶжҖҜ пјҸзҫҺиІҢеҘіеӯҗд»»дҪ жҢ‘вҖқгҖӮдёҺи—Ҹж—Ҹзӣёд»ҝпјҢе°јжіҠе°”дёҺдёӯеӣҪиҘҝи—ҸдёӨең°й—ҙзҡ„еӨҸе°”е·ҙдәәзҡ„ж–°е№ҙпјҢдј—дәәзҫӨиҒҡеҲ°дәӢе…Ҳз”ұжқ‘дёӯй•ҝиҫҲйў„е®ҡеҘҪзҡ„ең°зӮ№пјҢе№ҙиҪ»дәәеңЁжӯӨж¬ўжӯҢиө·иҲһпјҢзәөжғ…ж¬ўд№җпјҢйҖҡе®өиҫҫж—ҰпјҢ延з»өж•°ж—ҘгҖӮйӮ»иҝ‘иҘҝи—Ҹзҡ„еҚ°еәҰйҳҝиҗЁе§Ҷдәәзҡ„жҜ”еҝҪиҠӮдёҠжңүзқҖзұ»з–ҜзӢӮзҡ„жӯҢиҲһжҙ»еҠЁгҖӮе°јжіҠе°”зҡ„еҸӨйҡҶж—Ҹд»ҺжҜҸе№ҙдёҖжңҲзҡ„иҝҺжҳҘиҠӮпјҲShri pamchamiпјүејҖе§ӢзӣҙиҮіеӣӣжңҲпјҢдәә们йӣҶдјҡжӯҢиҲһпјҢиҲһиҖ…дё»иҰҒжҳҜе°‘еҘіпјҢдәӨз»“зҡ„жғ…дәәдјҡдёҖеҗҢеҮәе…ҘдәҺе®—ж•ҷеңЈең°гҖӮ
йӣӘеҹҹиҘҝи—ҸеҸҠе…¶е‘Ёиҫ№ж°‘ж—Ҹзҡ„жӯҢиҲһжҙ»еҠЁеёёеёёйӣҶдёӯеңЁжҳҘеӨ©йҮҚеӨ§зҡ„иҠӮж—Ҙжҙ»еҠЁдёӯжҳҜжңүж—¶д»ӨдёҠзҡ„еҺҹеӣ зҡ„гҖӮжҳҘеӨ©жҳҜеҶңдәәж’ӯз§Қ并зҘҲжұӮ丰收зҡ„еӯЈиҠӮпјҢд№ҹжҳҜзү§дәәиҪ¬жҚўиҚүеңә并зӣјжңӣз•ңзү§жҲҗеҠҹзҡ„еӯЈиҠӮгҖӮжҳҘеӨ©жҳҜз”ҹжҙ»ж ·ејҸиҪ¬жҚўеҸҳеҢ–зҡ„еӯЈиҠӮпјҢеҸҲжҳҜе……ж»ЎеёҢжңӣпјҢжӢ…еҝғзҒҫйҡҫзҡ„еӯЈиҠӮгҖӮйҮҚеӨ§зҘӯзҘҖйӣҶдёӯдәҺжҳҘеӨ©пјҢдҪ“зҺ°дәҶдәәеҜ№еӨ©ж—¶зҡ„йҖӮеә”дёҺеҜ№иҮӘ然зҡ„йҖүжӢ©гҖӮиҝӣе…Ҙйқ’жҳҘжңҹзҡ„з”·еҘійқ’е№ҙпјҢжёҙжңӣеңЁжҳҘеӨ©иҠӮж—ҘжҖ§жҙ»еҠЁзҡ„иҒҡдјҡдёӯпјҢеҜ»жүҫйӣҶдҪ“дәӨз»“гҖҒеҪјжӯӨзӣёиҜҶзӣёи§Ғзҡ„жңәдјҡгҖӮ他们йҰ–е…ҲжҲҗдәҶиҠӮж—ҘдёӯйҮҺеӨ–иҒҡдјҡжҙ»еҠЁзҡ„з§ҜжһҒеҲҶеӯҗгҖӮ他们зҡ„дәӨз»“жүӢж®өжҳҜеҜ№жӯҢпјҢе®ғеёёеёёеҸ‘з”ҹдәҺзӣёйӮ»иҖҢдә’дёҚзӣёиҜҶж°Ҹж—ҸгҖҒйғЁиҗҪжҲ–жқ‘еә„зҡ„йқ’е№ҙз”·еҘідёӯгҖӮ他们зӣјжңӣжҳҘеӨ©иҒҡйӣҶжҖ§жҙ»еҠЁзҡ„еҲ°жқҘпјҢе°ұжҳҜдёәдәҶжңҹеҫ…зәҰдјҡзҡ„дҪіжңҹпјҡвҖңзәөжңүеҚғйҮҢиҝўиҝўзҡ„йҳ»йҡ”пјҸд»ҚиғҪеңЁдҪӣж®ҝзҡ„дҫӣжЎҢдёҠзӣёдјҡпјҸжқңй№ғе•ҠпјҢжҲ‘们дёҚиғҪзӣёйҖўпјҸеӣ дёәиҝҳдёҚеҲ°еӣӣжңҲзҡ„еӯЈиҠӮвҖқгҖӮпјҲе®үеӨҡж°‘жӯҢпјүиҝҷйҮҢпјҢжҳҘж—ҘеҜ№жӯҢпјҲеҰӮвҖңеӣӣжңҲзҡ„еӯЈиҠӮвҖқпјүжҲҗдәҶжҒӢзҲұзҡ„еӘ’дҪ“гҖҒзәҰе©ҡзҡ„жүӢж®өгҖӮеҜ№жӯҢжҠҠдәәзҡ„еҝғжғ…дёҺжҳҘеӨ©зҡ„зҺҜеўғиҒ”зі»еңЁдёҖиө·пјҢиЎЁжҳҺдәәеҜ№иҮӘ然зҡ„йЎәеә”е’Ңд»ҝж•ҲгҖӮжӯЈеҰӮдёҖйҰ–и—Ҹж—Ҹж°‘жӯҢжүҖе”ұзҡ„пјҡ
гҖҖгҖҖиңңиңӮе’ҢйІңиҠұзӣёзҲұпјҢ
гҖҖгҖҖжҳҘйЈҺе°ұжҳҜеӘ’дәәпјӣ
гҖҖгҖҖйқ’е№ҙе’Ң姑еЁҳзӣёзҲұпјҢ
гҖҖгҖҖеұұжӯҢе°ұжҳҜеӘ’дәәгҖӮпјҲиҠҰз¬ӣиҜ‘пјү
жҳҘеӨ©зҡ„йҮҺеӨ–жңҖиғҪжҳҫзӨәжҳҘж„ҸгҖӮдёҮзү©еӨҚиӢҸпјҢе……ж»ЎдәҶз”ҹжңәе’ҢеёҢжңӣпјӣеҗҢж—¶йҮҺеӨ–еҸҲжҳҜжқҘиҮӘеҚұжңәпјҲеҰӮеұұжҙӘжҡҙеҸ‘пјҢжІіж°ҙжіӣж»Ҙпјүзҡ„ең°ж–№гҖӮиҝҷз§ҚеҜ№йҮҺеӨ–зҲұжғ§дәӨеҠ зҡ„еҝғзҗҶпјҢдҪҝжҳҘж—Ҙзҡ„е®—ж•ҷжҖ§жҙ»еҠЁеҫҖеҫҖе®үжҺ’еңЁйҮҺеӨ–иҝӣиЎҢгҖӮйҮҺеӨ–жҲҗдәҶжҳҘзҘӯйӣҶдјҡзҡ„еңЈең°пјҢдәә们йҖҡиҝҮеңЁжӯӨзҘӯзҘҖжқҘж”Ҝй…ҚиҮӘ然пјҢд»ҺиҖҢдҝқиҜҒдёҖе№ҙеҶ…еңҹи‘—йӣҶеӣўзҡ„йЎәеҲ©з”ҹеӯҳдёҺ延з»ӯгҖӮжӢүиҗЁи—ҸеҺҶжӯЈжңҲй—ҙзҡ„дј еӨ§жҳӯе’ҢеҚҒдә”дҫӣзҒҜд»ҘеҸҠдәҢжңҲеә•зҡ„иөӣе®қз»•иЎҢгҖҒеұұеҚ—дёҖжңҲдёҠж—¬зҡ„жҺӘзҸ иҫҫз“ҰгҖҒеҗ„ең°дә”жңҲдј жҳӯжұӮйӣЁе’ҢйғҠе®ҙзҘӯзғҹпјҢй—Ёе·ҙж—Ҹи—ҸеҺҶж–°е№ҙпјҲй—Ёе·ҙиҜӯвҖңжҙӣиҗЁвҖқй—ҙеңЁе®Ҫж•һең°ж–№зҡ„жӯҢиҲһпјҢиҘҝи—ҸеўЁи„ұзҸһе·ҙж—ҸзұіеҸӨе·ҙйғЁиҗҪдәҢжңҲзҘӯзҘҖеңҹең°д№ҢдҪ‘д»ӘејҸеҗҺзҡ„жӯҢиҲһпјҢиҝҷдәӣжҳҘеӨ©иҝӣиЎҢзҡ„зҫӨдҪ“жҖ§жҙ»еҠЁпјҢйғҪжҳҜеңЁе…¬е…ұеңәжүҖпјҲзү№еҲ«жҳҜеңЁйҮҺеӨ–пјүдёӯдјҙйҡҸзқҖзҘӯзҘҖд»ӘејҸеұ•ејҖзҡ„гҖӮеңЁиҜёеҰӮжӯӨзұ»зҡ„жҳҘзҘӯжҙ»еҠЁдёӯпјҢзҘӯзҘҖд»ӘејҸе’ҢеЁұд№җеҜ№жӯҢеҗҢж—¶жҲ–е…ҲеҗҺеұ•ејҖгҖӮз”ұдәҺиҝҷз§ҚйҮҺеӨ–зҡ„жҳҘзҘӯйӣҶдјҡеҜ„жүҳдәҶдёӢеұӮж°‘дј—жұӮзҘҲдёҖе№ҙ收иҺ·зҡ„жңҖй«ҳзҗҶжғіпјҢеӣ жӯӨпјҢе№ҙиҪ»дәәйҖүжӢ©еңЁиҝҷз§ҚеңәеҗҲиөӣжӯҢпјҢзңҹжӯЈдҪ“зҺ°дәҶдәәдёҺиҮӘ然зҡ„е…іиҒ”пјҢжӨҚзү©зҡ„з”ҹй•ҝдёҺжҳҘжғ…зҡ„иҗҢеҠЁпјҢйёҹе…Ҫзҡ„зӣёй…ҚдёҺдәәзҡ„жғ…ж¬Ізҡ„з„•еҸ‘гҖӮеҠЁжӨҚзү©еңЁжҳҘеӨ©жҳҫзӨәдәҶж—әзӣӣзҡ„з”ҹе‘ҪеҠӣпјҢдёҺдәәеңЁжҳҘеӨ©еҜ»жүҫзҲұжғ…дёҖж ·пјҢжҳҜз”ҹе‘ҪеҫӢеҠЁзҡ„иҮӘ然规еҫӢпјҢжүҖд»ҘпјҢжҳҘеӨ©дёӯд»Ҙи°Ҳжғ…иҜҙзҲұдёәзӣ®зҡ„зҡ„иөӣжӯҢпјҢдҪ“зҺ°дәҶдәәдёҺиҮӘ然зҡ„дәІе’ҢпјҢдәәдёҺдәәзҡ„дәІе’ҢдёҖйҰ–и—Ҹж—Ҹж°‘жӯҢе”ұйҒ“пјҡвҖңеұұиҷҪдёҚеңЁдёҖиө·пјҸйӣӘеҗҺдёҖж ·жҙҒзҷҪпјҸпјҸиҠұиҷҪдёҚеңЁдёҖиө·пјҸжҳҘеӨ©дёҖйҪҗејҖж”ҫ пјҸпјҸ жҲ‘дҝ©иҷҪдёҚеңЁдёҖиө·пјҸеҪјжӯӨж°ёдёҚеҸҳеҝғвҖқпјҢиҝҷйҮҢжҳҘиҠұз»Ҫж”ҫжҳҜдёӨжғ…зӣёеҗҲзҡ„иұЎеҫҒгҖӮеҶҚеҰӮвҖңдҪ жҳҜејҜејҜзҡ„жҳ еұұзәўпјҸжҲ‘жҳҜејҜејҜзҡ„е°Ҹжқңй№ғпјҸеҸӘиҰҒе’ұдҝ©жғ…ж„ҸеҗҲпјҢеүҚйһ’еҗҺйһ’дёҖеүҜйһҚвҖқгҖӮеҸҜи§ҒпјҢеұұиҠұз»Ҫж”ҫзҡ„жҳҘеӨ©жҳҜвҖңе’ұдҝ©жғ…ж„ҸеҗҲвҖқзҡ„дҪіжңҹгҖӮеҸҲеҰӮй—Ёе·ҙж—Ҹзҡ„дёҖйҰ–жғ…жӯҢпјҡвҖңвҖҳе®үе®«вҖҷиҠұзҷҪиғңжҙҒпјҸдёҚеҰӮй…ҘжІ№дјјйӣӘ пјҸ й…ҘжІ№дјјпјҸйӣӘзҠ№йҰҷ пјҸдёҚеҰӮ姑еЁҳй«ҳе°ҡ пјҸжқңй№ғиҠұзәўзҒ«зғҲпјҸдёҚеҰӮвҖҳиҗғеҰӮвҖҷпјҲ2пјүдјјиЎҖпјҸвҖҳиҗғеҰӮвҖҷдјјиЎҖзҠ№зӣӣ пјҸдёҚеҰӮ姑еЁҳиөӨиҜҡвҖқгҖӮиҝҷйҮҢ姑еЁҳзҡ„й«ҳе°ҡе’ҢиөӨиҜҡд№ҹжҳҜиҝҷзҫҺеҰҷзҡ„жҳҘеӨ©жҡ—зӨәзҡ„гҖӮ
жҳҘж—ҘеҜ№жӯҢжҳҜдәәи°ғйҖӮиҮӘ然зҡ„д»ӘејҸжҙ»еҠЁпјҢд№ҹжҳҜи°ғйҖӮдёҚеҗҢең°еҢәгҖҒдёҚеҗҢжҖ§еҲ«гҖҒдёҚеҗҢзӨҫдјҡзҫӨдҪ“зҡ„д»ӘејҸжҙ»еҠЁгҖӮйҰ–е…ҲжҲ‘们зңӢеҲ°зҡ„жҳҜпјҢжҳҘеӨ©йҮҺеӨ–йӣҶдјҡдёӯзҡ„йқ’е№ҙз”·еҘіиөӣжӯҢиЎҢдёәпјҢеӨҡеҸ‘з”ҹеңЁйқһиЎҖзјҳжҖ§зҡ„йҷҢз”ҹз”·еҘіжҖ§еҲ«йӣҶеӣўд№Ӣй—ҙгҖӮеә·еҢәзҡ„дёҖйҰ–и—Ҹж—Ҹж°‘жӯҢе”ұйҒ“пјҡвҖңд»ҺеүҚжҲ‘дҝ©дёҚзӣёиҜҶпјҸжҳҜзңјзқӣе…Ҳи®ІиҜқзҡ„пјҸ иө·еҲқжүҫдёҚеҲ°жқҘеҫҖзҡ„и·Ҝ пјҸжҳҜжӯҢеЈ°еј•зҡ„и·ҜвҖқгҖӮжҠҠвҖңдёҚзӣёиҜҶвҖқз”·еҘізүөиҝһеңЁдёҖиө·зҡ„еҜ№жӯҢд№ дҝ—пјҢжү“з ҙдәҶ家еәӯгҖҒж°Ҹж—ҸгҖҒжқ‘иҗҪе°Ғй—ӯжҖ§зҡ„жҺ’д»–дё»д№үпјҢеүҠејұдәҶжҖ§еҲ«йӣҶеӣўзҡ„еҜ№з«Ӣе’ҢзӨҫдјҡйӣҶеӣўзҡ„еҜ№жҠ—пјҢдҝғиҝӣдәҶиҒ”姻иЎҢдёәзҡ„еҸ‘з”ҹпјҢжҳҜдәәеҸҠе…¶жүҖеұһең°еҹҹгҖҒе®—ж•ҷе’ҢжҖ§еҲ«йӣҶеӣўзҡ„жһҒеҘҪзҡ„дәӨжҚўеҪўејҸпјҢиҝҷз§ҚдәӨжҚўе·©еӣәдәҶзӨҫдјҡзҡ„иҒ”еҗҲпјҢиҫҫжҲҗдәҶзӨҫдјҡзҡ„еҘ‘зәҰгҖӮз”ұдәҺе…ұеҗҢе®—ж•ҷеңәең°зҡ„йҖүжӢ©е’ҢеҜ№жӯҢпјҢи·Ёжқ‘иҗҪеҪўжҲҗе®—ж•ҷиҒ”зӣҹжҲҗдёәеҸҜиғҪгҖӮеҜ№жӯҢжҙ»еҠЁдёӯпјҢеҗҢжқ‘жҲ–еҗҢж°Ҹж—Ҹзҡ„еҗҢжҖ§йқ’е№ҙиҮӘ然иҒ”жҲҗз»„йҳөпјҢжң¬жқ‘пјҲж°Ҹж—Ҹпјүзҡ„з”·йқ’е№ҙжӯҢе”ұйҳҹдёҺйӮ»жқ‘пјҲж°Ҹж—Ҹпјүзҡ„еҘійқ’е№ҙжӯҢе”ұйҳҹеұ•ејҖиҲһи№Ҳе’ҢжӯҢе”ұзҡ„з«һдәүпјҢеҜ№ж–№дәҰ然гҖӮиҝҷдәӣеҸӮеҠ иөӣжӯҢзҡ„йқ’е№ҙз”·еҘіж—ўжҳҜжҖ§зҡ„д»ЈиЎЁиҖ…пјҢд№ҹжҳҜ他们жқ‘еә„пјҲж°Ҹж—ҸжҲ–家ж—ҸпјүйӣҶеӣўзҡ„д»ЈзҗҶиҖ…гҖӮжӯҢе”ұиЁҖиҫһз”ұеҜ№жҠ—пјҲеҺӢеҖ’еҜ№ж–№пјүеҲ°жҺҘиҝ‘пјҲи®ӨеҗҢеҜ№ж–№пјүпјҢж„ҹжғ…йҡҸзқҖеҸҚеӨҚе’Ҹе”ұиҖҢж„ҲзӣҠе…ҙеҘӢгҖӮжӯҢеЈ°зңҹжӯЈжҲҗдәҶиҒ”з»“зҲұжғ…зҡ„дј еӘ’гҖӮи—Ҹж—Ҹж°‘жӯҢеҰӮжӯӨеӨёиөһдәҶжӯҢе”ұеңЁиҝһжҺҘзҲұжғ…дёӯзҡ„зү№ж®Ҡйӯ…еҠӣпјҡвҖңжІійӮЈиҫ№жңүеҚғдёҮжңөйІңиҠұпјҸжҲ‘еҸӘзҲұж јжЎ‘иҠұпјҸеҚғдёҮжңөиҠұйҰҷж··еңЁдёҖиө·пјҸжҲ‘иғҪиҫЁеҮәж јжЎ‘иҠұзҡ„йҰҷе‘іпјҸпјҸжІійӮЈиҫ№жңүеҚғдёҮдёӘ姑еЁҳпјҸжҲ‘еҸӘзҲұж”ҫзҫҠ姑еЁҳ пјҸеҚғдёҮдёӘ姑еЁҳеңЁдёҖиө·е”ұжӯҢпјҸжҲ‘иғҪеҲҶиҫЁж”ҫзҫҠ姑еЁҳзҡ„жӯҢеЈ°вҖқпјҢвҖңжҲ‘жғіжғ…дәәзҡ„еҝғжҖқиҜҙдёҚжҲҗпјҸиӢҘиҜҙжҲ‘жғіжғ…дәәзҡ„еҝғжҖқе“ҹпјҸжҲ‘жҜҸеӨ©еӨңйҮҢжўҰдёүеұӮпјҸжўҰи§ҒеҘ№еҸЈе”ұжғ…жӯҢжқҘзӣёдјҡпјҸжўҰи§ҒеҘ№зғӯжүӢжҗӯеңЁжҲ‘иӮ©дёҠпјҸжўҰи§ҒеҘ№зәўй»‘дёқзәҝдёҖйҪҗжӢјпјҢжўҰи§ҒеҘ№дёүеҸҘжғ…иҜқз”ңйҖҸеҝғвҖқгҖӮи—Ҹж—Ҹж°‘й—ҙз”·еҘізҡ„е©ҡ姻еӨҡд»ҘжӯҢдёәеӘ’пјҢжӯҢеЈ°жҳҜдёӨжҖ§иһҚеҗҲзҡ„еүҚжҸҗе’Ңж Үеҝ—гҖӮ
еІҒж—¶зӨјдҝ—жҙ»еҠЁдёә他们жҸҗдҫӣдәҶеңЁзҘһеңЈе…үзҺҜз¬јзҪ©дёӢзҡ„з»“дәӨжңәдјҡпјҢйҷӨдәҶжҙ»еҠЁзҡ„дё»жҢҒиҖ…пјҢйқ’е№ҙз”·еҘідҫҝжҳҜеІҒж—¶зӨјдҝ—жҙ»еҠЁзҡ„жңҖжҙ»и·ғзҡ„жҲҗе‘ҳгҖӮйқ’е№ҙ们жҢүжҖ§еҲ«з»„жҲҗвҖңжҖ§еҲ«йӣҶеӣўвҖқеҸӮеҠ иҲһи№Ҳе’Ңе”ұжӯҢзҡ„з«һдәүпјҲеҚіиөӣжӯҢ songвҖ”tyingпјүиҜ—жӯҢе’ҢжҒӢзҲұеҗҢж—¶д»Һиҝҷз§Қз«һдәүдёӯдә§з”ҹеҮәжқҘпјҢ他们дёҖзҫӨеҗ‘еҸҰдёҖзҫӨпјҢдёҖдёӘеҗ‘еҸҰдёҖдёӘпјҢз”ЁжӯҢеЈ°еҸ‘еҮәжҢ‘жҲҳе’ҢжҢ‘йҖ—гҖӮзӯүзә§еҲ¶еәҰе’Ңе°ҠеҚ‘规е®ҡеңЁиҝҷдёӘзҹӯжҡӮзҡ„ж—¶й—ҙеҶ…еӨұж•ҲдәҶпјӣд»ӘејҸзҡ„еҸӮеҠ иҖ…д»ҝдҪӣз»„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з»қеҜ№е№ізӯүзҡ„д№ҢжүҳйӮҰзҺӢеӣҪпјҢе®ғжҳҜж„ҹжғ…дәӨжөҒзҡ„ејҖе§ӢпјҢжҳҜеҶ…еҝғжҺҘи§Ұзҡ„йў„жј”гҖӮпј»1пјҪпјҲP263пјүвҖңдәҺжҳҜдҫҝејҖе§Ӣд»ҘеҜ№жӯҢзҡ„еҪўејҸиҝӣиЎҢиөӣжӯҢеҫҲеӨҡжӯҢи°Јеҗ«жңүи°ғжғ…зҡ„иҜӯи°ғгҖӮ姑еЁҳ们еҜ№йӮЈдәӣж”ҫиӮҶзҡ„йӮ»жқ‘зҡ„е°Ҹдјҷеӯҗ并дёҚжӢ’з»қпјҢзӣёеҸҚпјҢиҝҷз§Қж”ҫиӮҶжҒ°жҒ°жҳҜ姑еЁҳ们йҖүжӢ©дёӯдёҚеҸҜзјәе°‘зҡ„жқЎд»¶вҖқгҖӮпј»2пјҪжі•еӣҪи‘—еҗҚзҡ„зӨҫдјҡеӯҰжҙҫдәәзұ»еӯҰ家и‘ӣе…°иЁҖ пјҲGrenardпјүжӣҫжіЁж„ҸеҲ°иҘҝи—Ҹж°‘жӯҢпјҲзү№еҲ«жҳҜжғ…жӯҢпјүзҡ„еҜ№е”ұеңЁж°‘дҝ—жҙ»еҠЁдёӯзҡ„йҮҚиҰҒжҖ§пјҢд»–иҝҷж ·еҶҷйҒ“пјҡ
жғ…жӯҢзҡ„з«һдәүвҖҰвҖҰиҝҷж ·зҡ„д№ дҝ—еңЁиҘҝи—Ҹд№ҹеҸҜзңӢеҲ°вҖҰвҖҰ
дёҖгҖҒжӯҢи°Јзҡ„иө·жәҗжҳҜз”·еҘійқ’е№ҙзӣёеҜ№еіҷзҡ„дәӨдә’еҗҲе”ұвҖҰвҖҰеңЁиҘҝи—ҸпјҢдәә们е–ңж¬ўз”·еҘізҡ„дәҢйҮҚеҗҲе”ұпјҢжҺ’жҲҗеҜ№йқўдёӨеҲ—пјҢжҢүз…§жӢҚеӯҗдёҖиҝӣдёҖйҖҖпјҢз”ЁиҜ—еҸҘдә’зӣёеә”зӯ”гҖӮ
дәҢгҖҒеҗҲе”ұиў«йқ’е№ҙз”·еҘізҡ„жҢ‘жҲҳе’ҢзҲұжғ…иЎЁзҷҪзҡ„еҚіе…ҙиҜ—жүҖеҲҶеүІвҖҰвҖҰеңЁиҘҝи—ҸпјҢз»“е©ҡж—¶пјҢе№ҙиҪ»з”·еҘід»¬зҡ„дәӨдә’ж··еЈ°жӯҢдёҖе®ҢпјҢдҫҝејҖе§ӢиҪ®з•ӘжӯҢе”ұеҜ№иҒ”жҲ–еӣӣиЎҢиҜ—пјҢеҜ№дёҚеҮәиҖ…иҰҒдәӨзҪҡйҮ‘гҖӮ
дёүгҖҒжғ…жӯҢзҡ„з«һдәүпјҢеңЁдј—еӨҡдјҡдј—еҸӮеҠ зҡ„еӯЈиҠӮзҘӯдёӯдёҺе…¶д»–з§Қз§Қз«һдәүз»“еҗҲиҝӣиЎҢгҖӮеҗ«жңүжҖ§зҡ„д»ӘзӨјзҡ„зҘӯзӨјеә”дёәзәҰе©ҡжҲ–з»“е©ҡзҡ„зҘӯзӨјгҖӮ
вҖҰвҖҰиҘҝи—ҸдәәеҹӢеӨҙдәҺжҳҘеӨ©зӣӣеӨ§зҡ„жӯҢи°Јжј”еҘҸгҖӮпј»3пјҪ
е°Ҫз®Ўи‘ӣе…°иЁҖжүҖиЁҖдҪҝз”Ёзҡ„жқҗж–ҷжңӘеҝ…е…ёеһӢе’ҢеҮҶзЎ®пјҢпј»3пјҪдҪҶи—Ҹж—Ҹз”·еҘійқ’е№ҙи°Ҳжғ…иҜҙзҲұе……ж–ҘзқҖеӨ§йҮҸзҡ„еҜ№е”ұд»ҘеҸҠе©ҡзӨјеүҚеҗҺиҮӘе§ӢиҮіз»ҲејҘжј«зқҖжӯҢеЈ°зҡ„жғ…еҶөпјҢзЎ®зі»дәӢе®һгҖӮеңЁиҝҷдәӣдёӨжҖ§з»“дәӨзҡ„жӯҢе”ұдёӯпјҢдёҚи®әз”·еҘіе“Әж–№е…Ҳе”ұпјҢе…Ҳе”ұзҡ„йғҪеҗ«жңүжҸЈж‘©гҖҒиҜ•жҺўд№ғиҮіжҢ‘йҖ—зҡ„еҸЈеҗ»пјҢиҜ·зңӢдёӢйқўзҡ„и—Ҹж—Ҹж°‘жӯҢпјҡ
гҖҖгҖҖи“қи“қзҡ„еӨ©дёҠйЈҳеҠЁзқҖеҗ„иүІеҗ„ж ·зҡ„дә‘еҪ©пјҢ
гҖҖгҖҖжҲ‘й—®дҪ еҲ°еә•зҲұе“ӘдёҖжңөпјҹ
гҖҖгҖҖжҲ‘зҡ„йЎ№й“ҫдёҠжңүзҸҠз‘ҡгҖҒзҗҘзҸҖе’ҢзҺӣз‘ҷпјҢ
гҖҖгҖҖжҲ‘й—®дҪ еҲ°еә•зҲұе“ӘдёҖйў—пјҹ
гҖҖгҖҖеә„еӯҗдёҠжңүиҝҷд№ҲеӨҡжјӮдә®зҡ„姑еЁҳпјҢ
гҖҖгҖҖжҲ‘й—®дҪ еҲ°еә•зҲұе“ӘдёҖдёӘпјҹ
гҖҖгҖҖи“қи“қзҡ„еӨ©дёҠйЈҳеҠЁзқҖеҗ„иүІеҗ„ж ·зҡ„дә‘еҪ©пјҢ
гҖҖгҖҖжҲ‘еҸӘзҲұеғҸзҷҪеӨ©й№…зҡ„йӮЈдёҖжңөгҖӮ
гҖҖгҖҖдҪ зҡ„йЎ№й“ҫдёҠжңүзҸҠз‘ҡгҖҒзҗҘзҸҖе’ҢзҺӣз‘ҷпјҢ
гҖҖгҖҖжҲ‘еҸӘзҲұиғёеүҚеҸҲзәўеҸҲеӨ§зҡ„йӮЈдёҖйў—гҖӮ
гҖҖгҖҖеә„еӯҗдёҠжңүйӮЈд№ҲеӨҡжјӮдә®зҡ„姑еЁҳпјҢ
гҖҖгҖҖжҲ‘еҸӘзҲұеҸҲзҫҺеҸҲеӢӨеҠізҡ„дҪ дёҖдёӘгҖӮ
иҝҷжҳҜеҘіе”ұз”·е’Ңзҡ„дҫӢеӯҗгҖӮеҶҚеҰӮдёҖйҰ–з”·е”ұеҘіеә”зҡ„и—Ҹж—Ҹжғ…жӯҢпјҡвҖңз”·пјҡд»ҺжңӘдәІиҮӘзҲ¬иҝҮйӣӘеұұпјҸдёҚзҹҘи·ҜзЁӢжҳҜеҗҰиү°йҷ© пјҸ д»ҺжңӘдёҺдәәи°Ҳжғ…иҜҙзҲұ пјҸдёҚзҹҘйҮҢйқўжҳҜиӢҰжҳҜз”ң пјҸпјҸеҘіпјҡиҰҒжғіжҺўжҳҺеұұи·ҜпјҸйңҖиҰҒиҮӘе·ұи·‘еҫҖеұұдёҠпјҸиҰҒжғізҹҘйҒ“зҲұжғ…зҡ„е‘ійҒ“ пјҸдҪ е°ұиҮӘе·ұеӨ§иғҶең°жқҘе°қе°қвҖқгҖӮи—Ҹж—Ҹз”·еҘіжғ…жӯҢеҜ№е”ұзҡ„дәӢдҫӢйқһеёёдё°еҜҢгҖӮиӢҘе°Ҷи—Ҹж—Ҹе©ҡжҒӢдёӯиҝҷз§ҚжӯҢе”ұзҡ„д№ дҝ—иҝӣиЎҢжәҜжәҗзҡ„иҜқпјҢжҲ‘们иҮіе°‘еҸҜд»Ҙд»ҺдёӯеҸ‘зҺ°дёүж–№йқўзҡ„еҶ…е®№пјҡпјҲ1пјүеҜ№е”ұпјҲдәӨжӣҝеҗҲе”ұпјүзҡ„еҪўејҸжқҘиҮӘеҸӨд»Јж°‘ж—ҸеӨ–е©ҡпјҲеҚіејӮж—Ҹе©ҡпјүзҡ„йҒ—з•ҷд№ жғҜпјӣпјҲ2пјүжӯҢе”ұжҳҜдёҖз§ҚзҪ®дәҺеҺҹе§Ӣе·«жңҜжҖқз»ҙж”Ҝй…ҚдёӢзҡ„вҖңиҜӯиЁҖйӯ”жі•вҖқпјҢеҚіеқҡдҝЎжӯҢе”ұеҶ…е®№дёӯжүҖж¬Іе®һзҺ°зҡ„еҚіжҳҜдәӢе®һдёҠиғҪеӨҹе®һзҺ°зҡ„пјӣпјҲ3пјүжғ…жӯҢжңҖеҲқжҳҜйӣҶдҪ“жҙ»еҠЁдёӯзҡ„дәӨдә’еҗҲе”ұпјҲиөӣжӯҢпјүпјҢжҒӢзҲұдёҚиў«зңӢжҲҗжҳҜз§ҒдәӢиҖҢжҳҜеңЁйӣҶдҪ“жҖ§зҡ„д»ӘејҸжҙ»еҠЁдёӯеҸ‘з”ҹзҡ„гҖӮпј»3пјҪ
жӯЈжҳҜжғ…жӯҢе”ұиҜөдҫқжүҳдәҺйӣҶдҪ“д»ӘејҸпјҢеӣ жӯӨд»ӘејҸдҫҝдёәжғ…жӯҢеҜ№зӯ”жҸҗдҫӣдәҶйҖӮдёӯзҡ„жңәдјҡгҖӮд»ӘејҸи®©дәә们иҒҡйӣҶпјҢжӯҢеЈ°и®©дәә们жҒӢзҲұгҖӮдёҖйҰ–и—Ҹж—Ҹж°‘жӯҢе”ұйҒ“пјҡ
гҖҖгҖҖ第дёҖж¬ЎзӣёзҶҹжҳҜжҳҺдә®зҡ„зңјпјҢ
гҖҖгҖҖзңјзқӣзңӢиҠұдәҶиҝҳжғізңӢпјӣ
гҖҖгҖҖ第дәҢж¬ЎзӣёзҶҹжҳҜжӯҢеЈ°пјҢ
гҖҖгҖҖдёүеҸҘеұұжӯҢе”ұеҠЁдәҶжғ…пјӣ
гҖҖгҖҖ第дёүж¬ЎзӣёзҶҹз»“дәҶдәІпјҢ
гҖҖгҖҖдәІдәІзғӯзғӯеҗҲжҲҗдёҖдёӘдәәгҖӮ пјҲзҺӢжІӮжҡ–иҜ‘пјү
иҝҷдёүж¬ЎвҖңзӣёзҶҹвҖқжңҖе…ій”®зҡ„ең°ж–№жҳҜвҖңдёүеҸҘеұұжӯҢе”ұеҠЁдәҶжғ…вҖқгҖӮд»ӘејҸжҙ»еҠЁдёӯеҖҹжӯҢеЈ°дј жғ…пјҢжҲҗдәҶеҜ№жӯҢзҡ„дё»иҰҒеҠҹиғҪгҖӮеҚід»ӘејҸеҠҹиғҪдёӯйҡҗеҗ«дәҶжҖ§еҲ«дәӨжҚўзҡ„еҠҹиғҪгҖӮ
иҝҷз§Қе”ұжғ…жӯҢз»“еҜ№еӯҗзҡ„д№ дҝ—пјҢд№ҹи§ҒдәҺиҘҝи—Ҹзҡ„е…¶д»–ж°‘ж—ҸгҖӮй—Ёе·ҙж—Ҹзҡ„дёҖйҰ–жғ…жӯҢпјҡвҖңзҺүе”ҮдёҚиҰҒзҙ§й—ӯпјҸе”ұйҰ–жӯҢе„ҝжҲ‘еҗ¬пјҸеҚідҪҝиҝӣеҲ°ең°зӢұпјҸзҠ№з„¶дј дҪ жӯҢеЈ°вҖқгҖӮпј»4пјҪпјҲP58пјүеҸҲеҰӮжөҒдј еңЁзҸһе·ҙж—ҸзұіеҸӨе·ҙйғЁиҗҪзҡ„дёҖйҰ–еҜ№жӯҢе”ұйҒ“пјҡ
гҖҖгҖҖз”·пјҡеҜ№жӯҢзҡ„ж—¶еҲ»еҲ°дәҶпјҢ
гҖҖгҖҖжқ‘йҮҢзҡ„姑еЁҳ们еҗ¬зқҖпјҢ
гҖҖгҖҖе“ӘдёӘеҜ№жҲ‘жңүжғ…пјҢ
гҖҖгҖҖиҜ·з”ЁжӯҢеЈ°иЎЁжҳҺгҖӮ
гҖҖгҖҖеҘіпјҡиӢұдҝҠе°‘е№ҙзҡ„еј“з®ӯпјҢ
гҖҖгҖҖз…§еҫ—жҲ‘зңјиҠұеҝғд№ұпјӣ
гҖҖгҖҖз»•иҝҮж ‘жўўзңӢдёҖзңјпјҢ
гҖҖгҖҖеҺҹжқҘжҳҜдёҖеҸӘзәўи„ёжқңй№ғгҖӮ
жӯҢи°ЈеҜ№е”ұдёӯзҡ„иҝҷз§ҚжҢ‘йҖ—е’ҢжҲҸи°‘жҒ°еҘҪжҳҜжҒӢзҲұзҡ„ејҖе§ӢгҖӮеҶҚеҰӮе–ң马жӢүйӣ…еұұеҚ—йә“е°јжіҠе°”дәәеңЁжҳҘеӨ©й…’зәўиҠӮеҲ°жқҘд№Ӣйҷ…пјҢйқ’е№ҙдәәеҫҖеҫҖеҖҹжӯӨжңәдјҡеҺ»еҜ№жӯҢжұӮзҲұгҖӮз”·йқ’е№ҙеңЁе§‘еЁҳзҡ„жҘјдёӢе”ұйҒ“пјҡвҖңжҘјдёҠзҡ„姑еЁҳжҲ‘зҲұдҪ пјҢдҪ дёҚдёӢжҘјжҲ‘з»қйЈҹгҖӮвҖқ姑еЁҳиӢҘжңүж„ҸпјҢе°ұдјҡеҜ№жӯҢзӨәзҲұпјҢеҗҢж„ҸдёҺе…¶зәҰдјҡпјҢеҗҰеҲҷе°ұдјҡзӯ”е”ұпјҡвҖңеҘҪеҘҪзҡ„еӨ§зұіжҲ‘жңүдёҖзў—пјҸзў—йҮҢж”ҫзқҖдёӨйёЎиӣӢпјҸзӯүдҪ еӨ§е“ҘйҘұйӨҗеҗҺ пјҸе°ҸеҝғиөҸдҪ дёҖз«№жқ–вҖқгҖӮз”·йқ’е№ҙжҳҺзҷҪж— жңӣпјҢдҫҝдјҡеҸҰеҜ»еҜ№иұЎеҺ»и°ғжғ…гҖӮ
и®ёеӨҡж°‘ж—ҸеҜ№жӯҢзҡ„е°ҫеЈ°пјҢжҳҜзӣёдә’зңӢдёӯзҡ„з”·еҘіжҲҗеҸҢжҲҗеҜ№зҰ»ејҖеҜ№жӯҢзҫӨдҪ“并йҡҗжІЎдәҺж¬ўдјҡз§ҳжүҖжҲ–еӨң幕иҚүдёӣд№ӢдёӯгҖӮи—Ҹж—ҸжҳҜеҜ№е®ҢжӯҢеҗҺзҡ„жңүжғ…дәәз§ҳеҜҶдәӨжҚўе®ҡжғ…зү©пјҡвҖңйӮЈжІіиҫ№жңүеә§жқҫе°”зҹіеұұпјҸеұұи„ҡйқ’е№ҙзҡ„жӯҢеЈ°еҠЁеҗ¬пјҸйқ’е№ҙпјҢдҪ иӢҘжҳҜиҜҙзҡ„зҹҘеҝғиҜқ пјҸиҜ·еёҰзқҖзҸҠз‘ҡз®Қеӯҗи·‘иҝҮжқҘвҖқпј»4пјҪе°јжіҠе°”еҲ©е§ҶеёҢдәәйҖҡеёёдәҺжҳҘеӨ©жӯҢдјҡж—¶пјҢз”ЁеҜ№жӯҢеҜ»жұӮй…ҚеҒ¶гҖӮдёҖиҲ¬еңЁеҜ№жӯҢдјҡдёҠйӮ»жқ‘姑еЁҳе…Ҳе”ұпјҢ然еҗҺжң¬жқ‘з”·йқ’е№ҙеҜ№зӯ”пјҢдёҖжқҘдәҢеҺ»и¶Ҡе”ұи¶ҠдәІиҝ‘пјҢйҡҸеҚіеҸҢеҸҢжҗәжүӢзҰ»ејҖжӯҢдјҡпјҢеҲ°жһ—дёӯж·ұеӨ„еӘҫе’ҢпјҢеҰӮжӯӨеҚідёәеӨ«еҰ»гҖӮзҝҢж—ҘжҷЁпјҢеҘіеӯҗеӣһ家е‘ҠзҹҘзҲ¶жҜҚиҮӘе·ұе·Із»ҸеҮәе«Ғпјӣз”·еӯҗеӣһеҲ°е®¶дёӯпјҢиҰҒжұӮзҲ¶жҜҚжүҳеӘ’дәәйҖҒеҪ©зӨјеҲ°еҘіе®¶иҰҒжұӮе®Ңе©ҡгҖӮеҸҜи§ҒпјҢжҳҘзҘӯйҮҺеӨ–йӣҶдјҡжҸҗдҫӣдәҶејӮжқ‘пјҲж°Ҹж—Ҹпјүз”·еҘідәӨз»“пјҢеҸ‘з”ҹзҲұжғ…зҡ„жңәдјҡпјҢеҜ№жӯҢдҫҝжҲҗдәҶеҜ№пјҲж°Ҹж—ҸпјүеӨ–е®һиЎҢе©ҡ姻关系пјҲејӮж°Ҹж—Ҹе©ҡпјүзҡ„йҒ—з•ҷж°‘дҝ—гҖӮ
з”ұдәҺеҜ№жӯҢеёёеёёжҳҜеңЁйӣҶдҪ“жҙ»еҠЁдёӯеұ•ејҖзҡ„пјҢжҳҜдј—дәәеҸӮдёҺзҡ„пјҢжӯҢе”ұиҖ…е”ұиҜөзҡ„йғҪжҳҜеӨ§е®¶е…ұйҖҡзҡ„ж„ҹжғ…пјҢеңЁдј—еӨҡз”·еҘіе…ұеҗҢеҸӮдёҺзҡ„еңәеҗҲпјҢдёӘдәәзҡ„ж„ҹжғ…йҡҗеҗ«еңЁйӣҶдҪ“зҡ„ж„ҹжғ…д№ӢдёӯгҖӮиҝҷз§Қж„ҹжғ…жүҖд»Ҙеј•еҸ‘е…ұйёЈпјҢжҳҜеӣ дёәжңҖеҲқзҲұжғ…жҳҜеңЁйӣҶдҪ“зҡ„д»ӘејҸжҖ§жҙ»еҠЁдёӯиҜһз”ҹзҡ„гҖӮ
жғ…жӯҢеҜ№е”ұзҡ„йӣҶдҪ“жҖ§еҝ…然еҜјиҮҙжӯҢи°ЈйҮҢйқўжҒӢдәәеҪўиұЎзӣёдјјпјҢиЎЁиҫҫжғ…ж„ҹзҡ„ж–№жі•зӣёеҗҢпјӣж„ҹжғ…иҮӘ然жөҒйңІзҡ„еӨҡпјҢеҲ»ж„Ҹйӣ•зҗўзҡ„е°‘пјӣзјәе°‘иҜ—дәәиҲ¬зҡ„жғіиұЎпјҢд№ҹзјәд№ҸжҠҖе·§пјҢжғ…жӯҢзҡ„зҫҺдёҪеӯҳеңЁдәҺеҚ•зәҜзҡ„жҸҸеҶҷе’ҢзӣҙзҺҮзҡ„ж„ҹжғ…иЎЁзҺ°еҪ“дёӯгҖӮеҚідҫҝиҜҙеҸҚеӨҚгҖҒеҜ№еҒ¶жҳҜжғ…жӯҢдёӯеҜҢжңүзү№иүІзҡ„жҠҖе·§пјҢдҪҶиҝҷз§ҚжҠҖе·§жҳҜеҫ—зӣҠдәҺзҘӯд»Әдёӯз”·еҘідәӨжӣҝеҗҲе”ұ пјҲж··еЈ°жӯҢпјүе’ҢеҜ№иҲһпјҢдҪ“зҺ°дәҶй…ҚеҗҲеҠЁдҪңиҠӮеҘҸзҡ„йңҖиҰҒгҖӮи—Ҹж—ҸеҶңеҢәзҡ„ж°‘й—ҙиҲһвҖңжһңеҚҸвҖқпјҢеңЁз”·еҘідәӨжӣҝеҗҲе”ұдёӯиёҸең°иө·иҲһпјҢеұҠж—¶з”·еҘіеҲҶз«ҷдёӨжҺ’пјҢиҪ®зҸӯжӯҢе”ұпјҢ并д»Һе·Ұеҗ‘еҸіжІҝеңҲиҲһеҠЁгҖӮжүҖе”ұзҡ„жӯҢеҸҘжңүзӣёеҪ“еӨҡзҡ„еҸҚеӨҚпјҡвҖңеҰӮжһңжңүдҪ иҝҷж ·дёҖеҢ№й©¬пјҸжІЎжңүйҮ‘йһҚд№ҹдёҚйҡҫиҝҮпјҸпјҸеҰӮжһңжңүдҪ иҝҷж ·дёҖеӨҙзүӣпјҸжІЎжңүиҢ¶еҢ…д№ҹдёҚйҡҫиҝҮ пјҸпјҸеҰӮжһңжңүдҪ иҝҷж ·зҡ„жғ…дәәпјҸжІЎжңүиҙўдә§д№ҹдёҚйҡҫиҝҮвҖқгҖӮжӯҢдёӯдёүиҠӮеҸҚеӨҚпјҡвҖңеҰӮжһңжңүдҪ иҝҷж ·вҖҰвҖҰжІЎжңүвҖҰвҖҰд№ҹдёҚвҖҰвҖҰвҖқиҝҷж ·зҡ„еҸҘејҸгҖӮиҝҷиҜҙжҳҺпјҢеҸҚеӨҚжҳҜжһ„жҲҗжӯҢи°ЈиҠӮеҘҸе’ҢйҹөеҫӢзҡ„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жүӢж®өпјҢеӣ дёәеҸӘжңүеҸҚеӨҚең°еҗҹе”ұжүҚиғҪ收еҲ°вҖңдёҖе”ұдёүеҸ№вҖқзҡ„ж•ҲжһңгҖӮеҸҚеӨҚйҖҡиҝҮеҸҘејҸзҡ„зЁӢејҸеҢ–д»ҘйҖ жҲҗжғ…ж„ҹдёҠзҡ„еҸҚеӨҚдҪ“йӘҢпјҢдҪҝдәәеҸҚеӨҚдҪ“йӘҢе’ҢзҺ©е‘іжҹҗз§Қжғ…и°ғгҖӮеҸҚеӨҚгҖҒеҜ№еҒ¶иҝҷдәӣиҮӘи§үйҒөеҫӘзҡ„гҖҒзәҰе®ҡдҝ—жҲҗзҡ„д№ жғҜжҖ§жј”е”ұ规еҲҷпјҢиҜһз”ҹдәҺйӣҶдҪ“е”ұе’Ңд№ӢдёӯпјҢжҳҜйӣҶдҪ“е”ұе’Ңеҹ№жӨҚзҡ„гҖӮеңЁдёҖе”ұдј—е’ҢжҲ–дёҖе”ұдёҖе’ҢжҲ–еҮ дәәе”ұдј—дәәе’Ңзҡ„жј”е”ұж–№ејҸдёӯпјҢе’ҢиҖ…еҜ№йўҶе”ұиҖ…зҡ„жӯҢеҸҘзҡ„йҮҚеӨҚеҫҖеҫҖжҳҜдёҖйЎ№е…ұзҹҘзҡ„й»ҳеҘ‘гҖӮиҝҷз§Қй»ҳеҘ‘жңҖеҲқжҳҜе®—ж•ҷжҖ§зҡ„пјҢз”·еҘіз”ЁжқҘеҜ№е”ұеҲҷжҲҗдёәдј жғ…жҖ§зҡ„гҖӮжҜ”еҰӮе–ң马жӢүйӣ…еұұдёңеҚ—йә“зҸһе·ҙж—ҸйҳҝиҝӘдәәжј”е”ұеҪўејҸд№ӢдёҖзҡ„вҖңжіўйҡҶвҖқеңЁзҘӯд»Әдёӯе…Ҳз”ұе·«еёҲзұіеүӮйўҶе”ұпјҢеҮЎеңЁйўҶе”ұж–°зҡ„ж®өиҗҪд№ӢеүҚпјҢ姑еЁҳ们йғҪйӣҶдҪ“йҮҚе”ұдёҠдёҖеҸҘпјҢ并жҢүз…§жӯҢжӣІзҡ„иҠӮеҘҸи·іиҲһпјҢеҗҺжқҘиҝҷз§ҚйҮҚе”ұе’Ңи·іиҲһдҫҝ移用еҲ°еҜ№жӯҢдёҠеҺ»гҖӮпј»5пјҪпјҲP157пјүеҚ°еәҰж—ҒйҒ®жҷ®йӮҰзҡ„вҖңж јеЎ”иҲһвҖқпјҲеңҲиҲһпјүеҪ“и·іеҲ°еңҲеӯҗжү“ејҖеҗҺпјҢдҫҝжңүдёүеӣӣдәәиө°еҲ°еҪ“дёӯиө·иҲһйўҶе”ұдёҖз§ҚеҸ«вҖңеЎ”жӢңвҖқпјҲжҲ–вҖңе·ҙеҫ·вҖқпјүжҳҜж°‘жӯҢпјҢжҜҸиҮіжң«еҸҘпјҢе‘Ёеӣҙдјҙе”ұзҡ„дәәпјҲеӨҡдёәеҘіеӯҗпјүе°ұиҰҒжӢҚзқҖжүӢе°ҶиҜҘжң«еҸҘйҮҚе”ұдёҖйҒҚпјҢеҰӮжӯӨеҸҚеӨҚпјҢзӣҙиҮіз»“жқҹгҖӮпј»6пјҪиҝҷз§Қд»ӘејҸдёҠзҡ„еҸҚеӨҚе”ұиҜөзҡ„жЁЎејҸпјҢеҫҲе®№жҳ“з…§жҗ¬еҲ°жғ…жӯҢеҜ№е”ұеҪ“дёӯгҖӮ
йҷӨдәҶе”ұиҜөжҠҖе·§жҳҜд»ӘејҸиөӢдәҲзҡ„пјҢд»ҺеҶ…е®№зңӢпјҢжӯҢдёӯзҡ„жҠ’жғ…еҪўиұЎпјҲдҪ гҖҒжҲ‘пјүе…·жңүж¶өзӣ–жҖ§пјҢзӣёзҲұеҺҹеӣ д№ҹиҫғжЁЎзіҠпјҢиҝҷдёҺзҲұжғ…жҙ»еҠЁеҸ‘з”ҹдәҺйӣҶдҪ“еҜ№жӯҢжңүе…ігҖӮжң¬жҲ‘е’ҢйӣҶдҪ“ж— ж„ҸиҜҶеҸӘжңүеңЁиҝҷз§Қж„Ҹд№ұжғ…иҝ·зҡ„дј—дәәе”ұе’ҢдёӯпјҢдёҖи§Ҳж— йҒ—ең°еҫ—еҲ°иЎЁзҺ°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