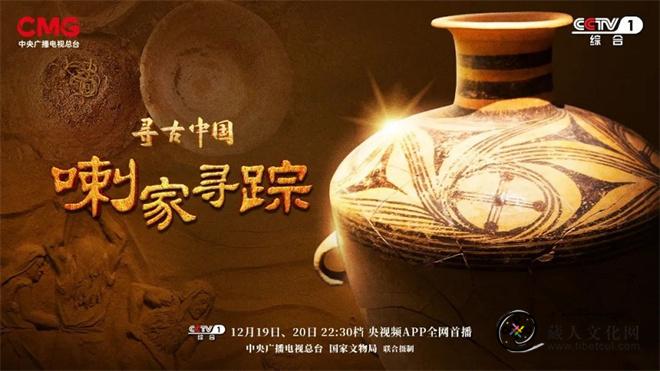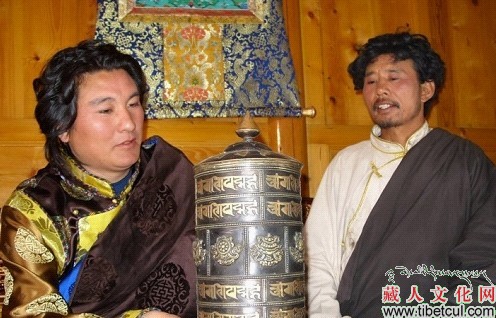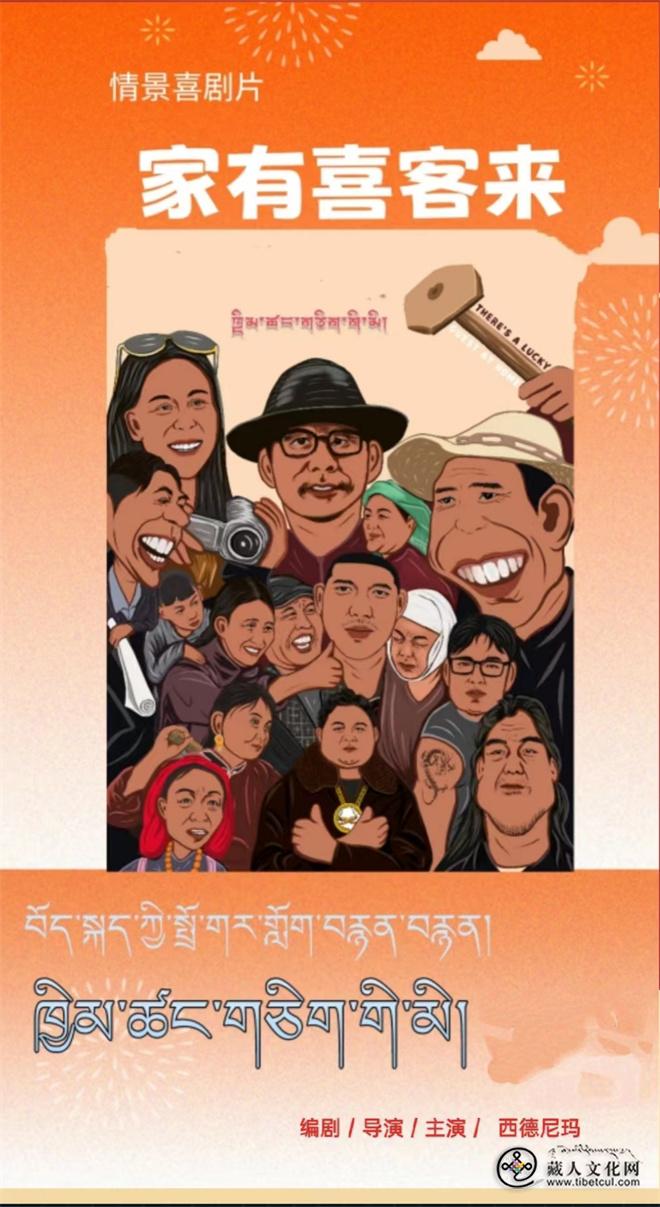1969е№ҙ12жңҲеҮәз”ҹдәҺйқ’жө·жө·еҚ—и—Ҹж—ҸиҮӘжІ»е·һиҙөеҫ·еҺҝзҡ„дёҮзҺӣжүҚж—ҰжҳҜдёҖдҪҚи—Ҹж—ҸеҜјжј”пјҢд»–зҡ„ж–°зүҮгҖҠеЎ”жҙӣгҖӢе°ұеғҸдёҖеҢ№й»‘马пјҢеҲҡеҸӮдёҺдәҶеЁҒе°јж–Ҝз”өеҪұиҠӮең°е№ізәҝз«һиөӣеҚ•е…ғпјҢеҸҲдәҺиҝ‘ж—ҘиҺ·еҫ—第52еұҠеҸ°ж№ҫз”өеҪұйҮ‘马еҘ–жңҖдҪіж”№зј–еү§жң¬еҘ–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д»ҺжқҘдёҚејәи°ғиҮӘе·ұзҡ„ж°‘ж—Ҹиә«д»ҪпјҢеӣ дёәд»–и§үеҫ—з”өеҪұе°ұжҳҜз”өеҪұгҖӮдёҚиҝҮд»–иҝҷеҮ е№ҙзҡ„з”өеҪұзЎ®е®һйғҪжҳҜи—Ҹж—ҸйўҳжқҗпјҢиҖҢдё”и—ҸиҜӯжҳҜд»–зҡ„жҜҚиҜӯпјҢд»–иҝҳжҳҜеёҢжңӣйҖҡиҝҮиҮӘе·ұзҡ„й•ңеӨҙжҠҠи—ҸеҢәзҡ„е…ЁиІҢе’ҢзҠ¶жҖҒе®Ңж•ҙең°е‘ҲзҺ°еҮәжқҘгҖӮ
гҖҠеЎ”жҙӣгҖӢж„ҸеӨ–йҖҡиҝҮе®ЎжҹҘ
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ҙпјҢжӢҚгҖҠеЎ”жҙӣгҖӢзҡ„зјҳиө·е…¶е®һд№ҹжҜ”иҫғз®ҖеҚ•пјҢд»–е…¶е®һеҶҷдәҶеҮ дёӘеү§жң¬пјҢжңүдәӣжҳҜж—¶жңәдёҚеӨӘжҲҗзҶҹе°ұжІЎиғҪжӢҚжҲҗпјҢжІЎйҖҡиҝҮе®ЎжҹҘгҖӮгҖҠеЎ”жҙӣгҖӢжҳҜж”№зј–иҮӘд»–зҡ„дёҖдёӘзҹӯзҜҮе°ҸиҜҙпјҢеҫҲж„ҸеӨ–йҖҡиҝҮдәҶе®ЎжҹҘпјҢ然еҗҺе°ұз«ӢйЎ№ејҖе§Ӣзӯ№еӨҮпјҢеҒҡеҮәдәҶиҝҷдёӘзүҮеӯҗгҖӮ
“з”·дё»и§’еЎ”жҙӣе…¶е®һжІЎжңүдёҖдёӘеӣәе®ҡзҡ„еҺҹеһӢпјҢйҰ–е…ҲжҳҜиҝҷж ·дёҖдёӘеҪўиұЎиҝӣе…ҘжҲ‘зҡ„и„‘жө·пјҢе°ұеҶҷдёӢдәҶ第дёҖеҸҘиҜқпјҢ然еҗҺж…ўж…ўеҶҷпјҢж…ўж…ўз»ҷд»–и®ҫзҪ®дәҶдёҖдәӣжғ…иҠӮпјҢжғіеҲ°еҠһиә«д»ҪиҜҒиҝҷдёӘдәӢжғ…пјҢе°ҸиҜҙйҮҢйқўз”ЁдәҶжҜ”иҫғеӨ§зҡ„зҜҮе№…еҶҷжқ‘ж°‘ж•ҙдҪ“жҚўз¬¬дәҢд»Јиә«д»ҪиҜҒпјҢ然еҗҺж…ўж…ўе°ұжңүдәәеҝөеҸЁиҝҷдёӘеЎ”жҙӣзҡ„еҗҚеӯ—пјҢеӨ§е®¶дёҚи®°еҫ—еЎ”жҙӣжҳҜи°ҒпјҢж…ўж…ўжғіиө·еЎ”жҙӣиҝҷдёӘдәәпјҢ然еҗҺеЎ”жҙӣжүҚиҝӣеҹҺеҠһиә«д»ҪиҜҒпјҢеҸ‘з”ҹдәҶеҗҺйқўзҡ„дёҖдәӣдәӢжғ…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ҙгҖӮ
иҝҷдёӘдҪңе“Ғдёӯ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第дёҖж¬Ўе°қиҜ•е…ЁзүҮз”Ёй»‘зҷҪз”»йқўжӢҚж‘„пјҢд»–и®Өдёәй»‘зҷҪз”»йқўзү№еҲ«йҖӮеҗҲз”ЁжқҘе‘ҲзҺ°дё»и§’зҡ„зҠ¶жҖҒпјҢдё»и§’з”ҹжҙ»зҡ„йӮЈз§Қз©әй—ҙпјҢйӮЈдёӘзҺҜеўғгҖӮеҰӮжһңз”ЁеҪ©иүІзҡ„иҜқдјҡжҜ”иҫғеҒҮпјҢеҰӮжһңз”Ёй»‘зҷҪзҡ„иҜқеҸҜиғҪжӣҙиғҪеҮёжҳҫдё»и§’зҡ„йӮЈз§ҚеӯӨзӢ¬ж„ҹгҖӮ“еЎ”жҙӣиҝҷдёӘдәәзү©еңЁж•…дәӢйҮҢйқўе°ұжҳҜдёҖдёӘеҫҲиҫ№зјҳеҢ–зҡ„дәәпјҢд»–еҹәжң¬дёҠи·ҹеӨ–з•ҢжІЎжңүд»Җд№Ҳе…ізі»пјҢд»–иҝӣе…ҘйӮЈдёӘзҺ°е®һдё–з•Ңзҡ„ж—¶еҖҷпјҢеҹәжң¬дёҠе°ұжҳҜеӨ„еңЁдёҖдёӘеҫҲиҫ№зјҳзҡ„дҪҚзҪ®пјҢжүҖд»ҘжҲ‘们用дәҶеӣәе®ҡжңәдҪҚпјҢе®Ңе…ЁжІЎжңүдёҖдёӘ移еҠЁзҡ„й•ңеӨҙпјҢжҲ‘и§үеҫ—йҖҡиҝҮжҢҒз»ӯзҡ„гҖҒж—¶й—ҙзҡ„жөҒйҖқпјҢиғҪжҠҠеЎ”жҙӣиә«дёҠзҡ„зҠ¶жҖҒз»ҷе‘ҲзҺ°еҮәжқҘ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ҙгҖӮ
жҲ‘дёҚжҳҜзү№еҲ«ејәи°ғи—Ҹж—ҸеҜјжј”зҡ„иә«д»Ҫ
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үеҫ—е…¶е®һиҮӘе·ұдёҚжҳҜзү№еҲ«ејәи°ғ“и—Ҹж—ҸеҜјжј””зҡ„иҝҷдёӘиә«д»ҪпјҢиҝҷжҳҜеҲ«дәәејәи°ғзҡ„гҖӮ
“жҲ‘и§үеҫ—з”өеҪұе°ұжҳҜз”өеҪұпјҢжІЎеҝ…иҰҒејәи°ғиҝҷж ·дёҖдёӘиә«д»ҪгҖӮдҪҶжҳҜзЎ®е®һжҲ‘иҝҷеҮ е№ҙжӢҚзҡ„йўҳжқҗйғҪжҳҜи—Ҹж—ҸйўҳжқҗпјҢиҖҢдё”йғҪжҳҜжҜҚиҜӯзҡ„з”өеҪұгҖӮжҲ‘еңЁеҒҡзүҮеӯҗзҡ„ж—¶еҖҷе…¶е®һжІЎжңүдёҖдёӘе®ҡдҪҚзҡ„пјҢжҜ”еҰӮжҲ‘иҝҷдёӘзүҮеӯҗжҳҜдё“й—ЁжӢҚз»ҷи—Ҹж—Ҹи§Ӯдј—зңӢпјҢжІЎжңүиҝҷдёӘеҢәеҲҶзҡ„пјҢдёҖејҖе§Ӣе°ұжҳҜйқўеҗ‘дёҚеҗҢзҡ„и§Ӯдј—пјҢжүҖд»ҘеңЁеҶҷеү§жң¬зҡ„ж—¶еҖҷд№ҹдјҡиҖғиҷ‘еҲ°дёҚеҗҢи§Ӯдј—зҡ„жҺҘеҸ—еәҰ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ҙпјҢ“еҸҜиғҪжңүдәӣдёңиҘҝжңүдәӣжғ…иҠӮпјҢеңЁи—ҸеҢәжҳҜ家喻жҲ·жҷ“зҡ„пјҢеҹәжң¬дёҠдёҚйңҖиҰҒеҒҡдәӨд»Јй“әеһ«пјҢдҪҶжҳҜдҪ зҰ»ејҖиҝҷдёӘж–ҮеҢ–зҡ„иҢғеӣҙд№ӢеҗҺпјҢе…¶д»–зҡ„и§Ӯдј—еҸҜиғҪе°ұдёҚеӨӘдәҶи§ЈпјҢжүҖд»ҘжҲ‘дјҡеңЁеҶҷеү§жң¬зҡ„ж—¶еҖҷеҒҡдёҖдәӣй“әеһ«пјҢеҒҡдёҖдәӣе®үжҺ’пјҢдҪҶдёҚжҳҜеҲ»ж„Ҹзҡ„йӮЈз§ҚиҜҙжҳҺжҲ–иҖ…й“әеһ«гҖӮдҪҶдҪ жҠҠз”өеҪұжӢҝеҲ°и—ҸеҢәж”ҫзҡ„ж—¶еҖҷи§Ӯдј—е°ұдјҡжңүдёҖз§ҚдәІеҲҮж„ҹпјҢиҝҷз§ҚдәІеҲҮж„ҹеҸҜиғҪе°ұжҳҜе»әз«ӢеңЁдёҖдёӘе…ұеҗҢзҡ„ж–ҮеҢ–пјҢе…ұеҗҢзҡ„иҜӯиЁҖпјҢе…ұеҗҢзҡ„дёҖдёӘжҖқз»ҙд№ жғҜиҝҷж ·дёҖдёӘеҹәзЎҖдёҠзҡ„гҖӮ”
еёҢжңӣйҖҡиҝҮдҪңе“Ғе‘ҲзҺ°и—ҸеҢәзҡ„е…ЁиІҢ
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ҙпјҡ“жҲ‘зҡ„з”өеҪұеңЁеҪўжҲҗеү§жң¬зҡ„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е…¶е®һд№ҹжңүеҫҲеӨҡи®ҫи®ЎпјҢе°ұжҳҜеёҢжңӣжҠҠи—ҸеҢәзҡ„е…ЁиІҢйҖҡиҝҮиҝҷдёӘзүҮеӯҗе®Ңж•ҙең°е‘ҲзҺ°еҮәжқҘпјҢд»ҘеүҚзҡ„зүҮеӯҗеғҸгҖҠйқҷйқҷзҡ„еҳӣе‘ўзҹігҖӢпјҢжҲ‘们еңЁеҫҲеӨҡең°еҢәеҒҡиҝҮдёҖдәӣе·Ўеӣһзҡ„ж”ҫжҳ пјҢдё“й—Ёз»„з»ҮдәҶдёҖдёӘж”ҫжҳ йҳҹеҺ»ж”ҫпјҢеҗҺжқҘз”өеҪұйў‘йҒ“иҝҷдәӣе№іеҸ°д№ҹдјҡж”ҫгҖӮеӣ дёәи—ҸеҢәд№ҹжІЎжңүз”өеҪұйҷўпјҢжүҖд»ҘеҫҲйҡҫеӨ§и§„жЁЎең°ж”ҫпјҢе°ұжүҫйҖӮеҪ“зҡ„ж—¶жңәпјҢеғҸиҝҷж¬ЎжҲ‘еҺ»йқ’жө·жһңжҙӣзҡ„дёҖдёӘеёӮйҮҢзҡ„дёҖдёӘиҒҢдёҡеӯҰж ЎпјҢ然еҗҺеҸӮеҠ 他们зҡ„ж ЎдјҡеҗҢзӣҹпјҢжӯЈеҘҪйӮЈиҫ№жңүдёҖдёӘеҚҺи°Ҡе…„ејҹжҚҗе»әзҡ„дёҖдёӘз”өеҪұйҷўпјҢе®ғжңүдёҖдәӣеҹәзЎҖзҡ„ж”ҫжҳ и®ҫж–ҪпјҢжүҖд»ҘжҲ‘е°ұеҖҹжӯӨжңәдјҡж”ҫдәҶд»ҘеүҚжӢҚзҡ„гҖҠдә”еҪ©зҘһз®ӯгҖӢе’Ңиҝҷж¬Ўзҡ„гҖҠеЎ”жҙӣгҖӢгҖӮ”
дёҮзҺӣжүҚж—Ұи®ӨдёәпјҢжңүж—¶еҖҷиҮӘе·ұд№ҹжҳҜеЎ”жҙӣпјҢеӨ„еңЁиҝҷж ·дёҖдёӘзҺҜеўғйҮҢйқўпјҢд№ҹдјҡеҸҚжҖқиҮӘе·ұзҡ„иә«д»ҪгҖӮ“дҪҶжҲ‘и·ҹеЎ”жҙӣиҝҳжҳҜжңүеҢәеҲ«зҡ„пјҢеЎ”жҙӣд»–жҳҜжІЎжңүиө°еҮәеҺ»пјҢе°ұжҳҜеңЁиҮӘе·ұзҡ„зҺҜеўғйҮҢйқўпјҢд»–жңүдёҖдёӘеҲ«дәәејәеҢ–д»–зҡ„иә«д»ҪпјҢ然еҗҺи®©д»–еҺ»еҜ»жүҫиҮӘе·ұзҡ„иә«д»ҪпјҢд»–иҮӘе·ұеңЁиҝҷдёӘеҜ»жүҫзҡ„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д№ҹжңүз–‘жғ‘д№ҹжңүиҝ·иҢ«жңҖеҗҺиҝ·еӨұпјҢеғҸжҲ‘зҡ„иҜқпјҢе°ұжҳҜиө°еҮәжқҘдәҶпјҢ然еҗҺеңЁдёҖдёӘи·ҹд»ҘеҫҖдёҚеҗҢзҡ„зҺҜеўғйҮҢйқўпјҢеҸҚжҖқиҮӘе·ұзҡ„еӨ„еўғпјҢеҸҚжҖқиҮӘе·ұзҡ„иә«д»ҪгҖӮеңЁзҺҜеўғйҮҢйқўејәеҢ–иҮӘе·ұзҡ„иә«д»ҪпјҢеҸҜиғҪиҝҷдёӘдёҚжҳҜйҮҚиҰҒзҡ„гҖӮжҲ‘и§үеҫ—з”өеҪұе®ғжңүиҮӘе·ұзҡ„规еҫӢпјҢз”Ёз”өеҪұзҡ„иҝҷж ·дёҖдёӘ规еҫӢпјҢеҺ»е‘ҲзҺ°иҮӘе·ұзҡ„ж–ҮеҢ–пјҢжҲ‘и§үеҫ—иҝҷдёӘжҳҜеҫҲйҮҚиҰҒзҡ„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