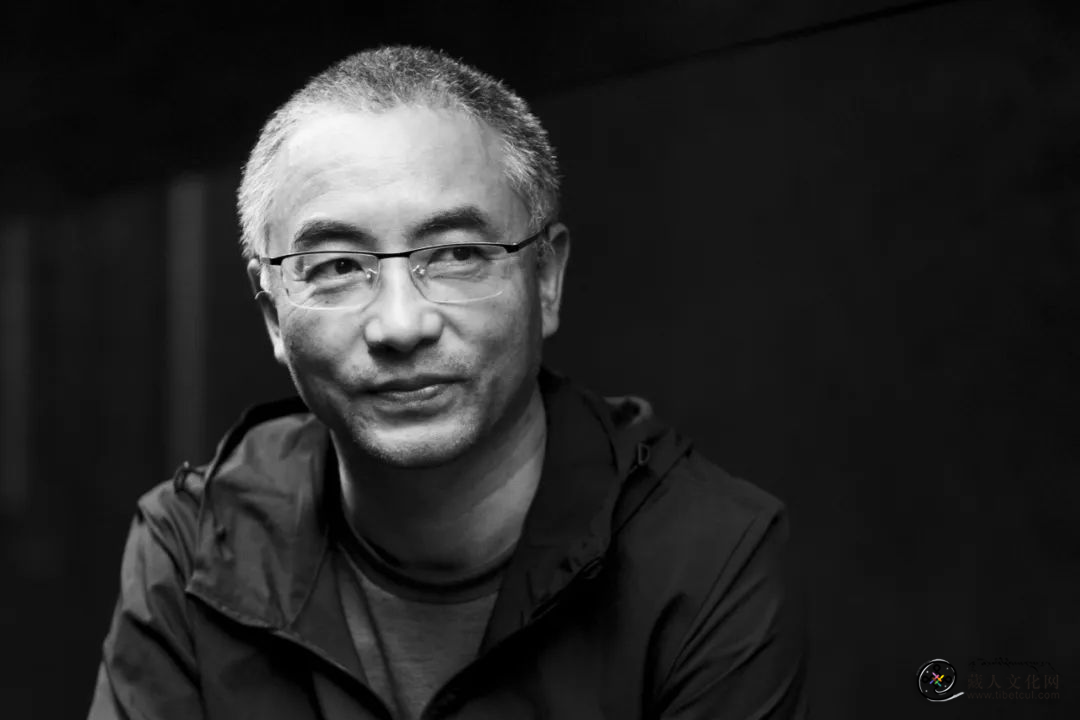经过新时期文学的迅猛发展,新世纪以来,藏族文学迎来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一些藏文文学刊物经历了最初的起步阶段,伴随经验的积累,文学品鉴力的保持以及刊物良好的运转,《章恰尔》《西藏文艺》《邦锦梅朵》《拉萨河》《民族文学》(藏文版)等刊物形成母语文学十分重要的阵地。这一时期,德本加、扎巴、扎西东主、万玛才旦、嘉布庆·德卓、拉先加等作家呈现出比较活跃的创作状态。德本加的创作一直稳定,近年来发表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专门为德本加举行了作品研讨会,据说这是国内第一次母语作家专场文学研讨会。德本加生活在藏区基层,任教二十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他被视为“母语文学的引领者”,他一贯以讽刺、幽默的笔调来揭示主人公的生存境遇,揭示时代转型与人们内心的种种体验,讽刺幽默之余是淡淡的忧伤。虽然作家惯用现实主义笔调,但常有荒诞意识和黑色幽默的先锋色彩,其“老狗”系列小说所展示的人性底色和晦暗冲突,在当下社会极具震撼力。
近十几年的藏族汉语小说也收获颇丰,文学发展势头比较强劲。伴随阿来的《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一批努力探索小说艺术的作家共同将藏族汉语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准,从小说技巧、文体探索到民族话语书写等方面与其他民族的写作展开对话。以阿来为例,在获奖之后,他又有《空山》三部曲、《格萨尔王》等长篇问世。阿来的《空山》在2000年后陆续面世,最后一部完成于2007年。这部三部曲分为《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与《空山》共六卷,是关于一个藏族村庄——“机村”的一部村落叙事。1950年至1999年,中国正处于“变”的巅峰期,“机村”和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个地域一样,处在“变”的涡流中心,“机村”的外部环境与人们的内心都承受着巨大的“变”——生长与毁灭,阿来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这种充满痛苦的生长与毁灭。这部村落叙事与《尘埃落定》不同之处在于作家目光从历史向当下的转移,具有更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更敏锐的批判意识,尽管阿来总强调他在书写普遍性,但藏民族性格与情感的流露仍旧十分鲜明。
近年来一些优秀作品也频频问世,一些年轻的藏族作家逐渐崛起,次仁罗布在阿来之后又以短篇小说《放生羊》获得2010年的鲁迅文学奖;玉树作家江洋才让写诗多年后,写出《然后在狼印奔走》《康巴方式》等小说,作品立足于康巴大地、巴塘草原,书写康巴人的游牧生活、康巴人在当下的不同生命际遇。这一时期小说的总体特点是更多追求民族话语的表达方式,在民族文学的想象中,完成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完成对民族精神底蕴的把握,揭示时代变迁中民族生活的变奏。
同一时期,藏族女性的汉语写作得到集中的展示,作品的艺术水准和现实关怀达到一定高度。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藏族文坛就有“女神时代”之说,作家马丽华如此命名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群,学者李鸿然也沿用了这一命名。以央珍、梅卓、格央、唯色为代表的女性作家构成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基础,央珍《无性别的神》、梅卓《太阳部落》《月亮营地》、格央《灵魂穿洞》、唯色《幻影憧憧》等作品展示了这一时期女作家的创作实绩。步入新世纪以来,梅卓继续发力,创作了多篇中短篇小说,结集为《麝香之爱》;其文体实验式的作品《人在高处》将纪实性作品与虚构性作品穿插在一起,构成青藏高原虚幻与现实结合的神秘色彩。继这几位代表作家之后,白玛娜珍、尼玛潘多、严英秀、央金拉姆、永基卓玛等成为这一只女性作家队伍的接续力量,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白玛娜珍的《复活的度母》以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故事展开叙事,在描写两代女性的感情经历的同时,展开了一幅西藏宗教、文化、民俗的风情画,唯美的笔触,细腻的描写,书写了属于藏地女性的难忘记忆。2010年,尼玛潘多以一部长篇小说《紫青稞》让读者感受到了久违的质朴与情切。作家以忠实的现实主义笔调描写了20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初西藏偏僻山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带来的变化,受到震动的人们在走出大山之后的挣扎、努力和迷失,但就像“紫青稞”总是执着倔强地成长于恶劣环境一样,生命力极强的“普村”人也总能找到自己生存的角落。小说中的女性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杂草一样生长,“紫青稞”一样执着,她们构成西藏人生命中最浓重的底色。云南的央金拉姆和永基卓玛将笔触根植于足下那片广阔的滇西草原、田野、山川和河流,展示了藏民族又一种风情意绪和生命体验。
在这样一个背景中,两位安多作家的创作体现出了较为稳定的气脉,尤其新世纪以来的一些作品体现出了作家浑厚有力的创作脉动。万玛才旦进行双语写作多年,近几年来的汉语短篇小说尤其引人瞩目。2014年出版的《嘛呢石,静静地敲》收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优秀小说10 篇,被国内著名作家阎连科、扎西达娃、刘醒龙推崇为最好的藏地生活小说。龙仁青从早期的《转世》《锅庄》到近年来的《光荣的草原》《人贩子》都十分关注当下牧民的精神现实,专注于在现实主义中注入更多技巧,打造小说艺术的高度。近期刚刚出版的“龙仁青藏地文典”三卷本精选了他的小说、散文和译文创作,在藏区文坛制造了一股“龙卷风”。
九叶诗人唐湜有一个观点:“诗歌应该体现诗人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成。”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小说作家。万玛才旦和龙仁青作为藏族当代作家中的代表,各自在他们自己的文本中发展和完成着自己。这种发展和完成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两位作家在叙事艺术上的追求,精进,是他们作为作家发展和完成自我的重要保证。
万玛才旦兼用汉藏两种文字创作。藏文硕士的求学经历使他受到过良好的母语教育。这也使他的汉文小说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气韵。在2014年6月举办的万玛才旦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研讨会上,洪治纲、宁小龄等评论家就集中阐述了万玛才旦小说“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万玛才旦的小说往往故事比较简单,情节并不会更丰富,这的确与极简主义“少即为多”的美学追求有相似之处。然而细读他的文本,我们会发现他的重要作品都具有一个共性特征,即叙事上有意的延宕,铺展乃至停滞,造成细节上的冗赘、甚至肥大,最终构成叙事内在的紧张和尖锐,从而通过小说形式的修辞达到揭示主题的作用。我姑且将其称之为:“手磨糌粑式的细节肥大”。
《乌金的牙齿》用了接近一半的篇幅来细细叙述“我”对乌金牙齿的思索,用这一叙事行为最大化地揭示了主题。乌金圆寂,寺庙要建佛塔纪念,佛塔中要放入乌金的牙齿,结果搜集的牙齿多达58颗,“我”问别人、查询网络,知道正常该有的颗数,又想起小时在乌金家被他父亲拔过一颗乳牙,这颗牙也被寺庙的僧人收集到塔中,“和乌金那些尊贵的牙齿一起享受着万千信众的顶礼膜拜”。这种思索的过程被充分研磨、细化,其间,有关牙齿的颗数,“我”与乌金牙齿的混杂,这些细节含混的外壳被有意冗赘化处理的言语逐步磨亮,小说主题也就散发出光芒:佛性即至高的人性表现,乌金的思辨追问、“我”的思辨迷惘都是可贵的“人”的探索。
相比《乌金的牙齿》体现出的思辨精神,《塔洛》是万玛才旦少有的表达愤怒的作品之一。但是,和愤怒及一种无可皈依的痛感相对的是,《塔洛》叙事的语态却惯常的安静。一个叫塔洛的牧羊人在试图获取身份的过程中却丢失身份的故事本来可以来得更荒诞,但作家仍然用充分的研磨、延宕来冷静地深入文本的核心。这种致使细节肥大的手段即是对话。通篇绵密的对话编织了一种密不透风的“低气压”环境,压抑、透不过气来的感受与塔洛只字不漏背诵《为人民服务》的几乎令人因屏息而昏厥的话语效果相当。这种对话的回环荡漾、铺展冗赘最终为主题的揭示形成了最佳的语义场。我一直很警惕同时做编剧的作家的小说,他们往往因为写作习惯将小说文本处理成以对话为主体的剧本,失去了小说本该有的曲径通幽。但万玛才旦这篇小说还是让人松了一口气,对话在这里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它得牢牢承担起护送塔洛直抵叙事终点的重任。它聒噪,它喧闹,但惟其如此,塔洛被遮蔽的生命意义才得以反衬出来。
《午后》是万玛才旦短篇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篇,他先后两次将其选入小说选集。这篇小说写一个时间感错乱的人的故事。类似于一种“白日梦”型的叙事。詹姆斯•瑟伯的短篇小说《沃尔特·米蒂的隐秘生活》就是这种“白日梦”小说成功的例子。刘呐鸥的新感觉小说《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也反映了飞速回旋的城市之舞中时间不感症者的病态反应。《午后》将这种“时间不感症者”的故事植入了藏地。因此小说主题最终获得意义的路径是对少年昂本的“时间不感症”表现展开了类似于“流浪汉”小说的叙事路数,路遇贾巴、寡妇周措、东巴大叔,每一个事件都被细细铺展,这一个个事件似乎象征着“贪、嗔、痴”的宗教内涵,因此少年昂本一次约会的过程竟然一生般漫长。这种昼夜颠倒,一瞬百年的时间叙事,这种对时间任意捏合的时间修辞,使小说《午后》获得了内在结构紧致,外在阅读放松愉悦的感受。
纵观万玛才旦两部小说集,收入他出版于2011年的《流浪歌手的梦》中的《尸说新语:枪》在笔者看来是他又一部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文本。这篇小说看上去是一部仿写之作,但从结构上来看,不啻于是他小说诞生的“息壤”。小说借鉴了藏族口传经典“如意宝尸的故事”(又称为“尸语故事”),以“说不完的故事”类型为文本结构,加入具有现代元素的“枪”,而“枪”这一异质元素的介入,却推动“说不完的故事”周而复始,延宕铺展,回到原点。《陌生人》《第九个男人》就是这种结构的复现。这种循环往复的“手磨糌粑式的细节肥大”,非常符合万玛才旦沉静的性格,他很有耐心地研磨小说故事,鞣制一个个细节,使小说逐步散发出馥郁的味道,最终打上万玛才旦独特的叙事徽记。这种小说雕镂的方式,反映在他的电影叙事中,就是惯用长镜头来细细碾过,目力所及之处,一定刻骨铭心。
龙仁青写于九十年代初的《转世》曾入选外教社出版的《英译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精选》,应该说,从这时起,龙仁青的写作就一直葆有鲜明的个性。出生于青海湖畔铁卜加草原一个汉藏游牧家庭中的龙仁青从小就徜徉于汉藏双重文化之中,加之所受的良好的双语教育,使他能够自由穿行在汉藏文化时空中。赤岭(今日月山)东西两麓一直以来就是青海“茶马互市”的重镇,民族交往呈现着纷繁复杂的状态,农民与牧民在经济、文化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上的交往互动更是频繁生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互动的历史、汉藏文化交流的背景,加之龙仁青个人的家庭背景三重因素使得龙仁青既拥有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穿越能力,又葆有一种恒定的悲悯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持久穿透力使得他的小说文本形成了可观的精神容量。这种精神容量在小说文本中外化为或克制冷静,或诗化多义,或荒诞戏谑的叙事策略中。
《人贩子》是龙仁青最好的小说之一。小说描写了一场慈善活动引发的悲剧。在情节发展的五个片段中,作家极具耐心地缓缓道来: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父子独特的个性,充满地方性知识的意蕴……作家在前三个片段中运用了类似酒曲牧歌的悠扬调子,节奏舒缓,不急切,在做足了一切情节上的准备之后,情节突转,悲剧遽然发生,儿子被山洪卷走,尼玛思子心切,被误会为人贩子,小说主题至此揭幕。这种极度克制、冷静的悲怆叙事带来的震撼力丝毫不亚于小说中决堤的山洪所具有的摧枯拉朽的力度。
《鸟巢》也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一开篇就充满着荒诞的意味。小鸟筑巢的大经堂却是曲果镇的党政机关曾经的所在地;为了追赶北京的潮流,筑巢的大经堂要被拆除,取代它的是一所模仿北京“鸟巢”的建筑。然而,这种荒诞的结果却是以卓玛少女怀春的憧憬和青春悸动的情愫徐徐展开的。小说中的描写恍惚带有铁凝《哦,香雪》的抒情调子,整个结构却与汪曾祺短篇小说《徙》相似,充满诗化的氛围。这种抒情化的情调叙事丝毫没有减弱小说的荒诞性,反而因为这种参差对照给予了读者更富于层次感的阅读体验。
《香巴拉》是作家不多的探究女性内心的作品。与其他探讨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文本不同的是,面对私奔这样一种惯常要受到道德谴责的行为,小说人物表现出的一种暧昧态度。这与沈从文《萧萧》中众人对偷情生子的萧萧的暧昧态度何其相似。这是边地文化骨血中的自由不羁,离经叛道的神似。除却这一重意蕴,主人公金措游移、踌躇的状态揭示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私奔故事,香巴拉,也并不仅仅是理想生活的象征。这种以女性自我放逐,以渴望出走代替对自我的发现,或是以死亡实现对自我的追寻的故事带有类型学特征。乔万尼·维尔加的《格拉米格纳的情人》、丁玲的《阿毛姑娘》、萧红的《小城三月》、汪曾祺的《徙》以及阿来的《自愿被拐卖的卓玛》都属于这一主题。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写,作家们都以自己不同的人生体验进行了演绎。而龙仁青这种多义叙事赋予了这个简单故事以饱满的意蕴厚度,完全可以将其列入这一类主题小说的方阵之中。
曾有论者论及龙仁青小说中的“孤独感”,在我看来,正是作家精神容量巨大的悲悯精神构成了一个个富于孤独感的文本。这种文本要找到同样具有悲悯精神的读者并不容易。作家通过悲怆叙事、情调叙事和多义叙事等策略体现了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的叙事艺术。作家是离群索居的人,恰是这种疏离,留给他们漫长的足以细细雕镂语言的时间,也留给他们集聚故事活力的漫漶空间。
万玛才旦、龙仁青以及阿来、次仁罗布、德本加、江洋才让等藏族作家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书写中留下了不同的叙事表情,就短篇小说而言,则因为这两位作家柔弱却勇猛的追求而日益丰满动人。
原刊于《青海湖》2019年第10期

万玛才旦,电影导演,编剧,作家。已出版藏、汉文小说集多部,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推介到国外,获“青海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入选“中国年度小说排行榜”等专业榜单。电影作品有《静静的嘛呢石》《塔洛》等,曾获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等多项电影大奖。2018年9月,电影《撞死了一只羊》获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剧本”奖。

龙仁青,出版有原创、翻译作品20余部。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省《格萨尔》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民族文学》《芳草》《章恰尔》等汉藏文报刊发表作品。

卓玛,青海民族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青藏多民族文学。